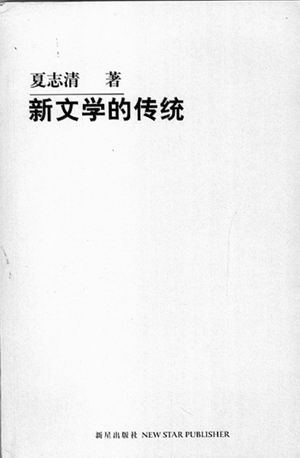
自1979年夏志清教授的《新文学的传统》繁体字版面世以来,经过
何谓新文学的传统?大体来说,乃五四的传统。然而即使就五四本身,也是各大门派林立,有鲁迅的彻底否定几千年来的封建家族制、冲出铁牢笼的传统;有胡适的“整理国故”,目的在于在历史的“烂纸堆”里捉妖打鬼的传统;有周作人的发掘传统的非主流资源,创造性地转化为今世今日所用的传统……因此关于新文学的传统,说法也莫衷一是,有张扬个体精神之说,有为人生写人生之说,有世界性的开放意识之说,也有人道主义、民间立场之说。而有一点,是大多数论者都持有的,新文学的传统,就是反传统,就是要体现出“新”。一群接受过西方思潮洗礼的学者和文人,在面对满目疮痍、国将不国时,把罪责都压在了传统的身上,于是迫不及待地要与中国古代的传统斩断血缘关系,构建起一种全新的与历史完全断裂的传统。然而历史究竟不是快刀斩乱麻,因此夏先生开宗明义地提出:“新文学的传统,不单指现代文学,也包括了属于同一传统的古代文学。大体说来,它是有别于士大夫文学那个传统的传统”,敢于正面承认新文学的传统并不只是新文学所独有,而是承了古代文学衣钵的论调的确不多,夏先生在这里显出了他独到的眼光与勇气。按夏先生言,新文学承的,又是古代文学主流的、光明正大的那一支,“我们认为中国的文学传统应该一直是入世的,关注人生现实的,富有儒家仁爱精神的,则我们可以说这个传统进入20世纪后才真正发扬光大,走上了一条康庄大道”。从《诗经》到古乐府、从杜甫到关汉卿,再到晚清谴责小说,“载道”、“写实”一直就占据着主流的位置,肯为老百姓说话也一直一脉相承。所谓士大夫文学的传统,当然是指那些明哲保身、温柔敦厚、躲在山水田园间求个怡然自得最终连同自身一起消泯于大自然的“出世”一派,这是主流拒斥的,也是新文学拒斥的,当然不能“躲进小楼成一统”,于是夏先生指出新文学的两面旗帜――“人道主义”、“写实主义”,用他后面的话来说是“批评人心、针砭社会的写实传统”,按照这一思路,夏先生对自己以往的文学史观作出了修正,肯定了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倡的“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的确为新文学家指点了一条必走的路径”;强调了以往忽略的萧红与端木蕻良,“《呼兰河传》、《科尔沁旗草原》二书尤该重视,讨论它们的篇幅应该不比讨论鲁迅的短篇小说少,这样才能显示文学史家的公正”。当然强调新文学传统与古文学传统一脉相承的一面,并不意味着要把新文学的“新”完全抹煞,五四一代受西方思潮的洗礼,这是任何人也否认不了的事实,问题在于西方思潮究竟对新文学产生了多大程度的影响,是令其脱胎换骨呢还只是改头换面?夏先生的这番话说得中肯,“中国现代作家,正因为他们吸收了西方思想,读了西方作品,才能写出比古代文人更有劲、更有生气的作品来。至少中国大半旧小说,其艺术成就,其对人生关注的严肃态度,实在不能同新小说相比的”。此言比他早年说的“中国文学传统里并没有一个正视人生的宗教观”、“摒弃了传统的宗教信仰”就可值得推敲得多。如果说基督教文化背景下的西方文学凝视的是人与上帝的彼岸世界,能够写出具形而上意味的人间永恒的矛盾和冲突,那么,在上帝死了的现代,西方文学就信仰式微、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虚无与荒诞。而儒家文化背景下的中国文学关注的则是此岸当下与感时忧国,以齐家治国为要务,信仰就被搁浅了,所以对于中国文人而言,信儒之外兼信佛道,从来都不是什么问题。两种不同的文化体系,如果一定说关注上帝就比关注百姓来得伟大的话,就难逃西方中心论之嫌,好在夏先生及时作了反省,“拿富有宗教意义的西方名著尺度来衡量现代中国文学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必要的”,否则又会引来一阵新的棒喝。不人云亦云,不以西方为尺度,夏先生依照自己独特的文学标准,从五四人物品评到当代台湾小说评析,都有许多精辟独到的见解。其中较具特色的是《亲情与爱情――漫谈许地山、顾一樵的作品》,这是的的确确的漫谈,从《浮生六记》到胡适《四十自述》,从沙翁名剧到梁实秋的恋爱史,从文化传统到文学创作,从许对顾的感悟到夏对许的评论,乍一看的确让人产生云雾中游走的感觉,可谓是批评的批评,感悟的感悟。接下来讲了一个有些熟悉又有些老套的故事,恩爱夫妻被亲人硬生生地拆开,古有《孔雀东南飞》,近有《金锁记》,当你正对棒打鸳鸯者咬牙切齿、指望夏先生跟你一起来笔伐声讨封建家长制之际,他却也如许地山一样沾染了佛教的悲悯情怀,拿中国是一个重亲情、爱父母甚过爱夫妇的民族来搪塞了事,再感叹了几句古代女子的苦命,在我们遗憾没有大快人心之际也不得不感慨夏先生的另辟蹊径。
批评人心,针砭社会,这不仅为新文学的传统,也实为夏先生作文的传统。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批评人心,针砭社会”与我们一般理解的左翼革命现实主义是有出入的,更准确的表述是通过作用于人心来达到针砭社会的目的,即与五四的启蒙传统一拍即合。既然要批评人心、直指人心,当然首先得直指人身,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知人论世”,因此注重人物的生平考证,《〈胡适杂忆〉序》、《重会钱钟书记实》对两位大家生平的琐事娓娓道来,胡适与江冬秀的婚姻生活、胡适与几位女友的微妙关系、钱钟书妻妹的才气与早逝……并大有乐此不疲之势。琐是琐了点,可贵的在于夏先生一样能做到“正襟危坐”、考证严密,也许是被正统的文学评论的书写惯坏了口味的我们一时的不适应,所谓知人论世,当然不是简单地交待生平就算了事。同时在品评人物或者作品时,敢于直言不讳:丁玲30年代的作品“实在一篇也说不上是佳作”,庐隐“连中文都不通的,大可不列其名”、“假如收到(朱自清)《匆匆》这样拙劣的文稿,目今有眼光的副刊编辑,我想都会把它丢进字纸篓去的”,中国时报小说奖首奖作者“还得好好习写”,誉则誉之,毁则毁之,态度鲜明,见惯了内地许多评论家说了三分批评马上来三分解释三分肯定外加一分希望,就如夏志清对李健吾的评价“批评的尺度太宽,对作家鼓励有余,严正不够”,我们的确为之耳目一新。当然夏的严正或许只是他没有为稻梁谋的后顾之忧。关于针砭社会,夏老先生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伊朗学生盲目的示威游行,美国学文学的青年选修侦探、恐怖小说,台湾琼瑶之流的“新大众小说”的抬头,以及最近在一则访谈里谈到的“现在是美国的娱乐产品水平低劣,全世界都跟着低”,种种现状,都是不尽如人意,作为批评家,要做的不应是回避现实、推诿责任,而应引导“大众文艺”向“高雅文艺”迈进,所以夏先生一直在为“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而殚精竭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