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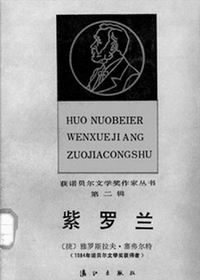
[捷]雅罗斯拉夫・赛弗尔特著,星灿译,漓江出版社1986年第一版
奥威尔预言“老大哥在看着你”的那个年头,两个来自弗吉尼亚州的美国人通过捷克斯洛伐克官员的层层盘查,进入这个国家。他们的行箧中装着雅罗斯拉夫・赛弗尔特的诗集,从那时开始,这位捷克诗人的作品英译才越来越多,换句话说,开始走向世界。
“老大哥在看着你”是虚构的故事,但到了1984年,赛弗尔特的处境并不比温斯顿强出多少。他病得很重,卧床不起;他很难写作,他的作品全面遭禁。当得知诗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后,布拉格的一些书店店主按捺不住兴奋,悄悄挂起了他的肖像,旋即被勒令摘下。捷克斯洛伐克《红色权利报》上发表了一篇评论,称:赛弗尔特作为一名诗人和一位公民,“不是没有错误的,甚至是有争议的,但是他的作品的重要性对我国的诗歌而言是无可非议的。”
评论措辞谨慎。这个去日无多的病人受到了充分的“照顾”,因为他的影响力太大了。就在3年前,老人在自己的80大寿时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几百封贺信,还出版了《世界美如斯》,这部回忆散文集描叙家乡,怀思故人,是典型的人到晚年的恬静散淡之作,但人们可以猜想,为促成这本书的出版,诗人强忍着吞下了多少创伤记忆。因为,赛弗尔特从来就“不是没有错误的”诗人。
“我不善于处理细节……我不善于故意放慢速度、在情节上来个停顿……所以我大多只写诗。我觉得写诗容易些。”这是实话,赛弗尔特的记性不算好,所以他的回忆散文文字间隙很大,文字之间有诗性的抒情蹈虚腾跃,补充记忆之不足。《世界美如斯》跟一些我们熟悉的斯拉夫人的回忆录――例如吉皮乌斯的《往事如昨》、帕乌斯托夫斯基的《一生的故事》――一样,东鳞西爪,疏朗如水,处处少不了家思乡恋、母爱亲情,少不了“寒梅著花未”式的缱绻问候。“我出生在日什科夫。布拉格这一郊区,它的如画景色,它的欢乐、贫穷和忧伤、过去和现在都始终在我心中。从前,倘若有人蒙住我的眼睛,让我从克拉洛夫斯基-维诺赫拉德走往日什科夫,我能准确无误地说出它们各自的地界。”在这个寡民小国,赛弗尔特和古往今来几乎所有的捷克诗人一样,把布拉格视为掌上明珠,五百年前领导独立运动的扬・胡斯,则是民族无可争议的第一英雄。
所以赛弗尔特对二战中的遭际没齿难忘。1945年5月,布拉格的爱国者们在德军撤离之前猝然发动起义,2000人为之献身,场面无比惨烈。起义当日,赛弗尔特平生第一次近距离面对死亡,被德军的刺刀顶着,穿过战友的尸首走向刑场。读他回忆的当时的心理状况,其性格可见一斑:“唉,车站上面的这条道路啊,曾经有过多少次,多少次,我幸福地、喜滋滋地在此奔跑。从童年时代起就在此奔跑了。每到假期,我总是急匆匆地经过这里,兴高采烈地上克拉卢比去度假,回来时又经过这里投入妈妈的怀抱……”他哪里是个战士,他胆怯、内向、多愁善感;他极有自知之明地说,很是羡慕“陀思妥耶夫斯基当年绝无仅有的经历:被判处死刑,体验了必须同生命告别和接受无情现实的滋味,然后死里逃生,重新品尝到生命的甜蜜,得救了”。跟上刑场的老陀相比,“一个小国家的抒情诗人”被穷途末路的德国人押在枪下,最后侥幸逃生,实在不值得引以为傲。
然而,这种性格却与诗人的创作互为表里:即使在描述战争的恐怖时,赛弗尔特的笔触也离不开生活:“我看见/我所爱者的笑脸”(《克拉卢比轰炸》)他放声控诉暴力的句子听起来也带着羞怯:“再也别来了,战争!”这些词句统统流自心灵深处,因此在战争面前,他仍在挂念诗的命运:“那时,我连一行句子/都无法构思!”别说什么“国家不幸诗家幸”,在诗人心中,战争这类东西是他想都不敢想的,因为它连世间最最娇美的事物――诗歌――也要伤害!在《身为诗人》中,赛弗尔特把音乐和诗歌描述成“世上至美之物”――“当然,还有爱。”这爱也远非柏拉图式的:它总是伴以“女人的一笑和/风拂起的头发。”回忆往事的时候,赛弗尔特从不掩饰自己对可餐秀色的喜爱,不住地对邂逅的年轻女子施以一吻之邀。对他而言,诗歌、故乡和女人实是平级的三大至爱主题。
1945年的那个晚春,赛弗尔特惊魂甫定,发现自己因为战时出版的一批鼓舞人心的诗集,已跃升为民族第一诗人,犹如叶芝之于爱尔兰,耶胡达・阿米亥之于以色列。赛弗尔特记录了好友万楚拉惨死于纳粹之手的全部经过,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本回忆录注重的是感伤而非思考,很少表现他与社会大背景的密切接触。我们看不见另一个赛弗尔特――回忆录面世之时,那个“错误的”赛弗尔特黯然背转了身去。
米兰・昆德拉记得赛弗尔特在国家电台的嘶声疾呼:“我们不过被奴役的生活!”他后来在《纽约时报》上赞道:“他已经行走困难,需要拄双拐。也许正是因此,他坐在椅子上仿佛一块岩石:纹丝不动、结实、坚硬。(他是)诗人,民族天才的化身,无权者惟一的光荣。”往昔历历在目,他怎么可能忘记呢?但他必须隐忍不发,默然地做一块让“老大哥”们感到棘手的岩石。靠着那些“伪装”功能极强的抒情诗,靠着民众的爱戴,靠着同S.K.诺伊曼、奈兹瓦尔、霍拉、沙尔达等他在书中深情追忆的文化人的良好关系,赛弗尔特躲过了迫害,在肃杀的冬季出版了一本回忆春天(尽管只回忆了一个)、呼唤春天的书――《世界美如斯》。关于爱与生活,他能尽吐肺腑:“今天我已深深懂得,当一个人断然同一切荒谬行径、一切渴望和形形色色的蠢事――它们同青年时代是那样的相称――永远决裂的时候,他便开始衰老。”而就自己的国家,他只能暗暗地、含沙射影地表态:“我们这个世纪怎么说也像屠宰场屠夫手里的抹布,不时地有又浓又黑的血水在流淌。”
两位美国来客――诗人汤姆・奥格莱迪和语言学家保罗・雅加斯基――几经辗转终于见到了诗人。他们后来如此感慨道:“你永远不会想到对他撒谎。你能想到的只是要拥抱他,告诉他你所知道的一切。”我们不了解他们谈了什么,但我们可以感知,那些赛弗尔特没能说出来的东西,就像种子一样流散到各处;它们并未死灭,而是一直醒着,一直等到春天捱过漫长的沉睡、终于复苏的一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