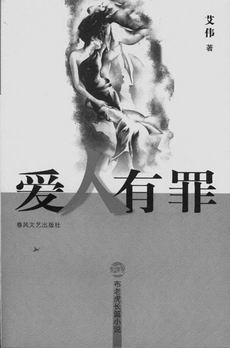
与《爱人同志》不同,《爱人有罪》从一开始就撇开了某些历史意志的崇高光环,撇开了某些狂欢性的现实场景,而是将人物自始至终置于一种极为幽暗的个人心境之中,在内心化的叙事语调中,围绕着“罪,惩罚,救赎”这几个看似庸常的主题,对生命的各种可能性状态进行了犀利的追问。年轻漂亮的俞智丽被人强奸了,而受到惩罚的不是真正的强奸犯,却是一直暗恋并跟踪她的鲁建。面对真相的揭示以及权力意志的强制性遮蔽,作为个体生命的存在,无论是俞智丽还是鲁建,都已无力改变现实的格局。为此,鲁建付出了长达八年的牢狱之灾,而俞智丽也由此踏上了漫漫的“赎罪”之路。
如果从“罪”的本质上进行追问,无论是俞智丽还是鲁建,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罪,但是,他们都活在沉重的“罪责”之中,并因此而被现实轻易地改写了各自的命运。这里,艾伟并没有极力推演执法部门对法律尊严的草率处理,也没有强力凸现权力意志对个人命运的藐视姿态,而是通过一种伦理化的道德转换,将本应由权力体系所承载的法律过错,巧妙地转化为个人的生命负重。这也表明,作者所要表达的,其实不只是权力意志对个人命运的践踏或伤害,而是人物在面对“罪责”时的内心挣扎以及某些可能性的选择。所以,在《爱人有罪》里,权力始终处于一种隐秘的控制状态,叙述的主体则是被伦理化的罪责折磨得无所适从的灵魂。
我之所以强调这种“罪责”是一种伦理化的精神存在,是因为“强奸罪”本身就包含了极为丰富的伦理信息。尤其是在观念并不开放的80年代初期,面对这一罪名,无论是凶手还是受害者,其精神负重都要远远超过法律意义上的惩罚与庇护。艾伟正是从这种特殊的事件入手,在庞杂的伦理化语境中,将叙事话语自始至终对准人物的心理世界,即通过纯粹的内心化叙述,不断地促使人物进入各种无法摆脱的伦理困境之中。譬如,俞智丽在遭受强奸之后,生活的自信力旋即出现了毁灭性的打击,以至于在家庭冲突中逼得母亲自杀身亡。后来,随着真正的凶手出现,她又发现自己还冤枉了一个好人。双重的过错终于迫使她无法原谅自己。“她是有罪的。她一直担负着害死母亲的罪,现在还担负着害那人的罪。”同样,鲁建出狱之后,他首先要解决的不仅仅是冤屈,还有罪名本身所隐含的伦理耻辱。所以他迫切地要找到俞智丽,找到精神蒙羞和身体受惩的理由,以便调整自己内心的失衡状态。
事实上,随着所有真相的逐渐显露,尤其是面对以姚力为代表的权力意志,鲁建已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冤屈和耻辱都将不可能被洗尽。但本能式的代偿愿望又迫使他无法就此罢休。在这种绝望的境域中,再度跟踪俞智丽便成了他寻求最后慰藉(或反抗)的惟一方式。《爱人有罪》正是在这种特殊的精神维度上展开了它的叙事。一方面,随着鲁建跟踪的持续,俞智丽近乎疯狂的赎罪式生活缓缓地展现出来,“她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帮助别人这件事上。”“她现在看起来比谁都崇高,不是宣传的那种高尚,是真正的骨子里的高尚。这样的人你一辈子也想象不出来。”而崇高的恒定价值,以及围绕着“崇高”所散发出来的母性情怀,又使俞智丽卷入各种正常或不正常的情感纠葛之中。但是,在俞智丽的心中,她真正需要赎罪的对象是鲁建,所以她毅然决然地接受了鲁建的情感,在“爱人”的名义下,以受虐式的惩罚意识,在本能体验中实现其隐秘的补偿意愿。另一方面,鲁建在获得俞智丽的情感之后,虽然使心理的某一方面获得了补偿,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社会伦理对他的判定。而且,在这种多少有些畸形的情感中,他又陷入了一种新的伦理冲突之中,譬如对待俞智丽的前夫和女儿,对待俞智丽的社会声誉……等等。
罪被确立之后,赎罪注定会成为一种无法结束的自我抗争。当俞智丽以绝对性的向善愿望去赎罪时,她终于发现,自己又迅速地滑入了各种新的“罪责”之中。同样,鲁建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自身“有罪”的社会身份,结果依然被现实伦理束缚在异常仄逼的生存空间里,以至于只有通过不断地施虐来缓和内心的痛苦。《爱人有罪》就是在这种尴尬的伦理困境中,让人物在自身的内心世界里反复盘旋,从而将作者的审美触须延伸到各种异常复杂的现实境域里――历史的强悍姿态,权力的潜规则,法律之罪与伦理之罪的巨大分裂,各种理性与非理性的尖锐对抗……它们像一团乱麻,将俞智丽和鲁建的情感不自觉地搅拌成一种无法了结的“孽缘”。
《爱人有罪》所散发出来的丰富信息,远远超过了“罪与惩罚”和“罪与救赎”的单纯命题,伸展到很多阐释不尽的生存困境之中。而作者对短句的精心运用,又像急促不停的自我追问,使人物的选择和抗争不断地陷入无法自控的状态――这种近乎无助的生存,或许正是人类的真实境况,犹如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
《爱人有罪》,艾伟著,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一版,28.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