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的思想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思想家从生活中提取的抽象范畴和创构的艰深观念体系,二是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真正发挥作用的观念和信条。这两个层面当然是密切联系着的,二者的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是不言而喻的。在当代内地学界对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中,大多研究的是前面一个方面,对于后一方面的研究则略显
在后一方面的研究中,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的陈弱水先生将社会史和思想史的研究结合起来,较好地探索了中国传统社会中真正发挥过作用的“公”、“义”等观念和信条,可以为我们提供有意义的借鉴。在此,我们想以《公共意识与中国文化》一书对华人精神世界的一个探索来展示一下他的研究对我们的可能启示。
在这本书中,有几篇文章对华人精神世界的历史性缺失进行了考察。陈先生通过对宋以来的童蒙书、家训和善书的梳理和勾连得出一个深刻切实的结论:一个方面,“从童蒙书、家训可以明显看出,近世中国的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对社会抱持疏离、疑惧的态度。世道险恶是人们对社会的一个基本看法,进入社会活动时,要随时小心,避免受害,在家中,要严防外界的侵袭”(第151页);另一个方面,从这些读物中还可以看出,在近世中国,“宗教社群和不少人士都强力鼓励慈善的心理与救贫济危的行为,对于人间苦难的同情和救援,是近世中国社会伦理意识的核心”(第151页)。从表面看来,陈先生在此揭示的两个方面在逻辑上似乎构成某种矛盾,但在真正的中国传统社会现实中,二者确乎同时存在且可构成互补,从某种意义上说,后者也许正是前者的产物和救治措施。而话到此处,我们自然想到的是,在中国近世以来的社会真实和思想真实中,这两个方面到底哪一个力量大,到底哪一个是社会生活和思想的主要方面?陈先生指出:“疏离的社会观可能比较普遍,力量也可能比较大。”(第152页)对此,他给出了自己的直觉根据和逻辑根据:“疏离的社会观与慈善救济是不同性质的观点。前者是普遍存在的心理习惯”,后者“是一个被宣扬的价值”,由于宣扬它的“机制是松散的,也缺乏社会组织上的配合,渗入人心的程度如何,颇可怀疑”(第152页)。也就是说,疑惧和疏离构成中国近世精神世界的主要内容,而救援和慈善则是次要的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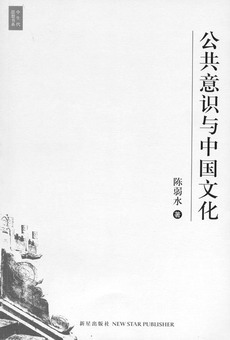
问题在于华人精神世界的这种来自历史的缺失并不仅仅是一个道德领域的问题,它深刻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对此,陈先生指出:“第一是为社会带来混乱。当社会状态已发生重大变化,公共领域急速扩大,而公民水平却仍低落之时,社会自然不易维持良好的秩序。缺乏秩序的结果则是个人与社会整体必须耗费许多资源应付这种混乱的局面,进而导致生活质量常有不升反降的情况。另一项影响则是现代化直接受到阻碍。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华人社会所面临的最艰巨工作之一就是,如何使现代社会所必需的种种政治、行政、法律制度得以建立生根,这可以说是现代化的软件基础工程。由于这些制度、法规大都和公共事务有关,如果没有健康的公民文化的支持,它们很难顺利运行,经常只能沦为纸上之具文。”(第64页)
应该说,陈先生的结论是符合中国近世和近代社会的史实和逻辑常识的,他也为我们提供了理解中国社会的一个切入点。但是,他揭示的华人精神世界的这个历史性缺失是不是会永远“缺失”下去呢?或者说,这种缺失是否是华人精神世界的宿命呢?我觉得他对日本文明进程的考察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
日本社会公共领域的弱小和对公共领域规范的漠然,在明治之前及明治初期,无疑也是极为严重的,这也是日本政府和整个知识界大力推行公德的原因。那么,华人社会经过努力,显然也可以改进公德水平。这是因为文明开化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过程,是人类社会演进中确定不移的趋势,是人类物质文明长期稳定提高的必然结果。华人社会想要脱离开这一必然性是不可想象的。而其中的关键,显然在于如何通过人的自觉努力来实现这一历史必然性。这又涉及本文开头所谈的思想创构和思想运用的关系问题。
通过中国知识分子对古今中外道德资源的开掘、阐发、创构和宣扬,影响社会大众的生活和信仰,使之符合今日人类文明的较高道德水准,这是中华民族克服这一历史性缺失的必由之路。当然,如果政治的力量也能够给予推动,那就会事半功倍了。
《公共意识与中国文化》,陈弱水著,新星出版社,2006年3月第一版,29.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