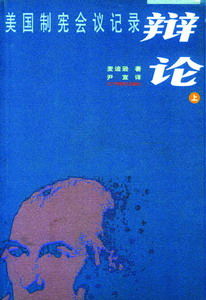
朋友把一本书放上我的案头:易中天著《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
易中天先生在“后记”里说:“令人高兴的是,2003年
早在100年前,特纳给他的朋友、《辩论》英文版编者法兰德写信说:“再无一人像我这样明白,你这样的作品,会把你的姓名与世界政治史中最有生命力的记录永远连在一起,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解说将如鸿毛飞逝,而我独具慧眼所见之书,却会走进寻常百姓之家,成为百谈不厌的话题,我自以为明白却未真懂的内容,将幸运地散落于街头巷尾,排成长队的学者,将会感戴你的这份深恩厚德。”
《辩论》的英文封面上,麦迪逊的姓名后面,没有“著”字;这本书的内容,是美国制宪会议代表的“群言荟萃”,麦迪逊是记录。《辩论》汉语译文初版,只署“尹宣译”,再版时,要改成“尹宣译注”:我为此书写了600多条注释,构成上、下两本书的格局;注释是此书的重要内容,占有相当篇幅,说明以示负责。
我译《辩论》并为之作注时,心想:都云译者痴,谁解其中味?
现在,易中天先生至少解出两味:译笔还好,注释详尽。我觉得:遇到知音。
《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后记”接着说:“我实在忍不住要把这个故事重讲一遍,以便有更多的人来分享这种感受。”
过去,有许多人曾经把经典著作通俗化,后来,人们发现,其中不少对原著作了阉割和曲解。为此,许多先贤一再提倡:要读原著。
《辩论》一书,线索众多,彼此纵横交错,制宪代表们在四轮辩论中,又爆发出许多灵感火花,大小故事,逸闻轶事,不一而足。要想理顺,然后综合叙述,需要功力。
不少朋友劝我做个缩写本,把译文和注释中的重要内容,浓缩拉顺,讲个好故事。
我做事慢,喜欢琢磨。好在,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保护。第十条下,列举了著作权受到保护的十七个方面。
没想到易中天先生是个快手,招呼也不打,捷足先登,就著起《美国宪法的诞生》来。其实,韩愈先生早就说过:“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
通俗并非易事。我在纽约图书馆读过英文版“世界领袖”丛书。那套丛书以美国中学生为主要对象,每本百页左右。我记得读过其中近二十位美国总统传,外加汉密尔顿传。丛书的主编,是美国史学界泰斗小阿瑟・施莱辛格,他在每本书前都有的“总序”里说:作者多是研究传主的专门人才。他们深入一个人物、掌握资料太多以后,就觉得一百页不够用,许多材料舍不得丢。施莱辛格看过许多初稿,认为问题多半出在取舍不当,有时反而抓不住要领。可见,越是深入,越难浅出。
麦迪逊的作品是经典,是精品,我译时,认定它难以畅销,但必定长销,只要能在智者之间渐行渐远,哪怕藏之名山,也会存之久远。担心的就是根底不足的人,随意改编,弄得不好,通俗很容易流为庸俗,要是抵不住哗众取宠的诱惑,搞些不三不四的类比,发些似是而非的议论,可能堕为媚俗。精品可能变成赝品。
花了两天,读完《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
易中天先生的手法,是夹叙夹议。
叙述部分,即基本内容,包括情节推进、人物评介,大体从一本书中提取:《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包括译文和注释。我越读越觉得书中的词句过于熟悉:我反复推敲而成的译文,字斟句酌写出的注释,星星点点化为易中天先生的“著作”。
易中天先生把他的书称为“著作”,这就向读书界和书评界提出一个富于挑战性的问题:何谓著作?何谓改写?改写等于著作?或者,二者之间有明确界线?如果有明确界线,如何划分?或许,研究版权法的法律专业人员,会给我们一些启示。
议论部分,往往信口一开,各种各样的时髦新论,便从嘴里流淌出来,令人叹为观止:诸如“婆婆媳妇论”,“防官如防贼论”,还有“半路里杀出个程咬金”,“连环扣与防火墙”。
“我的翻译原则,是尽量避免使用汉语中的现成词语,尤其是由典故生成的汉语成语,以免不必要的思维混同。希望有助于读者把捉和品尝制宪代表发言的原汁原味。”(《辩论》,“译者例言”,第12页)
这就提出第二个问题。如果有人说:“霸王别姬肯塔基”,“李白醉卧迪斯尼”,读书界和书评界会认为这是通俗、庸俗,媚俗?还是不伦不类?还是异想天开?
易中天先生在书中提出“防官如防贼论”(《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第103页),应该是一个为了通俗化而作的比喻。但是,比喻,要贴切,要恰如其分。夸大、缩小、拐弯,都可能引起质的变化。尤其理论问题,往往“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似是而非,易生误导之弊。
现代文明社会,讲究法治。管住官员,主要用宪法;打击盗贼,主要用刑法。这是两个范畴,不能随意混淆。官不等于贼。官员即使“不作为”,也可能危害一方;盗贼如果都“不作为”,就一方太平。防官的办法,不同于防贼的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