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3年2月,记者卡尔・冯・奥西茨基在狱中服刑
1933年2月,记者卡尔・冯・奥西茨基在狱中服刑
1933年2月27日晚上,卡尔・冯・奥西茨基正在回家的路上。不久前他刚从收音机里听到国会纵火案的消
息。持续了几天的内心不安又加剧了,同时加剧的还有他双手的颤抖。
当他回到柏林家中,妻子给他开门的时候,已经十点多了。妻子紧张地问:“我们现在怎么办?”奥西茨基说:“先上床睡觉吧!”
作为知名政论报纸《世界舞台》的总编,奥西茨基已经被同一个问题困扰了一整天,那就是他是否应该同其他知识分子和作家一样离开德国。大多数朋友和同事都劝他无论如何不能再回家了,得马不停蹄地赶乘下一班火车上路。奥西茨基迟疑了。这时候他的朋友兼政友海尔穆特・冯・格拉赫却回击了别人的建议:“现在不要惊惶失措!看吧,不管怎样我都留下来!”奥西茨基于是下了决心:“那么我也留下……”
他还没到家,妻子就已经开始盘算怎么说服他一起逃走。他安慰妻子,还要再等三天。可是这番话再也没能兑现。这一夜还没过去,凌晨三点半的时候,门铃声把夫妇俩从沉睡中吵醒。妻子毛特・冯・奥西茨基问:“我们非开门不可么?”一个声音回道:“非开不可!”两个当官儿的出示了警官证,并且正式通知卡尔・冯・奥西茨基:他被逮捕了。
卡尔・冯・奥西茨基是魏玛共和国时期最著名的出版人之一,他的分析和评论文章至今令人称快。“他是一把火炬,照亮黑暗,给回家的人指引方向,驱散那些颠覆共和国的阴谋诡计。”1994年弗利茨・J.拉达茨如是评价他。
卡尔・冯・奥西茨基于1889年出生于汉堡,“一战”之后积极投身和平运动。对于魏玛共和国的弱点和纳粹的野心,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果敢无畏地针锋相对。1931年1月20日,他在《世界舞台》上发表了针对阿道夫・希特勒的文章:“一个民族到底要在精神上沦落到何种程度,才能在这个无赖身上看出一个领袖的模子,看到令人追随的人格魅力?”
由于不遗余力地为民主振臂高呼,奥西茨基成了纳粹的眼中钉。阿道夫・希特勒被任命为帝国总理还不到一个月,奥西茨基就被逮捕了。服刑的地点在柏林亚历山大广场边上的警察监狱,也就是太阳集中营,后来被叫做伊斯特维根劳动营。
在那个埃姆斯兰,荒滩和沼泽丛生。身份已经变成了562号犯人的奥西茨基其实并不适应繁重的体力劳动。他首先无法适应的是来自党卫队看守的棍棒,那些人特别“照顾”魏玛共和国的知识分子。要不是国际抵抗力量为奥西茨基颁发诺贝尔和平奖,他必死无疑。
当诺贝尔委员会于1936年11月来到埃姆斯兰,给这位声名显赫的罪犯颁发1935年诺贝尔和平奖的时候,纳粹当局迫于国际压力将奥西茨基释放。但是,那时候的奥西茨基已经是个重病缠身的垂死之人。两年后,他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还在埃姆斯兰的时候他就被这个病击垮了。
卡尔・冯・奥西茨基无疑是最勇敢无畏的德国抵抗战士。然而过了几十年以后,他才在联邦德国国内广为人知。一些人不愿接受这样的事实――奥西茨基是个彻底的民主主义者,他反对任何暴力,他是一个“反抗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战士”。后来任联邦德国总理的威利・勃兰特曾写道:“人们不应该跳过历史书上黑暗的那几页,人们更不应该放弃可资维护民主的一切借鉴。”勃兰特在纳粹期间流亡国外,也是一位抵抗战士,曾帮助过奥西茨基逃亡到挪威。
埃姆斯兰集中营的囚犯早上扛着铁锹出发,挖坟墓,掘沙山,被称做“荒原战士”。1934年诞生于博尔格荒地的《荒原战士之歌》,在上世纪30年代就已传遍世界各地。只要是揭露纳粹和法西斯罪行的地方,就听得到有人传唱。“二战”之后,这首歌成为最著名的反战歌曲。
在第三帝国从事抵抗活动的,总是那些在危急时刻为人类正义挺身而出的人。他们不与压迫者和恐怖专制当局同流,就像希尔贡特・查森豪斯那样。战后,这个汉堡女人到了美国巴尔的摩,当了一名医生。
1938年,22岁的希尔贡特・查森豪斯通过了翻译证书考试,在汉堡的信件稽查处工作。她的职责是对波兰及其他国家犹太犯人的邮件进行审查――被扣下的都是要求添加食品、衣物、药品的信件。希尔贡特・查森豪斯偏偏“阳奉阴违”,她私下保留了一批信件,在一个汉堡经纪人的协助下,满足了寄信人的要求。
由于身在政府托管部门,这位年轻的女翻译有更多工作内容。她还要审查斯堪的纳维亚犯人的邮件,另外还得在神父参观监狱时负责陪同工作。在丹麦和挪威等被占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纳粹党徒逮捕了知识分子,并将他们带到了德国北部的集中营和惩戒所。
不久,希尔贡特・查森豪斯把教授、作家、教师和律师的信件一一挑拣出来,并且指派专人送到相应的收信人手里。在人满为患的火车上,她穿梭在一个个惩戒室之间。她还通过转递信件,帮了汉堡的斯堪的纳维亚水手协会和瑞典红十字会的忙。为了防止遗漏待救者,她还制作了花名册,被登记的名字很快就超过了1000个。
战争行将结束之际,希特勒下令将全部政治犯杀掉。在希尔贡特・查森豪斯的推动下,瑞典红十字会跟希姆莱就释放斯堪的纳维亚犯人达成了协议。她的花名册起了巨大的作用。有了这个名单,尽管遍地恐怖的烟云未散,仍然有1200名犯人被成功解救。
1945年春天,希尔贡特・查森豪斯自己也身陷险境。盖世太保要把她逮捕。在纳粹倒台之前,除了隐藏起来,她别无选择。这位年轻的女士今后唯一的目标是:移民到美国去,在那里完成医科专业的学习。她再也不想回德国,再也不想回欧洲了――不过她还是回来过一两次。比如当她获得斯堪的纳维亚最高荣誉的时候:挪威的圣奥拉夫勋章和丹麦的丹布罗格勋章。
有人问她,在第三帝国时的所作所为动机何在,她的回答很简单:“那是……人之常情……当时我学到的第一点是:当你迎着风暴游泳时,你是一个人;其次:每个人都可能鼓起勇气,做出反抗。没有机会爆发,只是出于害怕和缺乏能动性。”
不得不提的还有一位闻名世界的法兰克福商人―――奥斯卡・辛德勒,他召集了一批犹太劳工到石勒苏益格的工厂做工。这样一来,他们就不必在纳粹灭绝营里等死。1992年,美国导演史蒂芬・斯皮尔伯格把这个故事拍成了电影《辛德勒名单》,使这位企业家在去世之后又成了全球知名的人物。
无独有偶,还有一部关于克鲁伯公司前董事长贝尔托德・拜茨的影片。1942年8月,拜茨当时在加里奇恩,目睹了第一批被送到灭绝营的犹太人。看到成批的人走向死亡,他震惊极了,他要尽其所能去拯救他们。
跟辛德勒的做法相似,拜茨也招收犹太劳动力,有时甚至雇用妇女和儿童。要想在纳粹当局面前找个正当理由可并不容易。一有机会他就拦火车,从车厢里把犯人直接救出来。与此同时,他的妻子不顾纳粹党卫队的重重封锁,把犹太儿童藏到了自己的屋檐下。
贝尔托德・拜茨的所做所为被盖世太保发现了。他遭人告密,险些被捕。1944年,他被招入国防军,不得不中止营救活动。以色列国后来尊称他为“人民的正义卫士”。
瑞典外交官劳尔・华伦伯格从1944年夏天起开始援救匈牙利的犹太人。这些犹太人拿到了“瑞典护照”,住在华伦柏格亲自安排的房子里。
1944年12月,苏联在布达佩斯成立了一个临时政府。他们对华伦柏格的营救行动表示十分的不信任;他们无法想象会有人从人道主义出发保护犹太人免遭集体屠杀的厄运;他们怀疑这位瑞典外交官是美国人的卧底。1945年1月,华伦柏格如约来到了苏联。军队驻扎在布达佩斯郊外的总部。此后,他便销声匿迹了。这个拯救了诸多犹太人的功臣很有可能消失在了苏联的监禁营。他的命运至今仍是个谜。
另外,还有许多逃兵把命运交给了无声的反抗。“二战”期间,国防军法官总共判处了3万余例死刑案件――数量大大高出人民法庭和其他特别审判庭。2万多起死刑奉命执行,大概只有4000逃兵死里逃生。汉堡人路德维希・鲍曼就是幸存者之一。战争期间,鲍曼作为海军二等兵驻守在法国波尔多。他和一个朋友一起逃跑,目的是为帮助法国港口工人逃往摩洛哥。在法国,鲍曼被一个德国巡关人员逮捕,后又被送交海上军事法庭。判决结果是枪决,理由如下:“临阵脱逃,在德国军队中罪大恶极。”
鲍曼的父亲借助和海军上将埃里希・雷德的关系,让他的最后判决从死刑变成了有期徒刑。战争结束前后,鲍曼在白俄罗斯的一个刑事犯集中营战斗。1945年以后,他不得不继续受审,原因是他当过逃兵。直到2002年,德国议会宣布纳粹时期的所有叛逃罪名无效,路德维希・鲍曼从此终于彻底获得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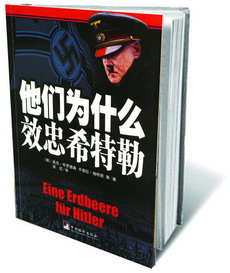
许许多多发生在那个时代的故事,那些关于勇气、民众的力量和同情的故事,都已经遗忘在昨天。残留下来的都成了“记忆文化”的一部分――这个概念通常带有贬义色彩。一个活在记忆里的民族,还有能力走出过去的阴影么?我认为不能。恰恰相反,在一个并没有完全理解纳粹主义究竟为何物的形势之下,关注已经过去了的和现在正发生着的无疑都是形势所需。
纵然如此,我们还是创造过一些成功的经验。比如,在我的家乡埃姆斯兰,人们对第三帝国历史的反思做得非常周到。在帕彭堡还成立了一个由官方支持的埃姆斯兰集中营资料信息中心(DIZ)。这里不仅经常把从前的集中营营民和荒原战士汇聚到一起,而且还吸引了德国与荷兰边界地区的中小学生以及青年人的关注。
DIZ是个活跃的集散地。到这里来的人不光是为了履行玛格丽特・米彻里希和亚历山大・米彻里希的“哀悼工作”,更是为了把了解历史当做通向现实以及未来欧洲统一的必经之路,从而不再重蹈过去可怕的覆辙。
(本文摘自《他们为什么效忠希特勒》,[德]英克・布罗德森、卡洛拉・施特恩等著,安尼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定价:29.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