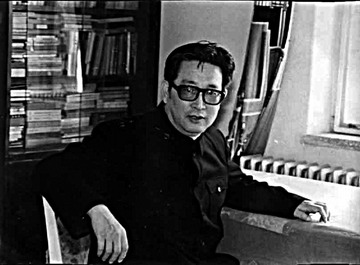 每当枝青叶绿时节,我就倍加思念我的良师益友刘绍棠。特别是近来,在纪念刘绍棠逝世10周年的日子里,这种思念之情变得尤为炽烈。我反复激动而甜蜜地
每当枝青叶绿时节,我就倍加思念我的良师益友刘绍棠。特别是近来,在纪念刘绍棠逝世10周年的日子里,这种思念之情变得尤为炽烈。我反复激动而甜蜜地
在如此漫长的岁月里,我去过绍棠家多少次?我实在是记不清了。特别是在1988年8月5日他中风左体偏瘫以后,为了刘绍棠乡土文学研究会的工作和写好《刘绍棠传》,去的次数就更多了,差不多每7-10天我们就要在一起聊上一、两个小时,一周之内碰面两次,也是常有的事。
绍棠是个把心挂在胸膛外边的人,讲起话来滔滔不绝,我们俩交谈大多时候都是我听他讲,我觉得他的脑子简直就是一个活电脑。每次谈话,对于我来说都是极好的一课,无论是谈文艺,还是论人生说世情,都给予我莫大的启迪,而几次关于他辞官不就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关于文人不能当官儿,也不可当官儿的话题,更是使我的心弦受到强烈的震颤。那一句句语重心长、极富真知灼见的话语,是我一辈子都要铭记在心的。
记得是1984年6月下旬的一天,我和绍棠应邀到新侨饭店出席中国作协召开的欢迎南斯拉夫作家代表团招待会。我们是乘坐103路无轨电车从府右街去新侨饭店的。路上,绍棠的心情不像平时那样平静,小声地对我说:“可能要给我个官儿当,这事你看行吗?”我知道这是只对知心朋友才能讲的话,因此颇为兴奋,十分认真地回答:“那好嘛!这是件好事,至少能说明有关领导对你有公道的看法,我看可以考虑。”绍棠轻轻地扬眉笑着说:“一当官儿,写小说可就要泡汤了。”我接过他的话说:“未必是那样,别人能干只挂名不出力的事,你为什么不可以也试一试?”绍棠仿佛很有感触地说:“当官儿也能当出官儿瘾,一个作家一旦染上官儿瘾,创作就很难说了……”停片刻,他又转过身来,好像下了决心似地补充说:“不行,还是不能干……”那次在103路无轨电车上关于他是否当官儿的话,说到那儿就结束了。至于有关方面要给他个什么官儿当,他没有说明,我也没有问。但从他的表情和心理活动看,我猜测一定是个很重要的职务。这里要说明的是,不管官儿大或是官儿小,反正他是一概都不想当,他怕从政影响创作,当不了职业文人。这一点我是耳闻目睹,完全可以作证的。
一个月后,绍棠给老首长(即胡耀邦同志)写了一封辞官不就的信,坦诚地阐释了他不肯当官儿,一心想在野从文的志向:“您(指胡耀邦同志)打算用我,不过是因为我是您从小看着长大的,使唤起来顺手。如果我在工作中跟您发生分歧,连几十年的交情都耽搁了。”“从政不如从文,在朝不如在野”;“什么员我都敢当,什么长我也当不了。哪怕是只管两个人的小组长,我也当不好。”
因为绍棠自青少年时代起就是一个中外闻名的神童、才子,具有同辈作家不可相比的广泛影响,所以,上级总是时不时地想给他安排个官儿当,直到他中风偏瘫前3个月,即1988年5月,北京市的几位领导还邀请他出任主管北京市文化工作的副市长。对此绍棠依然是毫不动心,对他们的好意依然婉谢不就。婉谢不成,便代之以戏耍,说:“你们叫我当官儿,那就叫我当主管房子的副市长,我要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可见,绍棠确确实实是不愿当官儿,而把写小说视为压倒一切的神圣使命,甚至比生命还要重要。
在与绍棠长期的交往中,我发现,不要因为从政而耽搁写小说固然是他辞官不就最重要的原因,不过,渊博的历史知识和丰富的社会阅历使他对文人当官儿弊多益少有深刻的了解,了解这一点,也是打开他决不受任何诱惑,一心固守文学家园的心灵秘密之门的一把钥匙。他曾大动感情地掏心窝子:“释迦牟尼在后宫见识的女人太多了,才跑出去当了与女人绝缘的‘和尚’。我16岁就接触官场,官场情态见识得多了,也就产生了不可从政的自知之明。文人犯官迷,古已有之。孔、孟都有官瘾,李(白)杜(甫)官欲甚炽。现代文人中,周作人卖国求荣,认贼作父,不过当了个‘副部级’(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号称创造社‘四君子’之一的三角文人张资平为当个汪伪政权的地矿部司长而附逆。卖身周、张都可耻、可鄙!在国民党那里,文人当特务的大有人在,当大官儿的难得(陈布雷其实是个秉笔‘太监’)。所以,我认定,文人不能当官儿,不可当官儿。屈原的下场太惨。司马迁那个‘秘书长’(中书令),付出的代价太大。”(《且说“大官人”》)
基于这种认识,绍棠给犯了官瘾的官迷们勾画出一幅丑态百出、面目可悲又可笑的漫画:“官瘾大于财迷,甚于色欲,烈于吸毒,也严重污染了知识分子。”(《何日可见三秋树》)而对某些只尊崇大官,瞧不起专家、学者的新潮人士的嘲讽,又是多么尖刻辛辣、发人深省:“令我大惑不解的对官位、官职、官衔、官称最为尊崇叩拜的却是新潮人士。有位以新潮著称的记者,采访一位女部长,竟然问人家:‘您当上了部长,但您的丈夫才是个院士,难道您不觉得心理不平衡吗?’女部长咯咯笑起来,说:‘我这个官儿,他还瞧不上(看不起)哩!’女部长还说她平日一直给丈夫做饭,退休之后还要兼当打字员。这位女部长年近60,50年代中专毕业,思想多么‘陈旧’,竟然认为部长诚可贵,院士价更高,‘妻以夫荣’而甘愿‘夫唱妇随’。在我们那位新潮记者心目中,部长了不起,院士算老几?女部长嫁男院士,跌份又栽面儿。恕我嘴损,我怎么从新潮中嗅出了泔水味?也许是环境污染所致,恐怕要送高碑店污水处理厂转化一下。”(见《四类手记》第538页)
绍棠与朋友交往,从不以官职大小、地位高低定厚薄,而是以人的品德、情操、志向作准则。他敢在大厅广众之中指名道姓地严厉批评北京市领导忽视运河污水治理造成的巨大损失,他也能与素不相识的街头理发员侃侃而谈,结为朋友,并进而为以这位理发员为代表的百分之十七的低收入群众著文代言,大声发出“我们不否认中国还是个发展中的穷国,那么就不能不承认穷国里面穷人多。治穷,或曰脱贫,才是万事最当先的任务”的呼喊。
绍棠担任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委员13载,但他从来不把自己看作官儿,而认为是为人民群众代言的勤务员。原来与他肩膀差不多一般高的人当了官儿,他毫无妒忌之心。18年中,他与我交谈的次数那么多,可从来未说过人家一个不字,相反,倒是时刻不忘少年时代的友情,建议有关方面出面唱一出八仙请寿,重整队伍再振少年行。当然,他也从来不认为自己比人家矮了一寸。他身兼的会长、顾问、名誉主编等头衔有一大堆,究竟有多少个,自己怎么也说不清,压根儿他就没统计过。他不认为这些称号给自己增加了多少砝码,只当作自己为别人、别的单位应尽社会义务的信号。他常对我说:“这些头衔、称号只能说明人家需要我刘绍棠出点力,那我就尽力而为之吧,何必费脑筋去记住这些头衔、称号呢!”
写到此处,我不由得想起1996年年底在第五次作代会上他被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时异常平静的心态。实事求是地说,作协副主席并不是一种握有实权的真正的官儿。不过,它至少可以标志作家的文学成就和读者对其认同、拥戴的程度。按照我的想象,这总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我作为绍棠晚年最信任的朋友之一和刘绍棠乡土文学研究会的负责人,他事后总会对我透露一点信息吧?可他没有这样做。这一消息最早我还是从我原来的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得知的。我带着这一喜讯,兴冲冲地到绍棠家为他祝贺并不无戏谑地“指责”他为什么对我封锁消息。他谦和地微微一笑,依然像18年前我们初次相会时长兄对幼弟讲话那样真诚地说:“这算什么!对一个作家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写出群众欢迎,经得起历史风雨考验的作品,至于挂个什么头衔,那都是很虚的东西,不必看得很重。通县人民政府授予我的‘人民作家光耀乡土’荣誉牌,才是最重要的。再说啦,对我这个人向来就有争议,我十几岁一登上文坛就是这样,当今新潮肆行,反对我的人,咒骂我的人依然存在,将来说不定还会有人往我头上再扣屎盆子呢!”我提议请志同道合的伙伴聚一聚,庆贺庆贺,他严肃但并无批评之意地笑着说:“不用,不用,你的好意我明白。”
绍棠面对喜事这种平静的心态,让我感到他比以前更成熟、更老练了。此时此刻,我不由得又想起他少年得志时对党讲的“我,一个直接由党栽培起来的青年,即使有星星点点的成绩,也都是渗透着党的心血的;因此我没有任何理由骄傲自满。”(《青枝绿叶》前记);也想起1958年春天,他被错划成“右派”,沦落乡野时立下的“莫因逆境生悲感,且把从前当死看”的誓言和在荒屋寒舍土炕上写出《地火》《春草》《狼烟》三部长篇的奇迹;更想起1979年1月党组织为他平反昭雪后,他一不喊冤叫屈,二不讨价还价,而是“要从2l岁开始,加倍努力为党的事业奋斗,为祖国和人民效力,为社会主义文学劳作,来弥补我21年创作生命的空白”(《让我从21岁开始……》)的高度党性……想起这些,我们特别崇敬的孙犁同志20多年以前讲过的那段论情操的话,顿时又涌上心头:“人之一生,或是作家一生,要能经受得清苦和寂寞,经受得污蔑和凌辱。要之,在这条道路上,冷也能安得,热也能处得,风里也来得,雨里也去得。历史上,到头来退却的,或者说是敛迹的,常常不是坚定的战士,而是那些跳梁小丑。”(《贾平凹散文集序》)我要欣慰骄傲地告诉天上有灵、地下有知的绍棠兄,孙犁老师对情操的要求,你是真正地做到了,你不愧是孙犁老师厚爱的学生。
绍棠毫无官欲,当然就不会与别人争官儿当,比如他对描写农村题材的四小名旦之一浩然(绍棠称孙犁、赵树理、柳青、周立波为描写农村题材的四大名旦,笔者称刘绍棠、马烽、李准、浩然为四小名旦)理解、关心、尊重的友善态度,就是一个极好的说明。浩然走背字时,尚未得到正式平反的绍棠,就亲自登门拜访他,鼓励他振作精神,为未来写作。浩然写出新的力作《苍生》,绍棠亲临作品讨论会,为浩然创作的新收获击节喝彩,作了长篇热情洋溢的发言。浩然在三河县筑起“泥土巢”,办起“泥土文学工程”,绍棠予以大力支持,让自己最得意的学生倪勤拿着成功的中篇小说到浩然的泥土文学队伍里加盟。浩然中风后,绍棠多次在笔者面前表示对文友的关心,并两次委托我到三河看望、慰问浩然这位老实巴交的“咱们农民的一支笔”。对浩然的文学成就,绍棠由衷地佩服,写下了《我说浩然》一篇见解精辟、深邃的美文,称浩然“在生活阅历上比自己丰富深刻得多”。绍棠还说:“李准和浩然,对农民在整体上比我了解得透彻。”绍棠一生写了一千多篇杂感、随笔(笔者称其为绍棠千字文),这篇《我说浩然》被绍棠选入几个集子里。最后,在精选的总数只有200篇文章的《刘绍棠文集》杂感、随笔卷中,又依然选了这一篇,可见绍棠对浩然是多么尊重!
绍棠对浩然情深,浩然对绍棠自然也就义重。1992年5月27日,通县档案馆“刘绍棠文库”揭幕,浩然高兴地从三河赶到通州为绍棠祝贺。1997年3月12日,绍棠驾鹤西行,浩然当天就写了题为《刘绍棠走了》的悼文,亲自送到《北京晚报》发表,对绍棠过早地逝世,表达了“悲痛万分”的深情,还说绍棠和其他同志对他的关爱之情“对他鼓起生活和写作的勇气,起了决定性的作用”。2000年5月,“纪念刘绍棠逝世3周年暨乡土文学讨论会”在通州运河苑度假村隆重举行,浩然身患重病,但依然应邀抵通州参加盛会以表贺意和对绍棠的思念之情。
这一件件活生生的感人肺腑的事实,都充分地显示出刘绍棠和浩然这两位农家子弟出身的泥土作家心地的宽厚与善良。他们彼此的关系是非常友善和谐的。
众所周知,绍棠自1988年8月5日左体中风偏瘫以后,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仍以难以想象的毅力日夜兼程,拼命坚持写作。1996年4月又患上肝腹水、肝硬化的重病。但是,视写作贵于生命的绍棠,仍然本着“活着是为了干活”的信条,完成了长篇小说《村妇》(第一都),整理编辑出10卷的《刘绍棠文集・大运河乡土文学体系》。直到逝世的前5天,他还和我一起商量为北京一位业余作者的小说《北京女人》召开研讨会的事,一句话,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绍棠还在顽强地拼命地固守着他的文学阵地,在为文学新人操心,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为毫无兴趣的事劳心分神,哪里还会去和他人争什么呢!著名作家苏叔阳说:“绍棠被评为写作战线上的劳动模范是当之无愧的”,“他是累死的”话是公道的,是符合客观实际情况的。
面对绍棠关于文人不能当官儿、不可当官儿的精湛评说和他采取的明智做法,以及60多种总计近700万字风格独具、脍炙人口的作品,我常常暗暗思忖:绍棠虽幼年成名,人称卓异,但真正用于创作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反右之前不足6年,不久便丧失了创作权利,白白耽搁了21年的宝贵时光。平反昭雪后,着实风风火火地大干了一阵子,可是,总共也未超过10年,紧接着就中风偏瘫,成了半倒体,一张稿纸写不满都要累得大汗淋漓。那么,最终他为什么能拿出那么多深受读者青睐的精品佳作,成为蜚声海内外的多产、优产、稳产的文学大家呢?我想,除生活积累深厚,天资聪颖又勤奋努力等因素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不管多么顺利、走红,也不头脑发晕飘飘然,更不被高官的桂冠所诱惑,而是始终在文学这条崎岖而艰险的小径上毫不动摇地向着既定的目标不懈地跋涉,不达到目的绝不罢休。文场上有的人刚刚小荷才露尖尖角,就被领导看中,匆匆戴上乌纱帽。但因不懂得官场的道行,屁股尚未坐稳就惨然落马,从此丢掉了老本行。这样的事例是屡见不鲜的。还有的人,才气确实不低,不幸的是染上了官瘾,成为官迷,认为唯有走上仕途,才会使自己前程似锦闪闪亮,于是,便施展出十八般武艺挤进官场。可是,哪里晓得,从政从文是截然不同的两个行道,感情用事成性的文人,是根本学不会当官人必须要掌握的要领的,因此,终因不得要领尚未在官场上像样的风光风光,便灰溜溜的败下阵来,落了个赔了夫人又折兵的下场。而绍棠却与这些人士迥然不同。看透了官场情态又深知自己缺乏为官的细胞和脾气秉性的绍棠,早已有了不能从政、不可从政的自知之明,因此便断然辞官不就,做了个天下头号“大傻人”,决心终生在野从文,专心致志地写大运河。绍棠犹如一个梗着脖子的村夫,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全神贯注耕耘着他那乡土文学的一亩三分地,终于获得好年景,那丰硕的果实堆成了一座金山。可见,一个作家只有真正以文学创作为最崇高的天职,才是正道。大多数作家如果真的都是这样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学事业才会大有希望。这就是终生不走仕途的完整职业文人刘绍棠身后给我们留下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作者系刘绍棠乡土文学研究会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