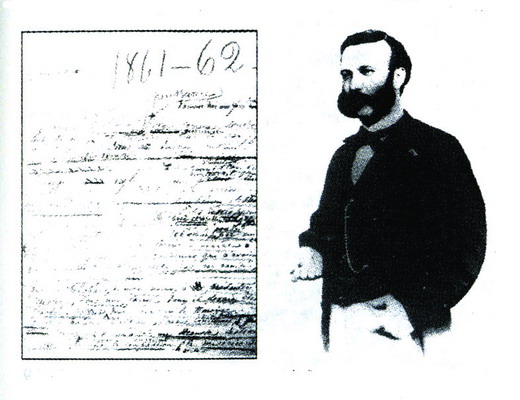 迪南和回忆录手稿
迪南和回忆录手稿
 描写这场战
描写这场战
役的画
出生在富豪之家,死在济贫院里;商业上取得过极大的成功,却又因破产而一文不名;一度名声赫赫,一度又默默无闻;曾是瑞士社交界的明星,后来实际上从那里被放逐;终生对荣誉一无所求,却给送来一顶顶桂冠。这些都发生在让・昂利・迪南(Jean Henri Dunant,1828-1910),一位首次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的身上,因此也就可能算得上是历史上最强烈的对比了。
世界之大,历史之久,留下来的回忆作品,何止千万,就作者的地位说,有英国首相温斯顿・邱吉尔爵士获1953年诺贝尔文学奖那通称“战争回忆录”的巨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回忆的坦诚说,有古罗马哲学家圣奥古斯丁、法国作家让-雅克・卢梭和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三大《忏悔录》;就记录社会生活的广泛性说,有法国外交家和作家法朗索瓦-夏多布里昂的《墓畔回忆录》;就史料珍贵说,有古希腊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等等。可能没有哪一部“回忆”所产生的影响能与昂利・迪南的那本薄薄的小册子《回忆索尔费里诺》相比。
索尔费里诺(Solferino)不过是意大利北部伦巴第地区境内卡斯蒂维耶雷堡(Castiglionedella Stiviere)东南大约六公里处的一个小镇,只因第二次意大利独立战争中,奥地利军队和法国西北部得到法国援助的皮埃蒙特区(Piedmont)的军队在这里发生过一场激烈的浴血战斗,使这个小镇顷刻之间便名闻全球,而且永远被记入史册。
那是1859年的6月24日。奥地利军队大约12万人在意大利伦巴第地区的马真塔(Magenta)一战中被击败后,向东撤退,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一世亲临前线指挥。法国-皮埃蒙特联军的兵力与奥地利军队的兵力几近相当。于是,拿破仑三世和撒丁-皮埃蒙特国王伊曼纽尔二世也共同指挥自己的军队,去穷追奥军。最后两军就在6月24日这天在索尔费里诺正面遭遇。
这是一场未经策划的战斗,结局取决于对加尔达湖(Lake Garda)南侧丘陵的控制。正面遭遇后,法军为突破奥军的中路,不惜付出巨大的代价;而奥军则采用拖延战术,使法国-皮埃蒙特军队精疲力竭,无法穷追。这也是一次在异常酷热的天气里进行的战斗,持续时间只不过15个小时,但给双方造成的伤亡都十分惨重:奥地利军队固然死伤14000人,失踪和被俘8000人,法国-皮埃蒙特军队也伤亡15000人,失踪、被俘2000余人。这天,昂利・迪南为寻求拿破仑三世,正好找到那里,并目睹了这么“一场可怕的肉搏战”。
昂利・迪南出身于瑞士日内瓦的贵族家庭。信仰基督教、富有强烈的慈善、人道和博爱情怀的双亲教导他要尊重和帮助需要他的人。从小,他就常陪母亲去日内瓦幽暗的街区和郊外看望穷人和患病的人,毫不吝啬地将自己的财产施舍给他们。他后来多次回忆起这初次对不幸和苦难的接触,让母亲的热情一直伴随他的一生。
成年之后,迪南在从事作为一位商人兼银行家的业务的同时,仿效伦敦商人乔治・威廉斯(Sir George,1821-1905)1844年在英国成立的“基督教青年会”组织,发起在日内瓦成立“基督教青年会联盟”(Young Men’s Christian Union)。这组织后来扩展到了欧洲和海外。
自从1830年阿尔及利亚被法国征服之后,欧洲许多冒险家都去那里寻求运气。迪南也有类似的意向:从1853到1859年,富有的日内瓦市民为他提供资金,让他去那里扩展谷物和大理石业务。这符合阿尔及利亚发展工农业的利益。为便于工作的开展,迪南要求有一个法国公民的身份,当时遭到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官僚的干扰。于是,迪南想到了拿破仑三世(Napoléon Ⅲ,1808-1873),因为这位“令人畏惧,受人尊敬,又深得人心”的法国皇帝,曾热衷于兴办公共事业,加快铁路建设,促进工农业发展,使法国获得20年的繁荣;阿尔及利亚作为法国的殖民地,他相信,这位开明的、爱护百姓的皇帝是不会不关心的。于是他决定直接去向他求助。
当迪南来到索尔费里诺战地时,展现在他面前的是数万人的尸体和大量的伤者,其中不少正处于垂死状态,这使迪南受到深深的震撼。
随后,他去找了拿破仑三世,说服他给他的士兵下一道命令:“无条件释放在奥地利军队中被俘的内科医生和外科医生,那些在索尔费里诺战役中受伤和在卡斯蒂维耶雷堡医院濒临死亡的人应该根据他们的要求,允许他们回奥地利。”
在此后的两三年里,迪南的心灵始终无法平静,促使他决心要把他自己的这一经历和感受写出来。
1862年,迪南的一本题为《回忆索尔费里诺》(Un Souvenirde Solferino)的书自费出版。
《回忆》的内容大致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介绍战争发生的过程;第二部分是描写战役结束后战场上的情景:“混乱不堪,难以描述的绝望,和各种各样的惨状”,讲述了在卡斯蒂维耶雷堡救助伤员的几个故事;第三部分是他自己在回忆了这场战役之后产生的一些设想。
迪南回忆说,他当时亲眼目睹到的是这样的一场异常可怕的肉搏战:
“……奥地利和法、意联军相互践踏着,在血淋淋的尸体上你拚我杀,他们毫不留情地用步枪射击对方,用刀劈向敌人的头颅,刺入敌人的胸膛。这完全是一场屠杀,是残暴的野兽之战……”
“枪炮散落在死伤者的身上,脑浆在车轮下涌出,四肢断裂,血肉横飞,人体被残害得难以辨认出原来的模样,泥土混拌着鲜血,尸横遍野,惨不忍睹……”
在这样的时刻,面对这样的惨景,迪南把自己的事丢到脑后去了。他首先想到的是要立即救护伤员,因为在那个时候,为军队的医疗服务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于是,迪南设法将当地的居民、神父和旅行到这里的人以及所有愿意来服务的人,组织起一个个看护队,把数以千计的伤员安顿进教堂、学校和民房里,慰劳他们,并给他们包扎伤口和喂食,使整个城镇都变成一个临时医院。他回忆说:
“……不一会儿,一个志愿救助队就组织起来了,伦巴第地区的妇女们首先照顾的是那些哭喊声最响的伤兵……我力图尽我最大的努力在需要的地方组织救护,那里有500名伤兵堆在教堂里,妇女们进了教堂,用盛满水的罐子和军人用的餐具一个挨一个地给军人们解渴,并湿润他们的伤口……她们的温柔和善良,她们那眼泪汪汪、充满同情的样子以及精心的照料,使一些伤员恢复了精神。”
但是,“也有一些受伤的奥地利俘虏抱有怀疑,不肯接受帮助,把绷带撕下,致使肌肉血流不止。一个克罗地亚人将一颗刚从他的伤口取出的子弹掷在外科医生的脸上。其他的则面有愠色,沉默寡言,表情冷漠。他们多数都缺乏拉丁民族所具有的开朗、愉快、乐观和活泼、友好的表情。”
“不过,”迪南指出,“对于(救助者的)仁慈,多数儿也都没有毫不领情和抵制的表现,在他们的脸上或许还可以看到真诚的感激。有一个19岁的孩子,跟他们国家的大约40个人一起呆在教堂最偏远的一个角落里,已经三天没有吃东西了。他失去了一只眼睛,正因寒热在发抖,无法说话,甚至没有力气喝一点点汤。但是我们的护理帮助他恢复了生命,在24小时后可以让他回(意大利的)布雷西亚去。他很难过,几乎是带着悲伤离开我们的。在他保留下来的那一只美丽蓝色眼睛里,是一种真正的深沉的感激,用他的唇深深地吻那些卡斯蒂维耶雷堡慈善妇女的手。”
志愿者们和伤员们让迪南深受感动的事很多。他忘不了有一名修女,当她得知有一个伤兵因为自己受了伤无法像以往那样寄钱给他所奉养的老母亲而痛苦流泪时,她便将自己仅有的五法郎硬币寄给了他那位远在法国的亲人;一位伯爵夫人听说此事后,也想给他和他母亲一笔钱。但是这位伤员却不愿收下,因为他想到还有比他更加困难的人。更使迪南感动不已的是,有一位女士,当她得知一名处在垂危之中的伤员希望在死之前吻一下他母亲时,她就立刻坐火车前往他的家,将他的母亲带来,并留给他年迈的父亲2000法郎。六天后,这两位母子得以见面时,他们互相紧紧拥抱在一起,一面深深祝福他们的这位恩人……
只是迪南并没有仅仅停留在这些事件本身的记述上,他是想得更远了。在书中,他先是这样设问:“为什么我要把这些痛苦悲伤的情景告诉读者,唤起他们的痛楚?为什么我会心甘情愿地呆在那些令人心痛的地方?为什么我要拼命真实地描绘出那些细节呢?”
迪南以他的远见预测,人类不可能完全避免战争,而在未来的战争中,甚至会有更可怕的武器被发明出来,因此将会更加残酷。为了防止他在索尔费里诺战役中亲眼目睹的这类互相残杀和因为没有医疗护理而悲惨死亡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场景重新出现,他随后就以自己对上述疑问的回答,提出一项设想――他的一个宏伟的理想:“在和平安定的时期成立一些救护团体,让那些热心、忠实并完全可以胜任的志愿者为战时的伤员服务,这难道不可能实现吗?”
迪南这设想或理想,主要是:建议各国成立救护团体,和平时期为志愿人员培训救护技能,战时为伤员服务;制定一部神圣不可侵犯的国际公约,使伤员和救护人员在战争中被视为中立受到法律保护。
迪南的这本小册子仅仅只有几万字,但出版后立即被译成德国、意大利、瑞典等多种文字,并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震荡。法国大作家维克多・雨果说自己深深被迪南的书所感动,给他写信,说“我要向您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另两位以其《日记》而闻名的法国作家埃德蒙和茹尔・龚古尔兄弟称赞他是“一个以一本书结束了诅咒的战争的人”,这书“比荷马的诗要优美一千倍”;著名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欧内斯特・勒南也给迪南写信,称颂他说:“你创作了本世纪最伟大的作品。”因三年前创建了世界上第一所护士学校而被认为是护理学先驱的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向迪南表示,要积极支持他的倡议。还有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耶路撒冷的宗教界首领圣约翰长老都保证支持迪南提出的建立一个国际性机构的理想;还有萨克森王国的国王和亲身参加索尔费里诺战斗的拿破仑三世,也都许诺愿尽自己的一切可能给予帮助。这使迪南有信心具体行动起来。
1862年,迪南给“日内瓦公共福利协会”(Societe Genevoised’Utilite Publique,the Geneva Public Welfare Society)主席居斯塔夫・穆尼埃(Gustave Moynier)寄去一册《回忆索尔费里诺》。读过书后,穆尼埃立即前来看望迪南,邀请他参加“日内瓦公共福利协会”于1863年2月9日召开的一次特别会议。在会上,迪南向14位与会者阐明他希望建立一个派遣志愿护理人员去战地服务的国际组织,并希望改善转送伤员和使他们在陆军医院受到看护的一些做法。
在这次会议后,决定建立“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the Relief of Wounded Combatants),由曾经担任过联邦军统帅的纪尧姆・昂利・迪富尔将军(GeneralHenriDufour)任主席,迪南和托马斯・莫奴埃医生(Dr.Thomas Maunoir)、居斯塔夫・穆尼埃和路易・阿皮亚医生(Dr.Louis Appia)四人同意任委员会委员。这个委员会就是“国际红十字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的前身。
1864年,委员会五人在日内瓦组织了一次由13个国家代表参加的国际会议,讨论如何更“人道”的救护工作。于是在8月22日会议结束那天,代表们签署了《日内瓦公约》(Geneva Convention),规定一切治疗伤病员的组织及其工作人员有免除被占、被俘或被破坏的权利;一切参加战斗者应得到公平的待遇和治疗;援助伤员的平民应受到保护;公认白底红十字作为识别公约涉及的人员和装备的标志。
《公约》很快就获得许多国家的赞同,先是比利时、丹麦、法国、意大利、荷兰、瑞典、挪威、西班牙和瑞士在1864年,随后是英国(1865)、普鲁士(1865)、希腊(1865)、土耳其(1865)……都批准了这一公约。如今几乎世界所有国家都赞同公约的要求。迪南因致力于人道救护的红十字组织,忽视了银行的经营,以致于1867年10月陷入破产。此时起,他就离开了日内瓦,在众人中失去踪影,而单独在巴黎贫民窟过着极其困苦的生活,甚至常因付不起房租而在火车站的长凳上过夜。1870年7月普法战争发生时,迪南又从贫民窟出来,宣传红十字的人道原则:改善战俘待遇,提倡裁军和国际仲裁,受到人们的尊重。但是从1875年起,他又再次从视界消失,且整整有15年时间都下落不明,被看成是一个传奇人物。1890年,迪南虽然已有62岁,仍在瑞士的小镇海登(Heiden)为老年人创办了一所济贫院,而这时的他,却患着妄想症。五年后,当他自己也成为这所济贫院的病人时,他被瑞士的一位新闻记者“重新发现”。在与他会见之后,这位记者撰文,称他是“一个贫穷、遭到抛弃但却丝毫也不灰心沮丧、痛苦深重的人,……对世界一无所求。”但是,尽管迪南对一切都没有任何要求,荣誉仍不断地来到他的面前。1901年,这位“一无所求”的人作为红十字会的创始人,与法国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帕西(Frederic Passy)一起,同被授予第一届诺贝尔和平奖。与此同时,他还得到其它许多荣誉。
迪南在82岁那年去世,正像他生前所说的,他完全不在乎许多受惠于他的战争蒙难者都还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他的理想,无疑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道主义成就之一的红十字会,在他死后发展得异常迅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