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初,我读到了赫拉巴尔的小说《过于喧嚣的孤独》。这部并不太长的中篇小说把我吓着了。如是阅读感受一方面说明我的阅读空间逼仄,阅读品质浮皮,阅读空项太多,因而少见多怪,一方面也说明,“喧嚣”本身确有夺人之魅。
从那时开始,隔三差五,只要在书店看见,我总会买下一两本“喧嚣”,分送给爱好
此外,“赫拉巴尔”这个陌生的名字也开始成为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逢人必说的话题,我甚至会像一个热情的产品推销员那样当众炫技,朗声背诵“喧嚣”让我过目难忘的首段:
“三十五年了,我置身在废纸堆中,这是我的lovestory。三十五年中我的身上蹭满了文字,俨然成了一本百科辞典……三十五年来我同自己、同周围的世界相处和谐,因为我读书的时候,实际上不是读而是把美丽的词句含在嘴里,嘬糖果似地嘬着,品烈酒似地一小口一小口地呷着,直到那词句像酒精一样溶解在我的身体里,不仅渗透我的大脑和心灵,而且在我的血管中奔腾,冲击到我每根血管的末梢……”
在赫拉巴尔之前,关于捷克文学,我大概只知道两个名字和两部小说,一是哈谢克和他的《好兵帅克》,一是昆德拉和他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没想到,跟随赫拉巴尔,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作品》随后也被引进出版。这样,继《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过于喧嚣的孤独》之后,我又读到克里玛的《真话游戏》等作品。
据说,米兰・昆德拉、赫拉巴尔、克里玛被称为捷克文学的“三驾马车”,可阅读告诉我,这种“三驾马车”之喻,其实只是一种“方便叙事”策略,以我的阅读经验而论,这三位并不一样。
米兰・昆德拉小说的主色在于其小说的高度形而上;克里玛小说的特色,则在于他对于生活琐碎以及日常经验的高度关注,他的小说《三个对话》里,无数凡俗碎片连缀在一起,几乎穷尽了人生琐碎、庸常、沮丧、无助的一切;而赫拉巴尔小说的特色则在于擅长将荒谬人生高度戏剧化……
昆德拉、赫拉巴尔两位好像是一出大戏中的男一号,站在舞台中央的聚光灯下,大段大段滔滔不绝地说着台词,而克里玛则站在舞台侧幕的昏暗里专注于匪兵甲、匪兵乙、群众若干……有的小角色甚至连一句台词也没有。“三驾马车”所处大的历史背景几近相同,可正如光线折射时不同物体会生成不同的反光一样,在三位作家的作品里,人性的呈现各有侧重。
有评论说,捷克作家是东欧作家中很有个性的一群异类。在捷克人性格中,一直有一种嘴上服输、心里绝不服输的禀性……可在表现这种捷克性格时,三位作家写出的,是完全不同的挑衅和反抗:昆德拉的小说像刀子,赫拉巴尔的小说像石头,而克里玛的小说则好比一把沙子。赫的石头砸向粗鄙而诗意的人性,而克的沙子则被撒到了不少诗人笔下甜美的生活蛋糕上,让人不知如何是好。
再后来,我陆续又读过赫拉巴尔的《巴比代尔》、《我是谁》、《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林中小屋》、《新生活》、《婚宴》等作品,直至最新出版的传记体长篇小说《河畔小屋》。阅读这些作品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我不断修正对赫拉巴尔粗陋、肤浅理解的过程。
迷恋“喧嚣”时,我曾将小说中的主人公汉嘉理解为“工人”、“酒鬼”、“书迷”三位一体的一位诗人,而将其通篇一气呵成的独角戏般絮絮叨叨的漫长独白拆解为由高音(诗歌)、中音(哲学)、低音(自传)组合而成的一个协奏曲……
这类解读沉浸在文本中,迷醉在文辞中,却忽视了由历史的风雨所构筑而成的环境、心境和语境,忽视了作者笔下那些卑微平凡小人物与历史、政治更迭等之间的隐秘连线。
而当我们可能在这些小人物身后还原出捷克民族所历经的控制与压迫、动乱与掠夺之类斑斓昏昧的背景后,弱如草芥的“帅克”乃至“汉嘉”们既坚韧悠游又近乎痴傻的个性乃至生活态度,才可能洇渗出比文辞、文本本身更斑斓、更深邃的内容,正如汉嘉博士身份的打包工生涯乃至其荒谬乖违的命运如果不是面对苍莽无涯的非理性时代,岂不更应该被理解为一种做秀?
在《河畔小屋》的第二部《甜甜的忧伤》的开篇部分,赫拉巴尔不惜笔墨,详尽描述他小时的一个“刺青”事件。在那个事件里,渴望也像装卸工人那样在自己的胸口刺上一艘帆船的赫拉巴尔被人愚弄了,最终刺到他胸口上的,是一条裸体美人鱼。
这则童年往事当然可以被解读为一则趣事,可其实,在它里面,也包含着此后作者一生的命运密码。
“他在胸口和手臂上都刺了美人鱼、锚和帆船。有一艘帆船让我喜欢得恨不能在我自己的胸脯上也立刻刺上一艘。我仿佛已经预感到这艘小船在我的胸脯上扬起风帆。今天我鼓起了勇气对那个运沙工说:‘您身上的这只小船是一辈子都洗不掉了吗?’”
是,是一辈子都洗不掉了!因为如此南辕北辙、覆水难收、荒谬怪诞,正是生活的真谛。你要的是风帆饱胀的一只船,它却错位地非给你一条鱼,直至变异为后来的“巴比代尔”……不过,就算被扔进垃圾堆、废纸站、水泥厂,在赫拉巴尔心中,透过“灵感钻石眼孔”,永远有一个可以畅想的世界――那里有着汪洋大海般美丽的幻境,有着无数神奇与美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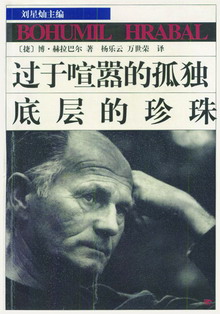
“我像塞内加一样,像苏格拉底一样,我选择了倒在我的压力机里,倒在我的地下室,也就是说在这里升天,虽然压板已在挤压我缩在下巴底下的双腿和其他部位,我拒绝被赶出我的天堂……一个书角顶着我的一根肋骨,我不由得呻吟起来,我仿佛注定要在自己制造的刑具上认识最后的真理,压板像一把儿童折刀在朝我阖拢……”
重读如上,我发现这一幕其实并非悲剧,也完全不是几年前我认定的所谓人世最黑暗的低谷,相反,它其实是一个开始进入天堂的时刻。
彼时彼刻,笼罩全书、面对世代递移、科技更替、文明变迁、价值扭转的兴叹、反讽开始变奏为一曲繁复而响亮的合唱:无论世道如何,他始终坚信着人类文明的精华,并始终诚恳着斑斓丰美的精神生活。
它当然就是卑微人生叹息缭绕无垠的最后一阙,可它并不凄凉,因为汉嘉即将抵达的那个天堂并不迷惘――有被他战战兢兢深情挑拣而出的那“3吨多重”的人类文明精华垫底,虚幻的天堂变得可以触摸可以感知……坚硬而明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