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很多的读者都知道韦尔斯和《世界史纲》,知道房龙和《人类的故事》;不过,我们更应该知道自己的韦尔斯和房龙,自己的《世界史纲》和《人类的故事》……吕思勉、何炳松、顾颉刚、陈衡哲等以大手笔写小文章,为后人留下了一批具有开创意义的历史读物,在今天仍无过时之感,值得向大家推
荐。
――编者



 何炳松 吕思勉顾颉刚 陈衡哲
何炳松 吕思勉顾颉刚 陈衡哲
民国时期,由于学制的改行、新文化运动的洗礼、西方史学思潮的引入,史学研究、教学和普及活动均很具活力,涌现出一批独具特色、颇有开创意义的历史普及读物。近日,中国工人出版社推出了四本民国年间极具影响力的历史读本:何炳松先生的《世界简史》、吕思勉先生的《中国简史》、顾颉刚、王钟麒先生的《中国史读本》和陈衡哲先生的《西洋史》。透过这些已成经典的历史读物,我们可以欣赏到民国年间历史普及领域的景致。
开白话文写史的新纪元
新文化运动带来了白话文,吕思勉先生首先将白话文叙述引入了历史读物。同代学者顾颉刚曾经这样评价吕思勉的通史著作:“编著中国通史的人,最易犯的毛病,是条列史实、缺乏见解……极为枯燥。自吕思勉先生出,有鉴于此,乃以丰富的史实与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一新的纪元。”(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在《中国简史》中,我们看到吕思勉先生关于义和团运动兴起的论述:
中国自海通以来,所吃外国人的亏不为不多了。自然朝野上下,都不免有不忿之心。然而忿之而不得其道。这时候,大众的心理以为:(一)外国所强的,惟是枪炮。(二)外国人是可以拒绝,使他不来的。(三)而民间的心理,尤以为交涉的失败,由于官的惧怕洋人。倘使人民都能齐心,一哄而起,少数的客籍,到底敌不过多数的土著。(四)而平话、戏剧,怪诞不经的思想,又深入民间。(五)在旧时易于号召的,自然是忠君爱国之说,所以有扶清灭洋的口号,所以有练了神拳,能避开枪炮之说,所以他们所崇奉的孙悟空、托塔李天王之类,无奇不有。这是义和团在民间心理上的起源。而自《天津条约》缔结,教禁解除以来,基督教的传布深入民间,不肖的人民,就有藉教为护符,以鱼肉良懦,横行乡里的。尤使人民受切肤之痛。所以从教禁解除以来,教案即连绵不绝。而拳民的排外、闹教,亦是其中重要的一因。
这段论述丰满、深刻,文笔流畅,且叙议结合,难得的是,这里的论述涉及到了大众心理,尤具识见。
陈衡哲可以说是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上早期的作家之一。了解这一事实,就不难理解她的《西洋史》语言何以能达到如此优美的程度了。
比如陈衡哲在叙述欧洲中古社会的宗教束缚时,这样写道,“总而言之,亘中古之世,宗教不啻是欧洲人生的唯一元素。他如天罗地网一样,任你……出生入死,终休想逃出他的范围来”。在叙述欧洲宗教革命时说:“所以宗教革命的意义,不啻便是这个拆城毁壁的事业。国王欲取回本来属于他们的城砖屋瓦,人民要挥走那般如狼似虎的守卒,信徒又要看一看那光华久藏的明珠(指基督教教义――笔者注)。于是一声高呼,群众立集,虽各怀各的目的,但他们的摩拳擦掌,却是一致的。他们的共同目的,乃是在拆毁这个巨堡。因此之故,宗教革命的范围便如是其广大,位置便如是其重要,影响便如是其深远了。”这样的叙事特征贯穿《西洋史》全书,以致胡适赞扬她“身上每一个细胞都充满着文艺气息”。
顾颉刚先生曾说:“公民所应有的知识全都要用文学的技巧灌输到不甚受教育的民众心中,使得他们可以身体力行。”(《通俗读物的重要性》,1939年1月8日《云南日报》)。诚哉斯言。
张扬民族意识
第二个特点是强烈的民族本位文化情结。终民国时期,挽救民族危亡、寻找民族自救道路一直是学者关心的主题。这种关心当然也反映在民国历史读物中。何炳松先生更提出学术“立场”的问题:
还有一个立场问题,值得我们讨论。这个问题以常理论,本无提出的必要,但是我们试看寻常所谓外国史或世界史,多半是欧洲中心扩大起来的西洋史。欧洲固然是现代世界文化的重心,值得我们格外的注意。但是我们中国人既系亚洲民族的一分子,而亚洲其他各民族在上古和中古时代对于世界的文化又确有很大的贡献,似乎不应因为他们久已衰亡,就可附和欧洲史家的偏见,一概置之不理。
以这样一种立场出发,何炳松先生的《世界简史》尤其是古代部分,几乎成了一部欧亚两洲互动的历史。在他的笔下,向来受人轻视的亚洲各民族,匈奴人、安息人、月氏人、突厥人、蒙古人等,都根据他们在世界文化史上活动和贡献的程度,给以恰当的位置加以叙述。从这种追根溯源中,读者可以领会到,欧洲并非一贯强盛,而饱受列强欺凌的亚洲各民族完全不必妄自菲薄,要坚定民族复兴的信心。融学术见解于文化普及
这四本书都是由著名学者编写,虽是普及读物,却反映了当时最新的研究成果。这其中顾颉刚、王钟麒先生的《中国史读本》表现得最为明显。
顾颉刚于1922年接受胡适邀请撰写历史教科书。编写之际就开始萌发了对中国古史的一些“既定”结论的怀疑。他说:
上古史方面怎样办呢?三皇五帝的系统,当然是推翻的了。考古学上的中国上古史,现在刚才动头,远不能得到一个简单的结论。思索了好久,以为只有把《诗》《书》和《论语》中的上古史传说整理出来,草成一篇《最早的上古史的传说》为宜。我便把这三部书中的古史观念比较看着,忽然发见了一个大疑窦――尧舜禹的地位问题!……《诗经》和《尚书》(除首数篇)中全没有说到尧舜,似乎不曾知道有他们似的;《论语》中有他们了,但还没有清楚的事实;到《尧典》中,他们的德行政事才灿然大备了。因为得到了这一个指示,所以在我的意想中觉得禹是西周时就有的,尧舜是到春秋末年才起来的。越是起得后,越是排在前面。等到有了伏羲神农之后,尧舜又成了晚辈,更不必说禹了。我就建立了一个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
这就是近代学术史上著名的“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说”。当然,顾颉刚先生在著《中国史读本》时,这一观点还未明确提出。但对此,龚鹏程先生有段论述说得很明白:
本书虽成于早岁,且系与王钟麒合作的书,却不难看做是最能代表顾氏整体史观与史学规模之作。许多在本书中简单的论断,后来顾先生也会用较繁复缜密的论著来说明,但说来说去,大旨其实亦不外本书所述。……据此而言,本书在近代史学史上之重要性,显然要远超过一般历史教科书所能具有之意义。
顾颉刚先生的学说,在当时可谓是石破天惊,此后引发了近代学术史上持久的争论。对于顾颉刚先生的影响,普林斯顿大学余英时先生认为:“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说,在史学界发生革命性震荡,主要就是因为它第一次有系统地体现现代史学的观念。”
将自己的学术见解写进历史读本,这里也隐含着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学术见解在历史普及读物中呈现的边界在哪里?几年后,顾、王两位先生的这部书被南京国民政府禁止发行,顾颉刚本人也受到南京国民政府弹劾。顾当时非常气愤,称之为“文字狱”。
然而,从教育政治学的角度看,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具有独立性,而是承载着传播社会认可的意识形态的重要职能。顾氏作为学者,一方面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另一方面还要介入中学历史教育,这本身就很难达成“和谐”。即使疑古史学的观点大致无错,可在南京国民政府看来,“三皇五帝”背后隐藏着中华民族的一种珍贵的信仰和崇拜,是维系国家和民族凝聚力的象征。南京国民政府担心在国运衰微的特殊时期,历史读本如此论述会不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在这种情况下,顾颉刚及其《中国史读本》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这确实是很无奈的事情。
实际上,顾氏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爱国主义者。1931年日本法西斯发动了侵华战争,民族危机愈来愈重。具有忧患意识的顾颉刚从学校历史教育的角度进行了积极思考。他于1935年在《教与学》杂志发表《中学历史教学法的商榷》,旗帜鲜明地指出:“一个民族的历史,无论如何应该以民族精神为中心思想。一个民族假如忘了他的精神,即使他存在,也是不健全的民族。”顾颉刚主张利用中国历史上民族英雄的故事来培养学生的民族精神和民族凝聚力。
观念现代,认识超前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四本书都体现相当现代的观念,有些方面甚至是相当超前的。限于篇幅,这里仅以陈衡哲著述的《西洋史》为例略做陈述。
“五四”期间,陈衡哲对中国当时存在的社会问题,尤其是妇女问题,寄予了强烈的关注,并发表了许多有思想深度的文章,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讨论。在四川大学任教的时候,她发现有许多女学生是官僚、财阀们的姨太太,这一事实,使她心头萌发了对四川当局的强烈不满,也更同情那些深受蹂躏、压迫的女性。愤怒之下,她在《新新新闻》上发表了一篇揭露四川问题的文章,说这是女性的耻辱,也是大学教育的破产,号召妇女要争取独立自主。她在后来所写的《女子教育的根本问题》一文中对女子教育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她说女子教育是“几千年来奴性的铲除”,“是独立人格的教育”,是“帮助她们能自己解放自己,从牢笼中跳出来,光明磊落、堂堂正正做人”。
这种关注也反映到她的史学研究中。作为唯一的一位为中学生编写历史教科书的女性作者,《西洋史》具有独特的“女性视角”。这也是《西洋史》的一大“亮点”。
 如,在阐释工业革命的结果和影响时,陈衡哲专门指出,靠了工厂制度的兴起,妇女已能获得经济的独立,靠了教育的普及,妇女的智识与能力,也日益增加了,所以,女子在教育方面、经济方面、职业方面、政事方面,确已与男子争到了平等的地位。在陈衡哲看来,女子能够参与政权是“妇女运动得到胜利的最明显的标帜”。虽然陈衡哲就工业革命对于妇女问题的积极影响表现出了过于乐观的姿态,但她分析问题的视角无疑是相当独特的,值得称赞。
如,在阐释工业革命的结果和影响时,陈衡哲专门指出,靠了工厂制度的兴起,妇女已能获得经济的独立,靠了教育的普及,妇女的智识与能力,也日益增加了,所以,女子在教育方面、经济方面、职业方面、政事方面,确已与男子争到了平等的地位。在陈衡哲看来,女子能够参与政权是“妇女运动得到胜利的最明显的标帜”。虽然陈衡哲就工业革命对于妇女问题的积极影响表现出了过于乐观的姿态,但她分析问题的视角无疑是相当独特的,值得称赞。
在论述工业革命这一节内容时,陈衡哲在教科书的“小字部分”就妇女问题做了进一步的探讨,论述了她关于妇女解放问题的主张。陈衡哲将妇女的智识、能力、人格与妇女的自身解放紧密联系起来,反映了她思考问题的深度。这也是陈衡哲人生经历的深刻总结与真实反映。她在书中这样写道:
人民常有把女子参政运动视为女子运动的唯一事业者,这是一个大错误。女子参政固是妇女运动的一件事,但他绝不足代表妇女运动的全部。这个理由很是简单的,因为,第一,政治上的活动,不过是人生活动的一部分,他不但不能代表人生的一切活动,并且不是人生活动的中心点。其二,参政权的争得……仍不过是一件比较肤浅的事。妇女们如欲与男子们争到真正的平等,根本上尚以自己的智识的解放,能力的修养,及人格的提高为最重要。……所以热心此妇女运动者的最大责任,即是去帮助我们的青年姊妹,使她们能发挥她们个人的天才于最适当的道途,至于参政运动,却不过是这些道途中一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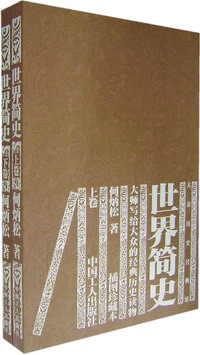 应该说,这些看法,在今天仍有相当突出的启发意义。
应该说,这些看法,在今天仍有相当突出的启发意义。
而在论述19世纪文化的重要表征时,妇女运动也是论述的一个角度。她说,妇女运动的原动力是民主主义。妇女主义是法国大革命及工业革命的一个结果。妇女运动的始祖,是英国人武斯冬克拉夫女士。她的名著《妇女权利的辩护》是关于妇女问题的第一本杰作,这本书的大旨认为妇女与男子是一样的,她们同是具有个性的人物,所以她们在智识方面、经济方面、政事方面等,应当与男子得到同样的机会。显然,这里陈衡哲实质上是在借武斯冬克拉夫女士之口阐释她关于妇女解放的观点。
在20世纪60、70年代美国的公民权利和平等权利运动中,相当多的社会民众就直言不讳地指责历史教科书中很少涉及历史上的妇女,进而施加对这种历史教科书在学校选择和使用时的压力。这么看来,20世纪20年代陈衡哲著述《西洋史》,其认识是相当超前的。
在回顾历史类图书的发展历程时,张耕华先生感叹道:“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史学研究已有长足的进步,各种大部头、多卷本的历史专著层出不穷,各类历史专题研究之新奇、深湛,也是前所未有。”但愿这套民国时期历史读物的重印刊行,能为我们今天的历史普及工作提供一些新的借鉴。
《中国简史》(上下卷),吕思勉著,中国工人出版社2007年6月第一版,39.00元
《世界简史》(上下卷),何炳松著,中国工人出版社2007年6月第一版,46.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