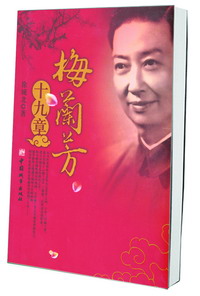 梅兰芳也不明白,自己新中国成立后总会在隐隐之间感到怅惘。按说,真不该再有什么不满意了。从个人的名誉地位讲,都远远超过了前半生。梨园的整体状况也很好,孩子们幼小就有学上,进了戏曲学校仍然读书。等再进
梅兰芳也不明白,自己新中国成立后总会在隐隐之间感到怅惘。按说,真不该再有什么不满意了。从个人的名誉地位讲,都远远超过了前半生。梨园的整体状况也很好,孩子们幼小就有学上,进了戏曲学校仍然读书。等再进他仔细分析过,现实中不让人满意的事还有,但比新中国成立前可要少得太多。更何况今天自己高位在上,有了这样一个“两院院长”的名义,再加上中国文联、中国剧协等的那些闲职,还能有什么不满意呢?
尽管梅兰芳不断这样的提醒甚至是告诫自己,但心中的隐忧却有增无减。最后的最后,他算是明白了原因:总觉得今天梨园的这拨中青年,有些接不上这辈老人的班。老人指谁?在梅兰芳心中,自己是不敢称“老”的,自己年幼之时,接触的老人实在太多。远的不说,就讲同台合作唱过戏的就有:伶界大王谭鑫培、武生泰斗杨小楼,至于年龄长于自己的,就比比皆是了。就说谭大王吧,自己接触他时他实际已经老啦,但只要他一上台,精神头儿就上来,而且聪明劲就更是有增无减。他是过来人,生活的艰苦自不待言,等生活不艰苦了,他依然还是惦记着从前,有些来得太容易的钱,他拿着也总觉得不踏实。比如刚开始灌唱片的时候,人家通过中间人把酬劳拿到自己面前,他竟然迟疑地说不出话!他想,自己不就是唱了那么两三个段子,就权当在家中吊嗓子吧。敢情――,吊嗓子也能吊出这么多的钱来。于是,他认真与身边的人讲:“拿人家这么多的钱,合适么?”身边的人告诉自己,唱片公司给了您这么多,他还有赚!谭半信半疑,反复说“以后再不能这么拿钱了”。身边的人听了暗笑,等下一回灌过唱片把酬劳再拿到谭大王跟前时,这身边的人预先就扣除了一半,只把这一半给谭。不料谭接到这一半,心中反而满意,脸上充满笑容,连说“这就好,这就好”。梅兰芳回想着前辈们的旧事,缅怀着他们艺术及做人上的风范。
谭老爷子会武功,给地主老财干过看家护院的差事。当然,他可不是《打渔杀家》中的教师爷,完全是正面人物。有了这武功,他拿进戏里就好看了,《翠屏山》里他就用进了六合刀。等他进了城市,依然不忘自己的武功,每年春天他都参加城市居民的游乐活动――“马会”,他自己站在飞奔着的马的马背上,招手向四周的群众致意。群众给他喝彩,他点点头,算是回报。这些活动是没有报酬的,他也全知道,他是自己要去参加的,而北京的群众也知道他会参加,因此去马会看他表演的人也特别多。谭老爷子知道自己究竟是干什么的,所以他一辈子活得特别明白,什么时候该干什么,什么时候不该干什么,他心里都有底。至于他钻研了一辈子的戏,其实也像是顺手给“带”出来的。他真是不经意间,一不留神,就把演技锤炼成这般境地。
回忆过谭老爷子,梅兰芳又想起如同叔叔大爷一般的杨老板。就说《霸王别姬》这出戏,最初是杨老板提携尚小云演的,一共两本。后来齐先生看了,觉得也适合我梅兰芳,就改成为一本。请杨老板与我排演了,一演,还挺红的。最初排名是杨与梅,并挂。我自刎之后,戏还有老长的一大截,霸王要在乌江旁边车轮大战。可这戏演来演去,不想就变成了我的戏。只要我一自刎,观众就纷纷起堂,人家可不再看了,觉得戏已经完了。杨老板看见这一幕,心中实在很无奈。心说“兰芳的人缘真好啊,我也比不了,看来这出戏――今后我是没法唱了。”我也无奈,此后再演这出,戏就只能结束在我的自刎的时候啦。关于杨老板的嗓子,还有一段故事:据说出科之后,一度喑哑失声,他就把自己封闭在小房间中,用纸把四壁糊得严严实实,密不通风。自己每天早晨去一个大庙练功,晚间则去戏园子看戏,经过一年半载,嗓子忽然出来了,再经过名师调教,这嗓子不仅好听,而且非常入味……
梅兰芳想过这些,他有一个最深而且又有所不解的感慨:无论是谭鑫培或杨小楼,他们的做人与做艺都是统一的,都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他们用了很大的功夫,但给人的感觉却是不累,是老天爷让他们成就如此大的功业的。甚至可以说,他们前无古人并后无来者。他们是一个历史阶段的集大成者,是业已过去了的历史阶段所竖立起来的丰碑。梅兰芳感觉到,自己能够有幸在青年时期得以与他们同台,乃是自己一生最大的幸运。没有这些经历,自己是成不了后来的成就的。
回忆过前辈,梅兰芳再看今天的学生弟子,就有些不满足了。今天学戏的青年条件多么好。首先是有学上,衣食无愁,政府帮着你们成名,给你们铺平了前进的道路。如果还认为有阻碍,政府也会帮你们铲除之。可是――这“可是”之后的话,就让梅兰芳不好说了。为什么今天(新中国成立后)的戏曲青年成不了艺术大家呢?他们一个个,身体好也精力充足,政治上也要求进步,其中有些还担当了这样那样的行政职务。说到他们舞台上的玩意儿,我只能说其中有些还过得去,但绝对比不了前辈。可我们这个时代,是早就超过了从前许多许多的。为什么我们今天的人(戏曲后辈)却超不过前辈呢?
梅兰芳困惑起来,他想了许久,始终也没能想清楚。
本文摘自《梅兰芳十九章》,徐城北著,中国城市出版社2008年1月第一版,32.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