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伊利亚・爱伦堡(1891-1967):苏联作家。1910年开始文学创作。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任战地记者。十月革命后曾参加苏维埃政府工作。1921年后以记者身份去德、法、比等国
伊利亚・爱伦堡(1891-1967):苏联作家。1910年开始文学创作。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任战地记者。十月革命后曾参加苏维埃政府工作。1921年后以记者身份去德、法、比等国
。在国外十多年中,写了众多作品。30年代回国后,在卫国战争中任《红星报》战地记者。著有长篇小说《巴黎的陷落》、《暴风雨》和《九级浪》等。1954年发表的中篇小说《解冻》在苏联文艺界引起巨大震动。后用五年时间写成长篇回忆录《人・岁月・生活》,于1960年开始陆续发表,在苏联及西方引起强烈反响和激烈争议。
十余年前,我曾在“经典重读”系列文章的开篇中写道:“经典不是流行,但远比流行久远。或许说,经典是永不过时的时尚,是细水长流的流行。经典并不因我们知识的丰富、阅历的增多和社会的巨变而过时,正是由于有了这些变化,才使每次‘经典重读’都有一种历久弥新的感受,都会获得新的教益与启示。这便是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的所在,也是经典的魅力之所在。”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便是我有常读常新之感的经典之一。
最近重读此书,自然又有新的感想。其中之一,便是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的遭遇和他本人命运引起的一些不期而然的联想。
《青年近卫军》描写的是煤矿小城克拉斯顿诺青年抵抗法西斯占领军、成员最后大都英勇牺牲的故事,50年代也是我国青少年的必读书。不知多少青年为书中英雄人物感动得热泪盈眶,说此书影响了一代青年毫不为过。
然而,这次读《人・岁月・生活》却发现,现在看来正统得不能再正统、旋律“主”得不能再“主”的《青年近卫军》,也险遭灭顶之灾。出生于1901年的法捷耶夫十月革命前就接近布尔什维克并参加革命活动,1918年入党,1919―1921年在远东参加红军游击队。不久就开始了以俄国国内革命战争为题材的文艺创作,特别是小说《毁灭》,赢得高度赞誉。后来他担任苏联作协总书记、理事会主席,成为文艺界的高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听说了克拉斯顿诺一些青年自发组织起来打击德国占领军的故事,深为感动,便以此为题材创作了小说《青年近卫军》。小说歌颂了反抗侵略者的英勇行为,作者又是作协总书记、理事会主席,于是就有电影导演将小说拍成电影。没想到,却惹了大祸。原来,斯大林看完电影后勃然大怒,因为这些青少年的行动都是自发的,“共青团组织哪里去了?党的领导哪里去了?”再一了解,电影是根据小说改编的,报上立即出现严厉批判小说《青年近卫军》的文章。随后,《真理报》上发表了法捷耶夫的信,公开承认这些批评是公正、正确的,并答应修改小说。爱伦堡回忆此事发生不久他与法捷耶夫会面时,法对他说自己“没有修改正文,而是增写了几章――写几个老布尔什维克。他沉默片刻,又补充道:‘当然,即便我成功了,小说将已经不是原来那样……不过,也许我是太崇拜游击习气了……时代是艰难的,斯大林知道的比咱们多……’”
读到这里,不禁想起不久前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新拍电视连续剧《铁道游击队》。“下一代”们看了这部电视剧后,听说早就有电影《铁道游击队》,而且这部现在看来正统得不能再正统、旋律“主”得不能再“主”的影片在“文革”中竟是被严厉批判的“禁片”时,全都大吃一惊、大惑不解。他们当然不知道,其实连我们这一代许多人也已经忘记了,那位当年一言九鼎的“文艺旗手”对电影《铁道游击队》的判定:“没写主席关于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原则,写的是主席批判的游击主义。游击队不依靠群众,都是神兵,只有芳林嫂一个群众。有政委,看不到政治工作,不像有高度组织纪律的无产阶级游击队,像一帮农民、小资产阶级队伍。没写党的领导,不像八路军领导的,单纯地搞惊险神奇动作,宣传个人英雄主义……”
许多东西,并非完全偶然,而是其来有自、渊源颇深呢!
爱伦堡与法捷耶夫在20年代就相识,但由于法捷耶夫是高级领导,所以在战前他的感觉是“他对我而言与其说是一个作家,不如说是一位首长”,所有作家还都熟悉他那种“善于在文章或报告中赋予斯大林的一句简短的话以深刻的含义”的特点。战后,他们开始亲近起来。法捷耶夫有次对他说,1951年有一天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之一马林科夫找他,说是冶金系统有人搞了重大发明,但却受到阶级敌人的破坏,要他写一部长篇小说。马林科夫还说:“倘若您把这写出来,您就给党帮了一个大忙……”听到党的召唤后,法捷耶夫立即行动起来,投入到紧张创作中去。由于对冶金业完全不了解,随后几年一直在辛苦采访、搜集素材,就在小说《黑色冶金业》快要完成时,政治形势大变,苏联开始平反一些冤假错案,冶金业的“案件”也被证明是桩冤案,根本不存在一个“阴谋破坏集团”,被诬陷的“阶级敌人”被公开恢复了名誉。法捷耶夫盛怒之后曾悄悄对爱伦堡说:“我就只得把手稿扔了。把自己也给扔了――我已不能动手写新的作品了……”
从个人艺术趣味来说,法捷耶夫不喜欢并且在1928年公开攻击过马雅可夫斯基的长诗《好!》,但30年代斯大林表示了对这首诗的欣赏,1938年法捷耶夫立即大赞此诗,称为“历史性事件”。当开始批判诗人帕斯捷尔纳克的时候,作为作协头号领导人他自然带头冲锋陷阵。但有次酒后,又私下对爱伦堡大大夸赞帕斯捷尔纳克的诗写得好,说这才是真正的诗歌,并滔滔不绝地背诵起来,“简直停不下来了,偶尔中断一下背诵也只是为了问一句:‘好吗?’”在三、四十年代的“大清洗”中,无数作家遭到迫害。法捷耶夫清楚,这些作家其实并不是“间谍”或“敌人”。但以他的身份、地位自然是不少迫害案的领导者和具体执行人。当然,尽管少有成功,他也曾设法保护过一些作家。
当政治形势大变,“解冻”开始,各种冤假错案纷纷平反时,法捷耶夫自然痛苦万分,于1956年5月饮弹自尽。对他的情况,爱伦堡颇能理解:“法捷耶夫年纪很轻的时候就参加了远东的游击队,尔后又参加镇压喀琅施塔得叛乱。他17岁入党,20岁被赤塔的党组织选为代表出席了第十次代表大会。”对他来说,“政治”并不是《简明教程》中的抽象篇章,而是自己活生生的经历。“在某些作家的一生中,政治斗争不过是几个月或几年的激情。对于法捷耶夫而言,政治却是他毕生的事业。”他的结论是:“法捷耶夫是个勇敢的,但又遵守纪律的士兵,他从未忘记总司令的特权。”
“把自己也给扔了”,读到法捷耶夫这句话时,我的心灵为之一震。这是一个作家良知复苏后的痛苦自白,是“两种身份”长期矛盾的最后爆发。作为有“灵魂拷问”传统的俄罗斯作家,他以自杀解决矛盾。而这,是没有“灵魂拷问”传统、不习惯忏悔的民族所难以理解的。他可以想法设法否认各种事实,力证自己的清白,力举自己曾经暗中保护过某些作家,等等。他更可以辩解说,自己当时只是执行领袖的指示,是真心实意听党的话的战士,出发点是好的,而且当时举国上下大家不都如此吗?因此,他完全可以心安理得,甚至,他的作品能被后人称为“革命文艺”的代表呢。然而,他却不能这样,因为他无法不忏悔、不自我拷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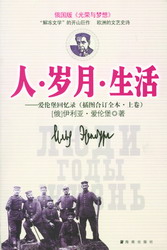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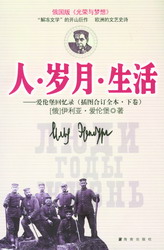
《人・岁月・生活――爱伦堡回忆录》(插图合订全本・上卷<下卷),【俄】伊利亚・爱伦堡著,冯江南、秦顺新译,海南出版社2008年2月版,98.00元(上・下两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