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已于今年早些时候在英国出版,同样大获好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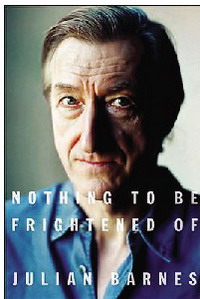 |
| 《没有什么好怕的》 |
没有人肉体不朽,也没有人能回避死亡。我们看看巴恩斯在面对死亡时的沉思吧:
《没有什么好怕的》选译
我不信上帝,但我思念上帝。我哥哥曾在牛津和索邦教哲学――比伦敦、曼彻斯特或卢顿好得多,您觉得呢?――他认为这种表白“叽叽歪歪”。他可不像我这么多愁善感。
先从我外婆说起吧。您可别以为本书是一本俗不可耐的自传;我或会将本人私生活中此类狂想的、堂吉诃德式的段落择其若干,予以呈现,但也仅在它们可以揭示我对死亡的理解时,才如此为之。我还要表现自己是何等的聪明。
看着我妈妈的遗体,我在想,她想穿什么衣服入土?我哥哥认为记忆往往都是假象,因此严厉责怪我将真愿望与伪愿望混为一体。我以福楼拜和左拉的名作中也能找到的笛卡儿的二元论作答。他再用康德辩证法拆解,予以回击,我俩大笑起来,彻底忘掉了我们的妈妈。
如果给我一个带有强烈反宗教观念的衰弱信仰背景,我或会变得十分虔诚。然而,我却投身于无神论,尽管在花甲之年,我的立场已经转向了不可知论。我的密友G,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说我是个死亡恐惧论者,像帕斯卡尔那样骑墙自保。
我会争辩说,我现在不过是对我不知道的那一切知道的更多了。上帝是否存在?如果他存在,那么他又采取何种形式存在呢?他有可能是个最高明的冷眼旁观者,并且乐见我们对永生的妄念吗?或者,我们只是一堆有限存在的细胞?这些问题人人都会自问,而当我在某夜意识到死亡问题(nocturnal réveil mortelut),也这样问自己的时候,它们听起来更加意味深长。
蒙田说过:“Philosopher,c'est apprendre à mourir”(哲学家,即总在学习死亡之人)。我倒更喜欢伟大的阿兰・德波顿(AlaindeBotton)套用的这句格言:“Philosopher,c'est apprendre à vendre des livres”(哲学家,即总在学习卖书之人)。作为小说家,我必须声明我对叙事是有兴趣的,尽管你未必会在读到这些天马行空、追根究底的冥想时对我妄加揣测。我盼望我的人生是有意义的,对于往事的记忆要有一种尼采式的触及;而死亡总是躲避我们对它的理解。我们始终无法控制消逝的方式与时机,除了吾辈中那些按部就班死去的人。
*
如果我自称20岁时是无神论者,50和60岁是不可知论者,这不是因为我在此期间获得了更多的知识,而只是因为对无知有了更多的了解。我们怎能确信自己知道的足够多了呢?作为21世纪的新达尔文主义唯物论者,我们对生命的意义和机理自1859年便已全完全澄清深信不疑,认为自己绝对比那些屈膝叩首的轻信者聪明,他们有点出离物外,相信神意、注定的世界、复活,以及最后审判。可是,我们虽然得到的信息更多,却并不高明,当然也不比他们更有智慧。是什么让我们相信自己的知识才是一切问题的解决之道呢?
我妈妈会说,也的确这样说过:那是因为“我的年纪”――仿佛随着大限将至,形而上学的谨慎和无情的恐惧会弱化我的意志。可她也许错了。意识到死亡始于很早以前,我十三四岁的时候。法国评论家夏尔・杜博斯(Charles du Bo),伊迪斯・沃顿的朋友和译者,创出了一个有用的短语,来形容这一时刻:le reveil mortel。怎么翻译才好?“死亡闹铃?”听起来有点像酒店的叫早服务;“死亡意识”,“死亡唤醒”?――有点德国化;“死亡觉醒”?――可它用以形容的并非一种特殊的心灵撞击。杜博斯短语的这几种译法都有久缺,但是,从某种角度上说,“死亡闹铃”这个翻译或许还不错:就像身处一个不熟悉的旅馆房间,闹铃的时间是前一个房客设好的,于是,在某个可恶的时刻,你突然被从睡梦中叫醒,进入黑暗、惊恐,可怕地领悟到这是一个寄居的世界。
我的朋友R最近问我是否经常想到死亡,在什么环境下想到死亡。我回答,每个醒着的日子都会至少想到一次;夜里它也会断断续续地来袭扰我。只要外部世界出现明显相关的变化,死亡意念便经常不请自到:夜色降临,白昼渐短,或是长日将尽。也许有点为我独享的是,我的闹铃常常在电视上的体育赛事开始时响起,不知什么原因,尤其是在五国(或六国)橄榄球联赛期间。我把这些对R和盘托出,并为自我纵容地停留于这一话题而道歉。他答道:“你的死亡意念是健康的。不像(我们共同的朋友)G那么变态。而我是超超变态的。总是上来就往死里整那种。大枪筒子插在嘴里。后来泰晤士谷警局的人来了,拿走了我的12毫米霰弹枪,我就好多了。因为他们在‘荒岛唱片’(译注:BBC一个电台节目)听到我说这事儿来着。现在我只有(儿子的)鸟枪。没意思。不够火暴。看来咱们要一起迎来夕阳红了。”
人们往往更乐于谈论死亡:不是死而复生,而是死掉,灰飞烟灭。20世纪20年代,西贝柳斯会去赫尔辛基的卡普(Kamp)饭馆,参加一个名叫“柠檬桌”的聚会:柠檬是中国人的死亡象征。他和共餐的食客――有画家、工厂主、医生和律师――不仅有权而且必须谈论死亡。一百来年前,在巴黎,有群不那么固定的作家在马尼(Magny)饭馆聚餐――福楼拜、屠格涅夫、埃德蒙・德・龚古尔、都德,还有左拉――也讨论这一问题,秩序井然、气氛融洽。这些人都是无神论者,或严肃的不可知论者;死亡有惧,但死亡不可避免。“人们觉得我们应具悲观信仰。”福楼拜写道,“人必须与自己的命运平起平坐,也就是说,要像命运一样冷漠。说着‘无所谓!无所谓!’,看着脚下的黑坑,不动声色。”
我从未想过要尝一尝大枪插嘴的滋味。与此不同,我对死亡的恐惧水平还低,还算合理、适度。而要想搞个新柠檬桌聚会或马尼晚餐,来讨论此事,可能会出现客人们互不买账的问题。比起男性喜欢自夸的汽车、收入、女人、鸡鸡长短……为什么死亡话题就该低人一等呢?“盗汗,尖叫――哈!――太小儿科了吧。你等着吧,直到你……”如此一来,我们的个人苦恼不仅显得无聊,而且乏力。“我对死亡的恐惧比你的大,可我还能更雄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