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备受瞩目的第七届茅盾文学奖颁奖典礼11月2日晚在茅盾先生故里――江南水乡古镇浙江乌镇举行。与此同时,本报约请了茅盾文学奖评委陈晓明、何向阳、汪政撰写了他们眼中的获奖作品。虽然对于作者和很多读者来说,这些作品并不新鲜,但是评委们的解读,或许会带领我们重新领悟和
认识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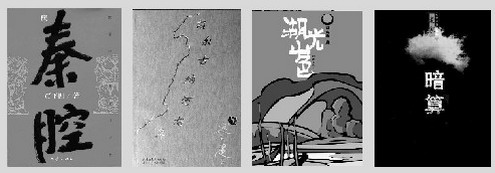
对于当代中国文坛来说,麦家的写作无疑属于独特的路数。这个人的存在已经变得不可忽视,他那么顽强、绝对而倔强。他的写作诡秘、幽暗、神奇,深不可测,到处潜伏着玄机,让人透不过气来。阅读他的作品,就像是被引诱到一个偏僻的山谷,而黑暗开始降临。阅读没有退路,只有在黑暗中摸索。那真是孤苦伶仃的阅读,无助的阅读,就像他的写作一样;当然,也是极其富有刺激性的阅读,这是一种关于阅读的阅读,也是关于写作的写作。
麦家以《解密》令文坛刮目相看,他的出现就像一片阴影,投在亮丽的文坛上,多少有些令人惊慌。事实上,麦家写作多年,他的写作姿势显然是潜伏式的,是一种秘谋,是对写作的宣誓。《解密》就这样出现了,令人措手不及。那是一个关于701单位破解密码的故事,很吸引人,像是侦探小说、间谍小说、恐怖小说的变种,一种新型而独特的种属,或者说一种四不像的写作怪物。麦家的小说可以看出有一种形而上的哲学意味与大众侦探小说的糅合,或者说是博尔赫斯与希区柯克或者斯蒂芬・金的糅合。这种糅合当然不是刻意的仿造,事实上,这乃是当今世界小说艺术的某种秘密探求。大众通俗类的小说如此,如《达・芬奇密码》;纯文学的艺术精品也不乏些例,如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现在,中国的麦家也来了这么一手,而且颇有中国本土风格。
2003年,《暗算》又给我们制造了一种黑暗,这是阿炳的黑暗。在这本书中,不用说,关于瞎子阿炳的篇章是最动人的,也是最接近麦家的写作本质的。这是对黑暗的书写,是在黑暗中书写。麦家再次动用了他对故事的处理能力,在这里,“暗算”被作了双重性的处理,暗算既是指破译电码,也是指这些破译者的生活如何被暗算。坦率地说,后者的显性化的故事并不巧妙,也不特别惊人。阿炳也被命运算计了,他无法生育,他的妻子林小芳与山东大汉有了儿子,阿炳为此自杀。真是人算不如天算,阿炳如此不堪一击,比暗算更强大的是一种命运,一种文化力量。那个黄依依的故事同样如此,她在做人流时被张国庆的妻子所暗算,结果死于非命。诸如此类,这些故事都有一些显性的被“暗算”的意味。我想说,这些显性的故事当然可以在宿命论的意义上提示存在的某种深度性,甚至触动读者掩卷而思的哲理性。但是对于麦家的书写来说,这些显性的故事却消除了黑暗,把黑暗中的故事带向了光亮处。但这并不是真正的光亮,这是另一种存在,另一种书写,一种世俗化的书写。而真正黑暗中书写,是永远身处黑暗中,那种光亮是从黑暗中的坚硬存在磨砺出的火花,它是黑暗极致的光亮。对存在之坚韧性的书写,书写能体会领悟到自身的力,书写是对存在的铭写,对生命之存在,存在之极限的书写。神秘的不是世界是怎样,而是世界是这样!维特根斯坦如是说。书写对那种黑暗中的存在给予接近,它就迫近了神秘,真正不可知的生命延伸之路。麦家给当代中国文学提示的,是一种坚韧的书写样式,一种真正的另类的,也是最虔诚的写作。这样的写作“暗算”了文坛,当然也可能“暗算”了茅盾文学奖。它就埋伏在那里,只要它现身,它就能完成命定的任务。
麦家的文字是有力的,那么简洁,一种被痛楚所浸满的文字,它可以引向不可知的深谷,穿过那黑暗的屋子,在黑暗中听风;能提供这种图景的文字的人,能独享一种秘密,一种幸福,一种意外之喜。
关于“7”的所有设想,可以看成是麦家关于写作的设想,小说中的那个叙述人“我”就是一个戴着墨镜的人。麦家就是一个戴着墨镜写作的人。由此就不难理解,这部小说的第一个主角就是“瞎子阿炳”。只有瞎子阿炳面对的黑暗,他带来的黑暗给麦家的写作提供了家园。隐秘、秘密、解密、暗算、秘谋、告密、宣誓……等等,这些都是黑暗中的行为,也都是本质性的写作,所有的本质性的写作都是黑暗的写作,都在黑暗中或关于黑暗的写作。写作就是沉入黑暗,在黑暗中发光;绝对的写作就是绝对的黑暗,就是绝对之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