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人民在诗歌当中起着统治的作用,那么人民在政治方面取得统治的日子就也更加靠近了。”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这句名言可以说明,新时期以来文坛的复苏,恰是这一声嘹亮的号角唤醒的。人心在思考中走向凝聚。经过10年犹如漫漫冬夜的“文化大革命”,人们在思考中孕育和积聚的春天的力量,最终在丙辰清明的
天安门广场,引发了一场悼念周恩来总理、反对“四人帮”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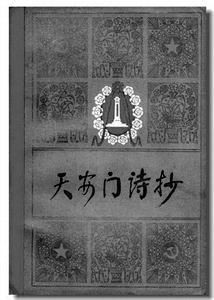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12月出版的《天安门诗抄》
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日子里,有记者就“新时期文学潮流是如何引发的”问题来采访,我翻出了珍藏的这样几本书:1、由“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于1977年7月1日编就的《革命诗抄》第二集;2、由“七机部五○二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革命诗抄》编辑组”于1977年12月编就的《革命诗抄》;3、由“北京外国语学院童怀周”于1977年11月编就的《天安门革命诗文选》;4、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12月出版的《天安门诗抄》,题签是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华国锋的手迹;5、北京出版社1979年1月出版的《天安门诗文集》,题签是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的手迹。
经历过那段历史或者对改革开放历史有研究的人,一看这几本书就会明白,这是记录1976年清明节悼念周恩来总理的“天安门事件”(又称“四五运动”)的。那一年的1月8日,人民爱戴的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而报纸等媒体上展现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舆论,使人们对再度从中国政坛沉寂的邓小平痛心惋惜的同时,对政坛出现转机无望。
人心在思考中走向凝聚。经过10年犹如漫漫冬夜的“文化大革命”,人们在思考中孕育和积聚的春天的力量,最终在丙辰清明的天安门广场,引发了一场悼念周恩来总理、反对“四人帮”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
三年后的1979年,中国文联主席周扬在谈到丙辰清明时说:“广大人民群众哀悼周总理,怒讨‘四人帮’,为后来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作了思想动员和舆论准备。历史是无情的,也是富于戏剧性的。‘四人帮’篡党夺权首先从文艺战线开刀,人民则用文艺的重锤敲响了他们覆灭的丧钟。”(周扬:《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 ――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一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79年11月20日)。
“假如人民在诗歌当中起着统治的作用,那么人民在政治方面取得统治的日子就也更加靠近了。”把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这句名言与周扬的话相印证,自然可以说明,新时期以来文坛的复苏,恰是这一声嘹亮的号角唤醒的。
不过,这几本书在当年的出版过程――当年编辑出版的有关“天安门诗抄”的书很多,我的收藏仅仅是一小部分,本身也是文学史和出版史上有意义和有趣味的事情,值得钩沉一番。
“非法出版”的“天安门诗抄”
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了!在欢庆的呐喊声中,人们渴望的万象更新、生机勃勃的春天却推迟了脚步。由于“两个凡是”指导方针的提出和推行,人们提出的涉及纠正“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某些错误决策的正当要求,被压制了。被毛泽东定为“反革命事件”的“四五运动”,自然不能触及。
但是,“两个凡是”也无法阻挡人们要求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渴望,搜集和传播天安门事件中的诗文,就很自然成为人们这种渴望的一种斗争手段。
“四人帮”刚垮台,原七机部二一一厂资料科和工艺科的15位同志就自发组织起来,首先在厂内贴出了手抄的《丙辰清明天安门诗抄》。诗抄一贴出,反响极大,人们辗转相抄并补充。一些有心人又从公安部立案的材料中,从本单位“追查”时收缴的诗词、胶卷和照片中,共收集了1800首诗词,一百多张照片,按照时间顺序,编排成册,形成了一部完整的诗稿。这大概是第一部反映天安门事件的诗抄。
诗稿形成后,为了扩大影响,自然有了印刷成书的想法。原七机部的领导人顺应民意,支持这一做法。但是,在中央依然维持“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定性的情况下,诗稿在北京印刷显然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于是,有人把书稿送到了辽宁省丹东市的一家印刷厂。几经周折后,1978年9月,这部名为《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诗文集印刷成书,印数10万册。这本诗文集除编选了丙辰清明张贴在天安门广场的诗文外,还收录了1977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一周年张贴在天安门部分诗词。
1976年12月,原七机部五○二所二室和七室的二十多名同志也自发组织起来,搜集、整理和刻印天安门诗文。在周恩来逝世一周年之际,他们把一百三十多首天安门诗词张贴在天安门广场和中关村的墙上。而此时,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的一些人,也在做这样的工作。于是,两家一拍即合,成立了“七机部五○二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革命诗抄》编辑组”,四处搜集有关天安门诗词。他们通过各种关系,从北京市公安局、中国科学院保卫部门得到了许多立案侦察时被封存的诗稿和影印件,于1977年12月编就了《一九七六年清明节革命诗抄》。自动化所领导支持“编辑组”的正义行动,专门批了20万元专款作为印刷费用。
为了扩大影响,“编辑组”决定找一位著名人士题写书名。可在当时天安门事件没有平反的情况下,党内著名人士不便找,他们便想到了赵朴初。
赵朴初既是知名人士,又是著名书法家、诗词学家,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仅仅具有这些头衔还不够,最重要的是要敢于承担政治责任,而赵朴初就是这样一个最好的人选。
天安门事件后不久,赵朴初就在激愤之中,写下了一首表露自己心迹的词:
春寒料峭欺灯暗,听风听雨过夜半。门前锦瑟起清商,陡地丝繁兼絮乱。人间自古多恩怨,休遣芳心轻易换。等闲漫道送春归,流水落花红不断。
1978年8月,赵朴初把这首词录给了楚庄,并题:“芳心一词寄调木兰花1976年作楚庄同志两正1978年8月赵朴初。”
1998年10月,我和桑思奋兄拜访楚庄时,他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把这首词展现给我们看。楚庄并逐一给我们解释,以怀念赵朴初的凛然正气。他说,“春寒料峭”指春天,当然在这里主要是指当时寒冷的政治空气。“欺灯暗”指1976年4月5日天安门事件当天晚上,在镇压进行之前,把广场的灯都灭了。“听风听雨过夜半”,是指得知清明节那天要镇压而夜不能寐的焦灼心情。“门前锦瑟起清商”,是指天安门前人们悼念周总理。“陡地丝繁兼絮乱”,意指一阵狂风把天安门前扫荡了。楚庄说,这首词的前半段是用文学的语言记录了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至于词的后半段,“等闲漫道送春归,流水落花红不断”一句,人们都能体会到作者当时对1976年天安门事件平反所寄予的希望。
1978年3月5日,中共中央党校校刊编辑室编辑的《理论动态》第47期上,又刊出了赵朴初怀念周总理的词《金缕曲・于西山得一幼松移植盆中持归供周总理像前因作》:
莫道盆松小,
是移来,
雪山筋骨,霜崖新貌。
遗像瞻前欣得地,
已见稚虬腾蹈,
待他日撑天夭矫。
自是扶持缘正直,
信人心所向关天道。
今与昔,长相照。
每因睹树思周召,
最难忘,
天安门外,万株衣缟。
泪涌江河流德泽,
袂举风标节操,
知激励人群多少!
大地春雷摧蚁梦,
喜兴邦渐展身前稿。
唱不尽,千秋调。
词中“最难忘,天安门外,万株衣缟。泪涌江河流德泽,袂举风标节操,知激励人群多少!”句,是对天安门事件的最直接的描述。这首词,当年曾被文艺界人士以多种艺术形式演唱,广泛表达了人民群众对周总理的哀思和缅怀。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们,至今仍能回想起那低昂激动的旋律。
赵朴初这两首广为流传的辞章表明,他是一个敢于承担政治风险的人。于是,“《革命诗抄》编辑组”找到他后,他欣然为该书题签。
经过一番周折,《一九七六年清明节革命诗抄》印刷成书后,却没有得到发行。有关部门得到该书后,为了与中央“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的定调保持一致,便以“非法印刷品”的“罪名”予以全部封存,并对“编辑组”的工作人员追查“政治责任”,责令他们写出“深刻检查”。但是,民心不可违。“编辑组”的人无所畏惧,他们作了两手准备:一方面准备变卖家产,赔偿所领导所拨的20万元专款,然后进监狱;另一方面则据理力争,争取该书得到发行的正当权利。经过两个多月的交涉,有关部门终于放行,但要求书名去掉“一九七六清明节”的敏感字样。因此,该书书名改为《革命诗抄》后,才得以发行。到1978年3月,这本诗抄先后共印发了二十六万多册。
1976年12月,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的16位教师,自发组织起来搜集和整理天安门诗文。他们把这个小组取名为“童怀周”――取“共同怀念周总理”之意。1977年1月,周总理逝世一周年之际,“童怀周”刻印成一本《天安门革命诗抄》。他们将诗抄在学院内散发,并张贴在天安门广场和王府井大街上。同时,为了能搜集到更多的诗词,他们还在天安门广场公开贴出征集布告,并留下了联系地址和电话号码。这在当时是一个危险的壮举。
北京市公安局立即指令,严密监视“童怀周”的行动。三月,“童怀周”成员之一白晓朗,因在1月8日张贴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的小字报,并被人联系到他编辑诗抄的活动是“社会联系较广、政治背景不清”而被捕。在查抄他的办公室时,那本油印本《天安门革命诗抄》也被抄走。为了防止意外,保存这些诗稿,“童怀周”们一同商量,决定把全部诗稿转移到家住郊区的一个人家里。
白晓朗的被捕,并没有延缓天安门诗稿的征集工作。童怀周的正义行为得到了诸多人的支持。那些曾经留存天安门诗稿的人,按照童怀周在天安门广场留下的联系方式,纷纷将诗稿送来,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的一些干警,也向他们提供了大量的诗词手稿、照片和影印资料。
1977年清明节前夕,童怀周编印出第一本铅印本的《革命诗抄》。7月1日,他们又编印出第二集。11月,他们又在一、二集的基础上进行了校订和整理,并和原拟编为第三集诗文补入,合为一本,定名为《天安门革命诗文选》,在周恩来逝世两周年前后,印刷发行。
印刷发行这些诗文集,都是童怀周成员们自掏腰包,承担了很大的经济压力。因此,在《天安门革命诗文选》印刷发行时,他们标上了“工本费1.20元”的字样。该书前面有30页的反映四五运动的照片,印刷精美,以当时书籍定价来看,这样的“工本费”实在不能说是高。
1977年6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稍后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文学》编辑部的四位同志,也开始从事天安门诗词的搜集和编辑工作。在“四五运动”两周年之际,这本书名为《心碑》的天安门诗文集终于问世。
不过,像《革命诗抄》一样,《心碑》的发行也受到过阻挠。《心碑》发行后,公安部门以外国人弄到了这本书为理由,要求对进行编辑工作的四位同志进行审查,而《世界文学》编辑部的领导则对这种无理要求予以拒绝:“天安门诗抄在香港早已出版了,这有什么稀奇的?!人民的作品为什么不能出版?”该书发行两万余册(参见童怀周主编:《伟大的四五运动》,页241―246;北京出版社,1979)。
这些“非法出版物”在民间广为流传着。人们从诗抄中不仅汲取了文学的养料,而且增加了要求中央改变定性的抗争的决心。
《中国青年》刊登“天安门诗抄”被封存
在此期间,出于对周恩来总理的热爱,一些公开的出版物,也在冲破种种阻力,将天安门诗歌公布于世。
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停刊的《中国青年》杂志社拟定于1978年复刊,复刊后的《中国青年》定于9月11日出版。复刊号有介绍“天安门事件”中勇敢斗争,在“四人帮”疯狂迫害下坚强不屈的青年工人韩志雄事迹报告文学《革命何须怕断头》,还选登了“童怀周”编辑的《天安门诗抄》。
9月10日,北京承印的60万份《中国青年》第一期已全部印完,北京地区已有四万多份邮送到读者手中。
但是,当天下午,共青团十大筹委会负责人韩英接到中共中央一个副主席的电话,具体内容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中国青年》第一期为什么只有叶副主席题词,没有华主席题词。
二、《革命何须怕断头》所宣传的韩志雄,你们了解清楚了吗?这个人有问题。
三、童怀周的《天安门诗抄》怎么又出来了。
四、没有纪念毛主席逝世两周年的文章。
中央副主席的命令自然分量不轻,而且这其中孕含着严厉的指责和批评。韩英不敢怠慢,马上将此意见转达《中国青年》编辑部,并宣布刊物停发,等待研究处理。
编辑部当即作了认真的研究,并正式写出报告,说明情况,大体内容是:第一,关于题词问题是在7月份即向华国锋请求,后又多次催请无结果,现又出国访问在外;第二,关于韩志雄材料由北京市公安局提供,并经多方查证属实:韩系共青团员代表,共青团北京市委已公开号召向其学习;第三,“童怀周”的《天安门诗抄》是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第四,纪念毛主席逝世两周年已有毛泽东1948年为《中国青年》创刊号写的手迹,并在复刊词中专门说到“以表达我们对毛主席的深切怀念”以示特别尊重。
9月11日,编辑部将其上述看法报告给了华国锋及其他几位中央副主席,并同时报给共青团十大筹委会。
9月12日晚,韩英召集杂志社干部开会传达了他同汪东兴共同商定的对这期刊物的四点意见:一、由汪东兴去请华国锋题词(华国锋已出访回国);二、增加毛泽东的诗词三首和照片;三、删去《革命何须怕断头》一文中的“这场伟大壮烈的人民运动被‘四人帮’无情地镇压下去了……”等段落;四、删去《青年革命诗抄》的天安门题图和编者按。
韩英还特地念了华国锋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有关天安门事件和“两个凡是”的段落,说以上两篇文章与华国锋的精神不符,有损毛泽东的形象。
9月13日下午,华国锋的题词送到了编辑部,当晚,编辑部向共青团十大筹委会报告增加华国锋题词和毛泽东词三首,而《革命何须怕断头》与《青年革命诗抄》还是以不改为好。但是,团十大筹委会负责人拒绝了编辑部的这个意见。
在此前后,社会上已对《中国青年》出刊受阻事表示强烈的不满,也有人在西单街头贴出《救救〈中国青年〉》的大字报。
9月14日,编辑部再次上书华国锋及几位中央副主席,阐述理由,表示最好不要删改《革命何须怕断头》及《青年革命诗抄》。
14日晚上,那位中共中央副主席把杂志社小组长以上干部召集到人民大会堂开会。会议在紧张的气氛中从晚上8点一刻开始,一直开到午夜12点50分。会上,这位副主席说:“刚才第一个是讲出版的组织观念,第二个讲文章内容不符合华主席对天安门事件的估价。华主席在天安门问题上早讲过,为什么有人还在上面纠缠?这样行不行?嘴里讲,文章又那么写,现在还这样干,行不行?内容上有这个意见,叫韩英去谈谈,你们不改也可以。中央不知道,将来你们承担责任就是了。这期《中国青年》没有经过中央审查。已经发了四万一千份,得到了赞扬,你们不要挑这个矛盾,好像中央不让出版,筹委会不让出版。”“童怀周的大字报,贴出来,说不让《中国青年》杂志出版。大字报可以写,但《中国青年》第一期到底发生什么影响,你们要考虑一下,如果你们认为这样行,就按你们意见办。”
这位副主席最后说:“已发出的四万一千份换回来。”
《中国青年》复刊的第一期,惊动了华国锋、汪东兴等中央主要领导,也引发了上述一系列风波,但历经曲曲折折,终于“敲”定了。从《中国青年》复刊号的前前后后,也可以看出当时党内的思想斗争是多么的复杂,多么的尖锐(张湛彬:《思想解冻的春天》,页244―248;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年)。
《天安门诗抄》的正式出版
童怀周编辑的《革命诗抄》和《天安门革命诗文选》,“七机部五○二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革命诗抄》编辑组”的《革命诗抄》发行后,他们请《人民日报》社转交给中央领导。《人民日报》社支持他们的行动,立即转交,却招致了中央一位副主席的批评。这位副主席一再下令追查是不是《人民日报》印刷的,是《人民日报》哪个负责人批准印刷的。他特别指出:《革命诗抄》最后一首诗的后两句“总理奇冤今日白,清明旧案何时清!?”,说“这个最坏”。他还说:已经讲过不要再提了,为什么还要提?
在此期间,人民文学出版社也拿到了“非法出版”的《革命诗抄》,他们当然想正式出版,但在当时的形势下,怎样公开出版是要反复考虑的。1978年9月底,他们完成《天安门诗抄》的一切编辑、出版准备工作后,按照“文革”后期的做法,先印了少量的征求意见本分送有关领导人。然后,通过关系打听这些领导人的意见。这些领导人大都希望出版,但又无法公开表态支持。
转眼到了1978年的11月初,虽然中央对天安门事件的定性仍然没有改变,但是,不论是民间还是官方高层,都对改变天安门事件的定性提出了强烈呼吁。在民间,上海热处理厂的青年工人宗福先创作的直接反映天安门事件话剧《于无声处》上演,引起极大的反响。11月4日,《人民日报》率先发表了关于这一话剧演出后的报道,用的是《歌颂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同“四人帮”斗争的时代英雄―――话剧〈于无声处〉轰动上海文艺界》的醒目标题。11月10日上午,《人民戏剧》编辑部邀请首都戏剧界人士举行《于无声处》座谈会。11月14日,应文化部、全国总工会的邀请,《于无声处》剧组晋京演出。“天安门事件”不再是禁区。在党内高层1978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于当时党内外普遍关注的天安门事件,几乎各个组都提出了平反的要求。
1978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新华社电讯稿《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这则电讯稿,本来是在刚结束的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报道中的一段话,在当时中央对这件事情还没有公开明确的说法的时候,新华社单独摘出来发电讯稿,在舆论上推动了天安门事件的彻底平反。
在此前后,新闻媒体密切配合,推动天安门事件的平反。11月17日,《人民日报》第三版上,发表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的《天安门诗抄》的前言和部分诗选;18日,又在第四版以整版的篇幅,发表了天安门群众活动的照片。同日,华国锋为《天安门诗抄》题写了书名。19日,《人民日报》在头版用大字标题刊登了新华社的电讯:《华主席为〈天安门诗抄〉题写书名》。
要求华国锋题写书名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对华的欣然命笔似乎心理准备不足。华的题词送达后,全书早已印好,前言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已不能再改了,也无法以惯例加上一句感谢华主席亲自题写书名的话。只好在扉页反面用红字写明“本书承华主席题签”,连当时通用的“英明领袖”都没有,真是对“英明领袖”的不敬了(黎之:《回忆与思考――〈天安门诗抄〉出版前后》,《新文学史料》2001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