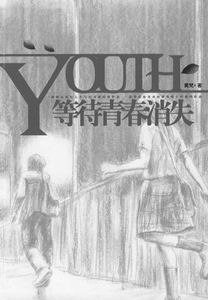 “后新生代”代表作家黄梵的长篇新著《等待青春消失》讲述了一个随处可见的贫穷家庭艰难竭蹶而又力图挣脱现状的生存情境:
“后新生代”代表作家黄梵的长篇新著《等待青春消失》讲述了一个随处可见的贫穷家庭艰难竭蹶而又力图挣脱现状的生存情境:
小说标题“等待青春消失”中的“等待”,在我看来,不仅带有“复指”的意义,而且带有消极、无奈甚至宿命的意味。母亲清月不仅无奈地、宿命地等待着自己青春的消失,也无奈地、宿命地等待着儿子青春的消失;而儿子小楠虽然没有母亲的那份与命运抗争的痛感,但同样也在消极地、无奈地“等待”着青春的失落。令人倍感残忍的是,清月母子的这两种看似不同的“等待”,却都是时代造成的,尽管母亲经历了“当下”的和“前当下”的两个时代,而儿子却只生活在“当下”的时代。
与作者的第一部长篇《第十一诫》相比,《等待青春消失》仿佛因为没有再像前者那样,通篇采用陀斯妥耶夫斯基《罪与罚》式的冷峻严厉、砭骨入髓的痛感语言去深入地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从而显得十分平实;但是细读这部长篇新著的某些章节,仍然会感受到《第十一诫》的语言风格的余绪。如对陈小楠为父亲守灵时的心理描写;如对戴琪出于自然的人性而与雕塑艺人武云飞的那段纯洁而又至美的“感情散步”的心灵描摹;如对清月完全出于下意识的“渴美露美”天性而去探访武云飞,以及与旅馆看门老人“幻情”般的情感展现……所不同的只是因为《第十一诫》的题材,是一种带有更多的“遮掩帷幕”因而显得更加隐秘的知识分子生活,而《等待青春消失》的题材,则是更加世俗更加普遍因而也更加暴露的底层民众的生活。因此,这两部作品的语言风格看似迥然有异,实则血脉相通。正如阅读沈从文的《八骏图》和《长河》时,读者的感觉自然有所不同,但沈从文终究还是沈从文,其潜伏于文字背后的那份“沉忧与隐痛”却又是一以贯之的。
出版者在《等待青春消失》的发行推介语中,称这部作品为“中国版的《在路上》”,就某种意义说来,它的确与生动展现美国的所谓“垮掉的一代”真实生活面貌的杰克・凯鲁亚克的长篇《在路上》存在着某些相似之处。陈小楠以及比陈小楠更加无所畏忌、胡作非为的马林、宋池等人,岂不就是中国的“垮掉的一代”吗?然而,这里更多的只是“比附”的意义,陈小楠们与萨尔、迪安们之间毕竟存在着众多的差异。其中最大的差异就是,迪安们的“反叛”行为带有更大的有意与自觉的成分,而陈小楠们的躁动与不安却充斥着盲目与被动;萨尔、迪安、玛丽卢们大胆妄为地逾越现成的法律与道德界限,目的是希望在与上帝的直接接触中找到“自我”和信仰,因而只能永远“在路上”,而马林、宋池和陈小楠们面对现存的“制度”却只能是浑浑噩噩、自暴自弃,因而最终也只能回归于现实的秩序。《等待青春消失》的作者黄梵是位十分注重“寻异”的作家,他认为对于一个作家而言,最重要的是能够“让视觉和心灵辨得出每个美丽月夜的不同”,而不必让作品死在“哲学”和“思想”的病榻上。因此,我们也就没有必要仅仅满足于《在路上》与《等待青春消失》的比附意义了。
我之所以说《等待青春消失》的语言是富于诗性的,仍然是因为黄梵是一位十分强调个人的感觉与经验的作家。他在《哲学和风格的迷信》一文中明确指出:“没有对生命细节明明白白的理解,也就谈不上对世界的想象与创造”,凭着个人极为敏锐的感觉与经验,努力地去捕捉生命的细节,然后对世界展开丰富的想象与创造,恰恰是保证诗成为诗的一条铁律,而黄梵的底子又恰恰是一位诗人。正因为如此,所以《等待青春消失》的叙事语言,几乎处处充满质感强烈而又异趣横生的想象与创造。比如:“越临近高考,小楠前途的轮廓就越清晰,叫清月产生了临近寒峭雪夜的冷森感”;“为了儿子能上大学,她必须像一根钢发条,把冷酷在心里一圈一圈上足”;医院里“大大小小的花费就像枝头上大大小小的花蕾,争相怒放”;“男孩的哭真是伟大,母亲马上像碰坏国宝似的坐立不安”;“上百个滑稽可笑的腐败故事,在她心里闹腾得就像船上一个个又蹦又跳的孩子”;……想象的奇特,加上夸张与比喻的陌生化处理,使整个文本弥漫着浓浓的诗情。大约也是为了突出“感觉”与“经验”的需要,黄梵在叙事人称的选择上,又有意将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加以交错:对母亲清月的叙写全部采用了第三人称,而对儿子小楠的叙写则全部采用第一人称。这样就在母子的“对视”与“观照”中,既适当地放宽了人物的视野,又打捞到了作家和所写人物更多的心灵感觉与经验,从而使整部小说更富于诗性。除此之外,情节与场景的大幅度省略、跨越与跳跃,也是这部作品的诗性特征之一,因为没有这些省略与跨越,其文本就无法显得如此的凝练与抒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