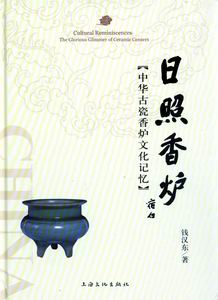 早就听上海田野考古作家钱汉东君说要写一本关于“香炉”的书。记得一次谈到书名,汉东君说拟用李白诗句里
早就听上海田野考古作家钱汉东君说要写一本关于“香炉”的书。记得一次谈到书名,汉东君说拟用李白诗句里
果然,历十余年精勤之功,一部厚重大气的《日照香炉――中华古瓷香炉文化记忆》,终于呈现在了世人面前。在这部书中,汉东君从东周至清代的两千三四百年间,历举约七十类一百六十余种陶鼎和香炉,细细道来,如数家珍。其实,书里所展示、述及的大多数香炉(135尊),就是汉东君的“家珍”――他多年来寻寻觅觅而得来的珍藏。这些正是为“香炉家族”写史的第一手材料。从汉东君的纵谈细说中,我们获知最早的香炉称为熏炉,始见于东周时期,古人用它来净化居室或清洁衣服,到后来香炉才逐渐演化成祭祀的一种主要器具;“香炉家族”在各朝各代繁衍滋荣而多姿多彩,有提炉、琴炉、鼎式炉、如意炉、莲花炉、罗汉炉,有三足炉、五足炉、六角炉、高足炉、竹节炉,有青花炉、白釉炉、黑釉炉、金釉炉、红斑炉、孔雀蓝炉……读文观图,美不胜收,令人叹为观止。而且,不仅是寓目于香炉的形态姿色,还能从中解读、品味出历史的变迁、风俗的影响以及审美情趣和艺术风格的演化等等。真可谓是:随君登堂读“香炉”,悦目益知乐何如!
说实话,对于香炉,我也和很多人一样所知有限。比如,“红袖添香夜读书”一语,这虽出自清代女诗人之手,却道出了旧时多数文人内心的“愿景”,关于此名句中的“红袖添香”,以前我总是以为,是美眉(红袖)往香炉中续添一炷线香。读了汉东君惠赠的这部书,才恍悟自己的理解有点想当然,“添香”其实未必是添线香。汉东君在书中说:“在古代生活中,焚香使用的‘香’,是经过‘合香’方式制成的各式香丸、香球、香饼,或者散末。……古代绘画中女性‘添香’的场景优雅而美丽,而香炉里基本上看不到插线香的情况。在日本、韩国及台湾等地,仍保存此焚香遗风。”经汉东君如此解说,对“红袖添香”豁然明矣。由此想到古人的“焚香沐浴”,也有了通顺的解释:“焚香”是用以洁净衣服,使之有幽香的气味,“沐浴”则是净洗发肤,这两者是为了表示一种庄重和虔诚。当然,用于祭拜的香,应该是线香,如戏剧《拜月记》里,相国千金王瑞兰在后花园焚香对月祭拜,祈祷早日与郎君重聚,她在香炉中焚燃的就应是线香。
孔夫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这里道出了研究学问的三个境界。汉东君多年探究古瓷和香炉,自然是辛苦备尝,如实物寻觅搜求的艰难,如跋山涉水考察的艰辛,如相关资料查找的繁难,凡此种种,汉东君都不以为是苦事,而总能甘之如饴。在书中汉东君写到,有一次他觅得一尊元代仿古影青炉,把它放在书桌上,“心想这尊在地下躺了六百余年的香炉,如今重见天日,来到我的手里,缘分两字真不能不信。后来我又找了许多典籍来研究并考证,我想复原那段消失已久的历史,这是收藏者的最大乐趣。不论是弄清一个小疑惑,还是发现一个新问题,我的心里总是充满了幸福感。”看来,汉东君研究古瓷香炉的学问,不仅达到“知之”和“好之”,而且也进入了“乐之”的境界。
我曾在《寻访中华名窑》一书的读后感中说过,汉东君对古窑遗址的考察,也是对曾在古窑中劳作、创制出无数精妙陶器瓷品的匠人们表达一种敬意。在这部新著中,我同样感受到这样的敬意。汉东君说,历史上多少“英雄”逝去,而先民亲手制作的器物,穿越千年时空,“活”到了今天,成为我们欣赏和研究历史的文物,实是弥足珍贵。汉东君又说到,有一次他走进宋代钧窑的炉膛内,用手抚摸着古老的窑炉,“那一刻我好像成了一名窑工”……汉东君不以自比“窑工”,而觉得降低身份,这分明是对古代窑工怀着一种真诚的敬意。我想,汉东君有这样的情感是很自然的,因为他更能真切地感受到,包括古瓷香炉在内的种种器物,无不凝聚着古代匠人们辛劳的心血,而且也是他们智慧的结晶。古时帝王、贵族和君子们是美好器物的享用者,然而,他们何曾对器物的创造者有过敬意?荀子在《礼论》中曾说:为了区别尊贵卑贱,天子立七代祖先的宗庙,诸侯的可立五代,大夫的可立三代,士君子的可立二代,“持手而食者不得立宗庙”。用双手来劳作的庶人,设立宗庙祭祖的权利完全被剥夺,理由是“积薄者流泽狭也”(功绩小的庶人可流传的恩泽稀少),因此根本不该有资格立庙受祭。但事实上,从天子到士君子,受“持手而食者”的恩泽太多了,他们的衣食住行以及诸般享用,哪一样离得了“持手而食者”?而且,劳动者(尤其是创造性的劳动者)不单是“持手”而已,他们也靠大脑的智慧,他们之中也不乏“大师”,否则他们怎能创造出巧夺天工美轮美奂令后人惊叹不已的无数器物?然而他们曾经被彻底地蔑视,经籍和正史中几乎都没留下他们的名字及功业的记录。而汉东君却以研究古瓷文化的大著,对古代匠人们表达了足够的敬意,他深深铭感着没留下名字的古代创造者们,他为他们立了功德碑,在他的心里,在他的书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