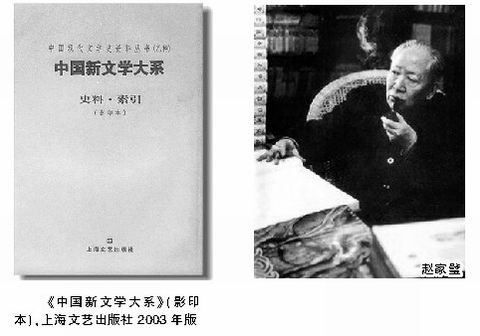
1
1935年,一部“声势浩大”(茅盾语)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开始问世。当年5月,随着《小说一集》出版,第一炮打响,7月,又是两种问世;8月出版三种;最后一种《史料・索引》遇见麻烦,可也于次年(1936
这部不仅当时产生极大反响,几十年后又重新影印精装出版的《大系》,是由一位刚从大学毕业两三年,年纪不过二十五六岁的年轻人主编成功的。这位年轻人,就是后来成为著名出版家的赵家璧。这部《文学大系》,分建设理论,文学论争集,小说、散文、诗歌、戏剧、史料索引等七部分。其中小说分三集,散文分二集,其余各一集,总共十集。这十集的分卷主编皆为当时重要的文化名人,例如胡适、鲁迅、郑振铎、茅盾、郑伯奇、周作人、郁达夫、朱自清、洪深、阿英……除去分卷主编人为每集写一长篇导言(要求2万字),还请德高望重的蔡元培撰一总序。难怪后来茅盾称此项工程“声势浩大”。
这部《大系》的分集主编人,几乎全是当时的不二之选。(亡命日本的郭沫若亦在被邀之列,主编诗歌卷。他本人亦同意参与,可后因政府当局反对,不得已放弃)以文学观念论,这些分卷主编人又并非一致。从这个角度看,这部《大系》主持者赵家璧是超越了当时以派分别限界的,这充分保障了此部大书的涵盖面和质量,确属难能。可是,在分卷主编人的选择上,又并非完全没有异议。譬如当时在左派文学人士看去有些偏右的胡适,思想有所“退坡”的周作人……但在完成主编任务中,这些人同样全力以赴,表现出别具的胸怀和眼光,例如选编散文的周作人,就与另一位编选者郁达夫,进行了一次良好的分工合作。
2
据《大系》主编者赵家璧回忆,当时找散文集编选者时,他曾与郑伯奇、郑振铎、阿英、施蛰存等个别交换了意见。大家首先想到的是郁达夫,这没有问题;另一位,赵家璧最初拟请的,是周作人,这却遭到一些人的反对。论当时的散文成绩,周作人当然是合适人选,可在左翼作家眼里,他的思想有些“退坡”,不甚“激进”了,因而表示反对。赵家璧在征求茅盾意见时,茅盾却认为,“大系”既请了胡适担任《建设理论集》的编选,散文集请周作人编选一卷也无不可。茅盾还认为:这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嘛。赵家璧一听,正中下怀,当即决定请周作人、郁达夫各负责分别编选一集散文,并进一步建议,可否以地区划分来选:周作人久居北方,请他选北方的散文家;郁达夫多在南方各地跑,可请他选南方的散文家。茅盾以一个行家的角度说,小说以团体分,较为合情理;散文的分工较难,将来最好由郁、周两位自己去商议吧。应当说,对于两位有个性、有见解的散文大家,茅盾的建议是恰当的。
赵家璧与郁达夫较为熟悉,所以较早去函杭州,约定下来。周作人当时在北平,赵家璧便先写信给友人郑振铎,一方面征求他的意见,另一方面想请他就近帮助约请周作人。不久,接到郑振铎的函,表示周作人已同意参与。赵家璧便自己写了一封恳切的信,感谢周作人能参加《大系》编选工作,同时将两份约稿合同一并寄给郑振铎,请他转交周作人。
不久,周作人给赵家璧回复一函,对《大系》的编选思路,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想法:
“从郑先生转来合同,今仍将一份寄奉,乞察收。大系规定至民十五年止,未免于编选稍为难,鄙意恐亦未能十分严格耳。有许多材料不能找到,将来尚须请尊处帮助。”
周作人的这些想法,与另一位散文编选者郁达夫不谋而合。在《大系・散文二集》“导言”里,郁达夫这样说:“原定体例,是只选自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七年之间的作品。但被选的诸家,大抵还是现在正在写作的现代作家(除两位已故者外),思想与文章,同科学实验不同,截去了尾巴,有时候前半截要分析不清的。对这问题,我和周先生所抱的,是同一个意见,所以明知有背体例,但一九二七以后的作品,也择优选了一点,以便考证。”这也是后来他们两人所选散文略略逸出《大系》规定时限范围的缘由。
3
周作人、郁达夫承担的散文任务,究竟如何选择,两人是颇费了一些脑筋的。最初,他们想以文学团体来分。例如郁达夫曾是创造社成员,对这批人的创造比较了解,他就承担这一部分;周作人是文学研究会成员,与语丝社同仁也相当熟悉,由他来编选这部分作家,就显得十分自然。可后来经过思考,自己选自己的作品,难免不易割爱;同理,对亲近友人作品,也难保不怀偏见。
当时,周作人在北平,郁达夫居住杭州,不能面谈,只好信函往来相商。以文学团体分别编选的思路,他们在通信中最终否定了。理由如上。后来郁达夫又想出一条路子:能否依当时的流派为标准,即“言志派”与“载道派”。这一点,后来两人又否定了。周作人对此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我看文艺的段落,并不以主义与党派的盛衰为唯一的依据,只看文人的态度,这是夹杂宗教气的主张载道呢,还是纯艺术的主张载道呢,以此来决定文学的转变。现在还是混乱时期,这也还难说,因为各自在那里打转身,似乎都很少真有明确态度。”
郁达夫于此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谈到了这一个派别问题,我们又各自起了怀疑。原来文学上的派别,是事过之后,旁人(文学批评家们)替加上去的名目,并不是先有了派,以后大家去参加,当派员,领薪水,做文章,像当职员那么的。况且就是在一人一派之中,文字也时有变化,虽则说朝秦暮楚,跨党骑墙等现象是不会有,可是一个人的思想、文章、感触之类,决没有十年如一日,固守而不变的道理。还有言志和载道的类别,也颇不容易断定,这两名词含义的模糊,正如客观和主观等抽象名词一样的难以捉摸。古人说:‘文以载道’,原是不错,但‘盍各言尔志’的志,‘诗言志’的志,又何尝不一样的是‘道’?‘道其道,非吾之所谓道’,那这一位先生所说的话,究竟是当它作‘志’呢还是作‘道’?”
最终,两人商定,以人为标准,分别取舍。这方法应当是周作人提出来的。他曾在后来回忆这段经过时写了这样的句子:“我还记得有一次,良友图书公司发起‘中国新文学大系’,集刊五四以来十年间的成绩,叫我和达夫编辑散文部分,那时我与达夫通过好几回信接洽分配人选的问题,由我择取若干人为散文集一,余下的凡是我所不熟悉或是不便选择的人,全归他去编选,我的这种‘任性’的办法居然为他所接受,这在我是觉得非常愉快而且应当感谢才是的。”(《郁达夫的书简》)
4
具体人选如何分配,郁达夫有致周作人一函,谈得很详细,并有幸保存了下来。从中我们可以知道许多当时的情形:
“启明先生:一月十三日的信,拜读了,以人名决定界限,最直截了当,我们以后,只须想出人数,各补各的不足好了。赵家璧又有信来,新提意见却并不妙,所以又去信复他,告以已决定的标准了。在这信中,再加上几个名字罢,以后你有所见请通知我,我有所见,当通知你。”
由信中可以看出,当时两人分列的名单,大致如次:
周作人选:郁达夫、徐志摩、庆言、俞平伯、郭沫若、刘半农。此外,郁达夫还据自己的阅读,认为还应当加上:徐祖正(及《骆驼草》时的散文),江绍原(及除林语堂、鲁迅外之《语丝》散文),另有几人,郁达夫均打了问号,大概是征询可否入列。他们是:钱玄同、李守常、顾颉刚;其他还列有:春苔、庐隐、沈从文、绿漪、凌叔华、高一涵;还在括号中注了“浅草社同人”。
郁达夫自己所选:周作人、冰心、鲁迅、朱自清、叶绍钧、林语堂;并以为还应当加上:川岛、创造社除郭沫若外其他人的散文、茅盾、蒋光慈、丰子恺、钟敬文、田汉、谢冰莹、许钦文、冯沅君、丁玲,还有湖畔诗人等……浅草社同人,郁达夫列了陈炜谟和陈翔鹤两位;湖畔诗人,郁达夫列有冯雪峰、修人、汪静之三人。
如何这样分配呢?郁达夫后来曾谈及:“譬如我选周先生的散文,周先生选我的东西,著手比较得简单,而材料又不至于冲突。于是就和周先生商定,凡鲁迅、周作人、冰心、林语堂、丰子恺、钟敬文……茅盾几家,归我来选,其他的则归之于周先生。”
对于郁达夫提到的那份名单,周作人自己又有所取舍。添加了几人,又减了几人,并在排序上,有所安排。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认识上:
一、有四位已故的人,即徐志摩,刘半农,刘大白,梁遇春,他们都列在卷首。所选文章也不以1926年为限,周作人称这是一个例外。这当然包含有对逝者尊重和纪念的意味。
二、加入一位吴稚晖。(周作人特意加注,活人也一律称名,不加“先生”)因为他虽“实在是文学革命以前的人物,他在《新世纪》上发表的妙文凡读去的人是谁也不会忘记的。他的这一种特别的说话法与作文法可惜至今竟无传人,真令人有广陵散之感。”为引发人注意这“奇文”起见,特别选录了两篇以示尊重。
三、因“大系”标明为散文,议论文照例不选入。所以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钱玄同,李大钊等人的作品便没有入编。可顾颉刚的一篇《古史辨序》却格外开恩选录,“因为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自叙”。
四、“废名所作本来是小说,但是我看这可以当小品散文读,不,不但是可以,或者这样更觉得有意味亦未可知。”基于这样的认识,周作人便从小说《桥》里选取了六则入集。
五、有些人当收未收,如梁实秋,沈从文,谢六逸,章克标,赵景深等,因为他们的大部分著作都在1926年之后,所以只好割爱。
……
在此期间,主编赵家璧还曾去快信向周作人询问有关情况,周作人复了一函,从中也可见大致情形:“快信敬悉。散文分选前西谛(即郑振铎)亦有以性质区分之说,但事实上甚不容易。达夫来信拟以人分,庶几可行,已复信商定人选矣。”当然,这样地分配,包含了两位大家对散文的见解。周作人曾在“编选感言”里这样表达过:“对于小说、戏剧、诗等,我不能懂,文章好坏似乎知道一点,不妨试一下子。选择的标准是文章好意思好,或是(我以为)能代表作者的作风的,不问长短都要。我并不是一定喜欢小品文,小品文这名字我也很不赞成,我觉得文就是文,没有大品小品之分。”
5
最终,周作人与郁达夫编选的集子完成了,可从实际的选择结果看,两人又都在其中表现了自己的鲜明个性。譬如,周作人的《散文一集》,实际选入了徐志摩、刘大白、刘半农、梁遇春、郁达夫、郭沫若、俞平伯、废名等17家,共71篇;每人至多8篇,少的仅1、2篇。郁达夫的《散文二集》,共选16家,文131篇。其中冰心,林语堂、丰子恺、川岛、朱自清、郑振铎、叶绍钧、茅盾等,每人多则5、6篇,少的仅1篇;可是,鲁迅却选入24篇,周作人更惊人,选了56篇。对周氏兄弟散文的喜爱,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按照《大系》主编者的要求,每集前面应有编选者二万字的长文介绍。周作人与郁达夫也都勉力做了。字数也许不足,可篇幅在他们文章中,却算是很长的。周作人如他中期其他文字一样,大量引述他人,尤其自己先前对散文的各种零星看法,算是把自己对散文的见解规整了一下。郁达夫的“导言”,则从散文的“名”、“外形”、“内容”,以及“现代的散文”几方面,阐述了自己对散文的见解。其中,他对所选作家的“妄评一二”,却写得很有意思,对自己格外大选特选的鲁迅、周作人,予以了评点。说得很精彩,值得略加引述:
“鲁迅的文体简练得像一把匕首,一刀见血。重要之点,抓住了之后,只消三言两语就可以把主题道破――这是鲁迅作文的秘诀……与此相反,周作人的文体,又来得舒徐自在,信笔所至,初看似乎散漫支离,过于繁琐!但仔细一读,却觉得他的漫谈,句句含有分量,一篇之中,少一句就不对,一句之中,易一字也不可,读完之后,还想翻转来从头再读的……近几年来,一变而为枯涩苍老,炉火纯青,归于古雅遒劲的一途了。”
郁达夫比较两人的文字风味:“两人文章里的幽默味。也各有不同的色彩:鲁迅的是辛辣干脆,全近讽刺,周作人的是湛然和蔼,出诸反语。”由思想引致态度:“他们的笃信科学,赞成进化论,热爱人类,有志改革社会,是弟兄一致的;而所主张的手段,却又各不相同。鲁迅是一味急进,宁为玉碎的,周作人则酷爱和平,想以人类爱来推进社会,用不流血的革命来实现他的理想。”
“周作人头脑比鲁迅冷静,行动比鲁迅夷犹……”“鲁迅的性喜疑人――这是他自己说的话――所看到的都是社会或人性的黑暗面,故而语多刻薄,发出来的尽是诛心之论;这与其说是他的天性使然,还不如说是环境造成的来得恰对……在鲁迅的刻薄的表皮上,人只见到他的一张冷冰冰的青脸,可在皮下一层,在那里潮涌发酵的,却正是一腔沸血,一股热情;”“周作人的理智既经发达,又时时加以灌溉,所以便造成了他的博识,但他的态度却不是卖智与炫学的,谦虚和真诚的二重内美,终于使他的理智放了光,博识致了用。”
郁达夫甚至这样说:“中国现代散文的成绩,以鲁迅周作人两人的为最丰富最伟大,我平时的偏嗜,亦以此二人的散文为最所溺爱。一经开选,如窃贼入阿拉伯的宝库,东张西望,简直迷了我取去的判断,忍心割爱,痛加删削,结果还是把他们两人的作品选成了这一本集子的中心,从分量上说,他们的散文恐怕要占得全书的十分之六七。”
虽然,郁达夫对其他如冰心、林语堂、丰子恺、钟敬文、朱自清、王统照、叶绍钧、茅盾等人的点评,也颇多确当见解和精妙文字,堪称一篇不可多得的作家风格谈。结语
《中国新文学大系》,从开编到出齐,不过一年多一点时间(本来可以一年内出齐,因阿英父亲出事,略有耽误,他负责的一册延至次年2月出版)。之后,虽然主编者赵家璧还颇有野心,想接续再编下去,可惜,日本人的入侵,使得良友图书公司损失惨重,随即宣告破产,后几经努力,仍无结果。这样一项有绝大价值的工程,便由此停顿下去。所幸的是,留下了这部由当时文坛各领域领军人物编选的十大卷集子,为新文学最初十年留下了珍贵的资料和实绩,仅此功劳,亦堪称卓绝。其中编选者通力合作,也展示了各自风采。仅从周作人与郁达夫编选散文过程的分工合作,亦可看出他们对文学事业的虔诚和别具的眼光。这部“大系”,数十年后重新精印再版,显现了其长久的价值。所以,记录其中两位学人的通力合作,一窥当时人的精神风貌,由文至人,我们对这部“大系”的领会,也许就能更为全面,更为丰富,对其中的特别价值,应当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