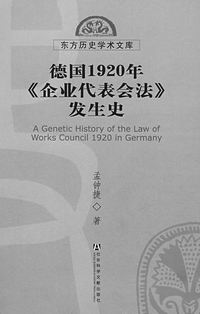
劳资关系是市场经济社会的经典难题。在这方面,德国在西方国家中属于比较成功的。有数据表明,在
从“企业苏维埃”到“企业代表会”
正如孟博士的导师郑寅达教授在该书序言开头所指出的那样:大多数中国读者或许会对德国的“代表会”之类的概念感到陌生,但如果把“代表会”改译成“苏维埃”,许多读者就会想起俄国十月革命和德国1918年十一月革命那段如火如荼的岁月。该书的研究对象正是德国1918年十一月革命中诞生的、在革命后法制化、规范化的企业工人与职员组织,即所谓的“Be鄄triebsrat”。其中“Betrieb”是指“企业”或“工厂”,而“Rat”既可以译为无政治色彩的“代表会”、“委员会”,也可以译为革命色彩浓厚的“苏维埃”。对于中国学者来说,这或许只是一个翻译问题,而在当时的德国则存在着一场对概念及其所指组织内涵的争夺。在同一概念掩盖下的“企业苏维埃”与“企业代表会”代表着当时德国社会极为不同的劳资关系模式设想。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强弱悬殊的政治势力的博弈使得“Betriebsrat”最终未能成为“企业苏维埃”,而只是成为了“企业代表会”。
1918年深秋,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革命爆发,基层民主式的工人士兵“代表会运动”(或者说“苏维埃运动”)席卷德国。帝制被推翻,共和国成立,因次年在文化古城魏玛举行的立宪会议而得名“魏玛共和国”。极左翼的独立社会民主党与德国共产党试图建立俄国式的“苏维埃共和国”,在经济领域建立“企业苏维埃”,掌控对企业的“完全控制权”。然而,代表会运动并未能够彻底颠覆帝国的政治与经济制度,已经被帝国政治制度驯化的社会民主党主张建立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左翼的暴动遭到镇压,政治性代表会运动失败。在此大背景下,经济领域的代表会运动,作为政治性代表会运动的承诺与继续,自然不能建立掌握企业“完全控制权”的“企业苏维埃”,而只能是改良主义的、在承认企业主的主导权前提下增加工人的部分“共决权”的“企业代表会”。
《企业代表会法》的实施与失败
1920年2月正式施行的《企业代表会法》规定,所有拥有雇员20名以上的企业必须成立企业代表会,雇员少于20名的企业必须设立企业代表,企业代表由雇员选举产生。企业代表会的主要职责在于支持企业主的经营与管理工作,但也在不挑战企业主主导地位的前提下维护雇员的利益与权利。企业代表会甚至可以派代表参加监事会并拥有投票权。企业主在雇佣与辞退大量雇员时必须征求企业代表的意见。应该说,《企业代表会法》在维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前提下,在相当程度上提高了雇员在其中的地位,维护了他们的利益。在1920年代,企业代表会的推广也颇具规模。到1929年,德国共有46299个企业成立了企业代表会,涉及雇员590万人,共选举产生15.6万企业代表会成员。但是,而这种劳资合作模式的实践结果却是失败的,让劳资双方都很失望。工人阶级觉得它没有充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资本家则感到企业代表会是在干涉其企业主权。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后不久,就颁布了《关于劳动信托人法令》与《国民劳动秩序法》,取消了企业代表会法,把企业主与工人职员之间的关系转化为“企业领袖――追随者”之间的关系。同时设立中立的“劳动信托人”,调节劳资之间的关系。魏玛共和国是德国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温和派相互妥协合作的产物。希特勒的上台与企业代表会的取消,标志着德国劳资阶级在国家与企业层面都失去了自主调节相互关系的能力。他们宁愿接受一个独裁者最不公正的裁决,也不愿意自主地做出微不足道的让步。最终的结局世人皆知,不过这已经是后话。
本书选题新颖、资料详尽、思路清晰,是近年来德国现代史研究的上乘之作;又出于一位潜心研究德国历史而同时关心中国现实的年轻学者之手,更是显得难能可贵。作者在结尾写到,“德国劳资关系演进的历史或许正是中国推进企业改革的一种参照。在这个意义上,本书对1920年德国《企业代表法》的历史研究不仅是从微观认识德国历史演进的尝试,也蕴含着笔者对于当下中国发展命运的忧思与关注”(第287页)。不过,由于该书属于微观研究,涉及的范围与时段较小,读者在掩卷之余难免会有兴犹未尽的感觉。德国历史充满着对于我们有益的经验,但并不是每一小段历史所展现的都是我们可以直接学习与借鉴的榜样。有时我们看到的更多是惨痛的教训,或者经验与教训盘根错节般的混杂物,或者是未完待续的“历史进行时”,最终的结论只有在几十年以后才会出现。本书的内容也不例外。就德国劳资关系史而言,书中的核心问题到20世纪末德国统一时才得到了回答。对于德国历史的细节,一般中国读者缺乏与专业人士一样的兴趣与耐心(除非是关于希特勒与二战的),他们更愿意看到的或许是关于19世纪中期以来德国劳资关系演变与结论的综述以及20世纪下半叶德国劳资成功合作模式的个案研究。不过,以在本书中表现出来的研究水准,相信作者在未来一定能够在此领域做出更好、更为“实用”的研究成绩。这样说来或许有些“急功近利”,但也确实是我们的“国情”。
寻找劳资关系的黄金分割点
在书中,就本书内容对于二战后德国劳资关系史的意义以及对当今中国劳资关系的有益经验与教训,作者“发挥”不多,严谨的历史研究也应该如此。在这里笔者愿意多说几句,暂且当作该书的一个“补注”。
“企业代表会”在魏玛共和国的尝试虽然失败了,但它仍是一个蕴含着合理因素的劳资关系模式。二战后,它在西德又得到了继承。在市场经济的框架下,工人与职员获得更多的企业管理权。如1951年的《共决法》规定,在矿山冶金业的董事会中,劳资双方享有同等数量的董事席位,另设一位双方共同推荐的独立董事。1972年的《企业宪法》扩展了工会与企业代表会的参与权。1976年的《共决法》又将1951年法案的适用范围扩大到所有雇员超过2000人以上的大企业。在工资谈判方面,如果劳资磋商再三,犹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罢工作为劳方的最后施压手段并没有被排除,但工会又设计出了一个以稳定为重的处理办法:罢工的决定,获得全体雇员的2/3的支持才算通过,但复工的决定只需超过1/3的投票就可以生效了。
而在东德,工人阶级的政党社统党(即“德国社会主义统一党”)获得了国民经济与国有企业的“完全控制权”,但也必须从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出发,努力实现现有资产的增值,难免也要提高劳动强度。然而,社统党的难处并没有得到工人的理解。1953年夏,社统党提高柏a到了工人的强烈反抗,并且引发了东德历史上第一次全面的严重政治危机。在此以后,社统党再也不敢得罪工人阶级。为了维护政治稳定,也为了在制度竞赛上不落后于西德,东德政府必须维持其经济水平难以承受的就业与福利负担。到1980年代末,在其政治上瓦解之际,东德经济已经抵达破产的边缘。
东德经济模式的失败,从反面证实了市场经济生产关系以及资本增值视角的不可或缺性。在市场经济中,企业主出于个人利益,充当着企业资产的增值追求的代表者,客观上保障着企业生产的高效率,促进着经济的发展。但这并不是说,企业主可以因此为所欲为,随意践踏工人的权利与利益。工人不仅有权在生产过程之后从企业主那里讨回其劳动成果的“剩余价值”,而且更有必要反击企业主借实现效率之名夺取对他们生活的“剩余权力”。必须分清哪些属于企业主为指挥生产、实现利润所不可缺少的权力与利益,哪些与此无关,而是属于工人与职员的正当权利与利益。用作者的话来说,也就是寻找劳资关系的“黄金分割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