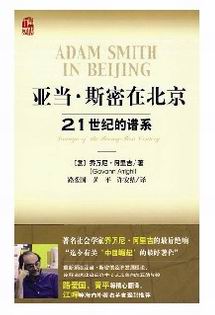
“具有资本主义特征的资本主义”无疑是同义反复。我只想说明这个词在本书中所代表的特定涵义。罗伯特・布伦纳指出,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批判的资本主义需要满足两个条件:其一,资本家成为资本职能的执行者,因而他们具有利润最大化的倾向;其二,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成为无产者。马克思是逻辑彻底的伟大理论家,他认为资本的力量是无坚不摧的。资本会武装自己,对内盘剥劳动者,对外开拓国际市场,获取廉价的生产资料。最终世界上任何蛮荒的角落都会被卷入资本所创造的世界体系之中。马克思意识到这种体系的不稳定性:劳动者与资本之间的冲突无可避免,因而“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为无产阶级的壮大打下基础,同时也为自己准备着掘墓人”。
阿里吉则认为,斯密提倡的基于市场的扩展秩序并不需要以上述两个条件为前提,原始积累――伴随着对农业生产者的剥夺的积累――是资本主义的结果而非先决条件。西方的增长路径确实不可持续,但既不是因为劳资纠纷不可调和,也不是因为创新性在异化中被毁灭(熊彼特),而是世界政治格局所决定的。即使坚船利炮横冲直撞、所向披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霸权也不可维系――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就是最好的例子。新的、更加平衡的世界秩序将在二十一世纪形成,它仰赖新生的活力,它来自东方,来自日本、中国和东亚国家。在阿里吉设想中,这些国家代表一种不同的、具有潜力的增长模式。
我是怀着感激和钦佩的心情阅读这本书的。阿里吉对中国寄予厚望。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一个政治托词和意识形态软着陆,而是一种真实的、可以付诸实践的理想。与西方的经济增长相比,中国的经济奇迹特殊在哪里?阿里吉认为,中国自1800年以来的革命传统和长达千年的农本社会塑造了独特的社会结构和价值理念,这使得中国近三十年的经济成长具有了明显斯密特点。具体来说,第一,在要素禀赋方面,由于农民未被剥夺,他们大多拥有土地,且分配较为平均。农民在农村享受了一份“制度工资”:由于他们能从土地上获得一份保障性的收入,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要价就相对较低,因而能为中国的工业化提供大量的低价劳动力。
第二,平等均匀的社会结构,这是二百年来中国革命的遗产。费正清教授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一书中写道:“1800年以来的现代中国已经进行了两次革命……其中一次是想用各种现代技艺把中国建成一个和外国相同的现代工业化国家,另外一次是在中国农村社会群众之中进行的社会革命。”我们谁也不能证明在农村消灭地主阶级可以通过逐渐进化而不经过暴力来实现,不能证明大规模增加人民群众识字的人数和迅速建立政治组织是一件在历史上无关紧要的事。阿里吉引用汪晖教授的话说:“社会主义传统是一种价值观的约束,底层民众(工、农)有抗议的合法性。”这部分解释了何以中国政治没有与精英集团结盟(虽然近来有这种倾向),而在一定程度上照顾了底层民众的利益。
第三,阿里吉认为,1978年以后中国政府基本上遵循了斯密的教导:谨慎的渐进改革、促进劳动分工、大量投入教育、使资本家的利益服从于国家利益、促进资本家之间的竞争――换句话说,政府利用市场作为规制贸易的工具。也就是说,在改革初期,中国政府是相对超然于资本的。
从全局的视角来做判断,我同意阿里吉的看法:政府在改革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改革本身具有实现个人自由和以人为本的特点。不过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正如阿里吉所担心的,中性政府的基础可能正在丧失、弱势者的生存境况可能正在相对甚至绝对的意义上变得更加糟糕。
作者的逻辑并非完全没有问题。首先,作者认为西方关注物质,走的是资本密集、能源消耗型的外延式增长路线,东亚则关注人的发展,走的是内拓式的增长路线。但这样的路径选择是否与要素的丰裕程度有关――当劳动力极度富裕时,自然会更多地使用人力。不过阿里吉倒是提了一个好问题:既然人力如此丰裕,为什么大家还那么热心地投资于人力资本?因为农业社会历来关注人?阿里吉的观察可以用经济学里的多任务问题来解释,对此,姚洋教授已有论述(《重新认识中国的小农经济――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的一种解释》)。其次,中国的工业化道路是否是资源节约型的,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中国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是否能够避免重工业化,在国内经济学界已争论数年。其三,农民手中的几亩土地能够提供多少保障?土地流转是否会使农民的境况变坏?这些都需要实证研究的检验。最后,超然于资本的中国政府――如果之前大体是那样的话――还能超然于资本多久,如果它仅仅被“传统”约束?中国式的增长奇迹是否有可能拒绝其他国家――包括西方的――相对成熟的政治经验,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这是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意]乔万尼・阿里吉著,路爱国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6月第一版,39.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