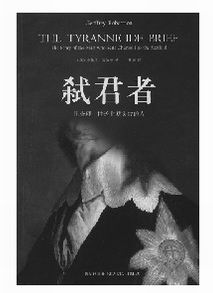 查理一世发起内战,使得十分之一的英国人在战争中丧生。1649年的议会却找不到一个有才华和勇气的律师来起诉自称高于法律的国王。约翰・库克最后临危受命,以清教徒的虔诚和对公民自由的热爱挑战“君权神授”,把
查理一世发起内战,使得十分之一的英国人在战争中丧生。1649年的议会却找不到一个有才华和勇气的律师来起诉自称高于法律的国王。约翰・库克最后临危受命,以清教徒的虔诚和对公民自由的热爱挑战“君权神授”,把《弑君者》,[英]杰弗逊・罗伯逊著,徐璇译,新星出版社2009年4月第一版,39.80元
国际知名人权律师杰弗里・罗伯逊的著作《弑君者:把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的人》(新星出版社,2009年)为一个曾参与审判查理一世、几被后世遗忘的律师约翰・库克立传,以丰富的史料和独特的视角再现内战时期及其前后的英国风云,也为我们了解17世纪英国司法发展史以及现代律师职业规则的起源提供了许多生动的细节。
柯克:法律高于“国王的事业”
罗伯逊借本书向一位三百多年前的业界前辈致敬,同时也是赞赏传主的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念:自由和法律高于王权――这正是十三世纪《大宪章》诞生以来,经过无数次与国王的冲突之后,英国人民所秉承的传统理念。《大宪章》最初的基本原则是保护贵族的财产与人身权利免遭专制王权的侵害,但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它所保护的权利逐渐扩展到平民阶层,在内战前后成为人民抗议王权的武器。当时,人们在激烈辩论中经常引用《大宪章》作为立论的根据。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库克的律师前辈、曾任詹姆士一世首席法官的爱德华・柯克居功至伟。
来自苏格兰的詹姆士一世信奉“君权神授”,显然不了解也不愿理解英格兰及其议会传统,曾极为自信地宣称:“一个经验丰富的君主根本不需要英格兰议会的任何教训。”(布伦达・拉尔夫・刘易斯《君主制的历史》,页128,三联书店,2007年)其宠臣培根迎合他说,法官就像“王座下的狮子”――这意味着“国王的事业至上”,毫无司法独立可言。我们知道,这样的司法只能沦为行政的附庸。无限期拘禁、秘密审判、有罪裁决、刑讯逼供、非法证据、禁止交叉问询、拒绝证人出庭、威吓律师等等被逐出真正的司法制度之外的玩意儿,都会大行其道,让权力成为每一个公民挥之不去的梦魇。查理二世复辟后操纵司法对所谓“弑君者”进行疯狂的报复,就是显例。
然而,柯克给詹姆士一世上了一堂“法律高于国王”的课。詹姆士自比神赋的最高法官,柯克不以为然:“就算国王是上帝指定的天才,他还是该受普通法的约束。法律是衡量王权由来的黄金尺度和工具,也只有靠法律,王权才得以安全与和平。”国王暴跳如雷,下令:“如果谁胆敢再发表君王在法律之下的言论,就是叛国罪。”(《弑君者》,页18)
柯克后因反对詹姆士提议对涉及自己的案件召集法官密商而丢掉职位,成为斯图亚特王朝的反对者,并撰写了著名的《法学总论》――这本书成为库克这一代法律学生的教科书,教导他们要将《大宪章》敬为英国人民自由之源。在议会跟查理一世斗争的时期,议会曾要求国王批准由柯克起草的《权利法案》。法案赋予《大宪章》高于一切的法律约束力,并解除国王任意裁决人身监禁的权力,自然为查理一世所拒,但其后通过的《权利请愿书》实质上仍延续了此一思路。(《弑君者》,页18、25-26)柯克的努力造成《大宪章》在普通法(以习惯法为主)里不可动摇的地位,故他曾自诩为普通法的主要设计师。柯克认为:《大宪章》“是英国所有基本法律的根源,它不仅确认,也奠定了习惯法治基础”。罗伯逊也指出:《大宪章》在17世纪经由柯克之手才成为“自由的声音和力量”。此后,《大宪章》的声音响彻云霄,遍及世界,被誉为“英语世界的自由基础”、“保护自由精神的咒文”。(梅尔文・布莱格《改变世界的12本书》,页76-81,联经出版公司,2008年)如今,《大宪章》精神所及之处,就意味着君主向法律低头,专制统治终结。
李尔本:平民推动对抗式程序
李尔本以平等派领导人知名,但其实他注定是英国法律史上的传奇人物:1637年因私运“反动小册子”而被捕时,他拒绝回答星室法庭的讯问,声称作为“生而自由”的英国人,有权利拒绝“自证其罪”――这就是闻名后世、保护无辜被拘禁者的“沉默权”的起源。(《弑君者》,页42、86)
1649年,李尔本因煽动士兵造反而被诉叛国罪。其时,平等派已式微,但李尔本并未退出历史舞台。罗伯逊写道,这年10月对李尔本的审讯应列为法律史上最重要的刑事审讯之一,因为他第一次在法庭上“把英国刑事审判转变成了一个抗辩式的法律程序,此前,被告的罪行是假定的,却没有机会辩解”。李尔本在此展现了其杰出的辩论能力,一开始就要求公开审判:“一切法庭都应当对所有遵守法庭纪律的民众开放,任其了解、观看和听审,要有条通道给他们自由进入;无论是谁都不应该在洞眼后和角落里,在一个被紧闭的地方受审。”法官基布尔微笑着打断他:“李尔本先生,请转过身去看看门是开着还是关着。”门已经开了,李尔本的一众支持者正整齐地坐在公众席上。李尔本的责难促使诞生了现代司法制度中最基本的原则:法官审案时,门必须开着。“那样全世界都知道本法庭对你进行的审讯是如何正直公义。”(《弑君者》,页220-222)
审讯中间,李尔本又挑战了陈述案情时被告不得进行辩护的规定。他强烈主张被告有权让律师就事实争议焦点进行辩论和对证人进行交叉询问,对下个世纪发生的法律改革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还干脆请求陪审团取代法官这一传统角色来依法进行裁定。最后,他请求休庭以恢复体力,法官拒绝并命令他别磨蹭了。这时,李尔本开创了他的最后一个先例――审讯中必须保证犯人在其位子上身体舒适:“先生,如果你要这么残酷不让我离开去方便一下,休息放松的话,那请你让我在法庭上就地解决吧。长官,我求你――给我一个夜壶吧!”法官们目瞪口呆地看着郡长提来夜壶,李尔本朝里面小便,然后交给陪审团主席。最后,陪审团裁决其无罪,这让正在征服爱尔兰的克伦威尔大吃一惊。这场审判之意义也可以从法官们的“审判者将被审判”的自我认知中看出――法官们意识到,他们正在为未来的叛国罪审讯创建一个先例,所以一开始就提醒李尔本说:“(不单是你),我们自己的生命也在受审。”在罗伯逊的笔下,这些场面读来令人动容。可以说,由于李尔本的抗争与法官们的清醒,才共同开创了一个公正审判的先例。(《弑君者》,页224-225)
库克身上也有这种“审判者将被审判”的清醒意识。早在查理一世被行刑后不久,库克就在《国王查理一世审判案》的后记中写道:“如果法官们有人变成暴君或依法同意建立起任何形式的暴政或妄图残忍地破坏及奴役本国自由人民的良心、人身和财产,则他们也同时对自己宣判了死刑。”(《弑君者》,页196)他后来当法官时,公正执法,认为“即使是罪大恶极者也应得到公正对待。我不敢冤枉任何人,因为我知道审判日来临时,我将同他们一起接受审判”。(《弑君者》,页310)但是,这种清醒意识在那些“国王的事业至上”的法官身上是看不到的,比如查理二世复辟时期,法官布里奇曼推翻了半个世纪以来的立宪成果,使英国再度置于专制制度之下。在布里奇曼主持的弑君案审判中,借由篡改司法程序、任意扭曲法律条文、拒绝辩护等等,对库克等人做了有罪判决。(《弑君者》,页299-333)
库克:首倡律师“计程车规则”
库克最重要的历史贡献除了审判国王外,也许就是针对当时的司法状况提出了一系列的法律职业规范。笔者最感兴趣的是律师职业伦理上的一个原则:“计程车规则”。按库克的阐释,这条原则就是:如果给予适当的报酬,律师的职责就是接手案件并尽其全力为委托人辩护,不论自身安危与荣辱如何。1649年1月,绝大多数律师都逃之夭夭以避开议会对国王的审判时,库克很平静地接受了议会的委托。学生劝他,他回答:“我知道审判国王会有严重的后果,他们把它交给我,我不能推脱,这你也是知道的。他们把它交给我了。”(《弑君者》,页320-324)库克尽了最大努力,在纷乱的两个星期中,为国王的豁免权设下了一个阿喀琉斯之踵。复辟到来时,库克坦然接受自己的命运。他认为:“士兵临阵脱逃是一种耻辱,辩护律师如果出卖当事人则更令人不齿。”(《弑君者》,页295)他为自己辩护的主要理由之一就是,一名律师不应对其起诉之犯人的命运负责:他只是一个奉命行事的律师,履行控告责任,乃是因为收了律师费,至多可以说自己贪财,但绝无恶意行为;“对委托人的案件,律师只能尽力而为,剩下的全凭法庭裁决”。(《弑君者》,页323)
库克的辩护当时显然未能起到作用,但在其后数百年中却引起了响亮的回声。两名英国律师正式提出了“计程车规则”:一是18世纪末厄斯金认为,如果律师有权拒接一些不讨好的案件,“英国的自由将不复存在”;二是1820年亨利・布劳汉则清楚地表示:“一名辩护律师,由于肩负的神圣职责,在工作中必须时刻站在委托人一边,甚至除委托人外六亲不认……即使为了维护当事人的利益使国家陷入混乱也在所不惜。”(《弑君者》,页324)20世纪一名美国律师西蒙・里福坎德更直白地表达:“叫我,我就是一部出租车。”(博西格诺等《法律之门[八版]》,页461,华夏出版社,2007年)
“计程车规则”是否太冷酷?通俗点说就是,律师能为“坏人”辩护吗?细审以对抗制为特色的英美司法历程,答案很明确:不仅是能,而且是必须。冯象曾清晰扼要地阐述对抗制下律师的辩护伦理:“他出力为包括坏人在内的被告人辩护,罔顾受害人和公众的利益,乃是法治为顺利运作而必须负担的成本。假如律师不这样热忱为客户服务,任凭政府操纵司法,到头来我们所有人的权利都会受到损害。……律师为坏人效劳,实际是履行他的体制角色。他辩护越是成功,那体制就越发健全,越让人放心。”(冯象《政法笔记》,页171-172,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这真是一个奇妙的体制,詹姆斯・米尔斯描写一个辩护律师时说:“他自己绝大部分时间里都在为有罪者工作,为一种司法制度工作,这一制度的基础是一项有效而又矛盾的原则:为了保护无辜者,必须放掉有罪人。”(《法律之门》,页538)
那么,要不要担心被冤枉的好人无人辩护?查尔斯・柯蒂斯认为其实多余:“可以刺痛一个律师良知的案件,总会撩拨另一个律师的美德。每一案件都有两个方面,每有一个律师站在错的一方时,都有另一名律师站到对的一面。”正是只有在对抗制中,当事人才能平等角力,诚如为古巴关塔那摩监狱里恐怖分子嫌疑人辩护的美国律师查尔斯・斯威夫特所说:“在对抗制中,我们的初始假定是双方平等较量,平等获得律师支持。”(《法律之门》,页524、453)实际上,如果没有对抗制,律师制度就形同虚设,那些得不到法律援助的当事人也许会面临无尽的噩梦,甚至成为“被冤枉的好人”。青年学者吴丹红曾经感慨:“如果律师真的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我宁愿生活在有律师的地狱,也不愿生活在没有律师的天堂。”(《法律的侧面》,页132,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9年)诚哉斯言!从前,笔者看到一些影视剧里律师为某恶人辩护而使其逍遥法外时,每每义愤填膺;如今,已经理解如果律师经常拒接某个案件,那么其后果不是国家之福,而是民族之悲;同样也明白如果秘密警察能随意抓“坏人”而律师无法介入,那么其真相不是人民之幸,而是公民之痛。
当朋友质疑马丁・厄德曼:“如果你为一个奸杀5岁女孩的人辩护使其无罪,当他一年后再犯同一罪行时,你还会以同样的热情为他辩护吗?”厄德曼回答,自己还会不顾绝大多数人的想法而为之辩护。他继续解释:“我不关注已发生的犯罪或者被放掉的罪犯。如果我关注,就无法执业了。我关注的是,看到每一委托人都能得到最好的辩护,如果他有20万美元的话。……如果你是一名医生,希特勒找到你,说你是世界上唯一可以治好他的病的人,你会为他治病的。”(《法律之门》,页549-550)假如希特勒被抓,来找你辩护呢?厄德曼的答案想必一如库克当年。
实际上,美国人已经这么做了:正是在杜鲁门和他的法律顾问罗伯特・杰克逊的推动下,纳粹领导人在纽伦堡接受了审判,有22名德国律师克尽其职为他们辩护。在纽伦堡之后的半个世纪,萨达姆・侯赛因在法庭上说的话几乎与360年前的查理一世一字不差:“你们凭什么审判我?”这说明这个世界尚存远离正义的角落,那里的人们要像库克那时,慎重考虑该如何限制那脱缰的权力,完善司法制度,以合乎正义的法律程序应对暴君们的这一问。(《弑君者》,页371-373)如此一来,也就愈加彰显罗伯逊挖掘柯克、李尔本以及库克等人曾在法律史上所留下来的印迹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