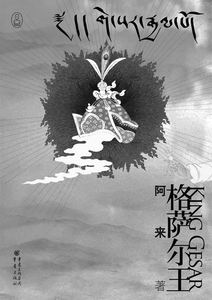
“重述神话”是一项全球性的跨国出版和写作计划,中国的作家苏童、叶兆言和李锐等都分别为此写出了《碧奴》、《后羿》、《人间》
我们知道《格萨尔》是公认的世界上最长的史诗,100多万行,2000多万字。同时它也是至今仍在民间口头传诵的活形态的史诗。《格萨尔》研究专家降边嘉措曾说:“《格萨尔王》是全人类的瑰宝。他的丰富性远远超过任何史诗,包括荷马的希腊史诗。”严格意义上说它还是一部形象化的古代藏族历史。如果说苏童、叶兆言和李锐等面对的是单一的个别的神话,他们可以根据神话原型和有限的资料发挥想象,自由地书写,没有任何约束。那么阿来的难度却在于他的面前是自己民族纷繁宏大绵远的传统和历史,面对的是结构宏伟,卷帙浩繁,并且由无数代人创作和口传的民间史诗,所以,他必须保持敬畏和谦卑之心。因为他的“重述”代表了一个民族甚至是整个人类的对传统和历史的回望,这种寄托无疑是沉重的,而且长诗《格萨尔》的丰富性远远超越了一个作家的想象,它的磅礴气势完全可以将一个作家的写作想望淹没和压垮。所幸,阿来成功了,他在强大而真实的民族意志和史诗、神话的虚构之间获得了写作的空间,并且为我们建造了一座新的神话和史诗性的文学圣碑。
从《尘埃落定》到《空山》,再到今天的《格萨尔王》,阿来一步一步找回了更真实的自己。如果有人说《尘埃落定》还有些许拉美文学《百年孤独》影响的印记,那么《格萨尔王》则是阿来回归传统,面对自己民族的伟大史诗的一次充满激情与理性的致敬。
史诗《格萨尔》讲述的是天神格萨尔下凡人间、降妖伏魔、抑强扶弱、造福百姓的事迹。小说《格萨尔王》基本遵循了这个故事框架,即“神子降生”(格萨尔从天上被派遣到人间)、“赛马称王”(格萨尔称王征战的过程)和“雄狮归天”(格萨尔返回天界)。但是我注意到,小说在充分表现格萨尔“神性”的同时,把更多的笔墨放在了这个天神的“人性”的部分。他在尘世脱胎,然后长大成人,甚至让他失掉天界生活的记忆。最后他几乎是被天界和他的人民共同推上了国王的位置。而当了国王之后,他同样感到了困惑,面对宫廷的金杯玉盏,面对嫔妃的衣香鬓影,他时常感觉无所事事,并经常反问自己:“这就是做一个国王吗?”当他讨平了四大魔王,使人民过上安康的生活的时候,他面对跪地埋首不敢正视自己国王的臣民同样感到不解:“他们应该爱我,而不是怕我。”他希望他们的人民不应该只知道他的英明、勇敢,也应该知道他的身世和爱情,当然也包括他曾经的迷失。
小说有两条线索。一是古代的神话,即格萨尔的生平;二是现代,《格萨尔》说唱艺人晋美(“仲肯”)的流浪游吟的经历。两者奇妙地形成了互为生成推演的关系。阿来曾说:晋美就是我。他说:“在藏族人传统的观念中,写作是一件具有‘神性’的事情。是探寻人生或历史的真谛,甚至是泄露上天的秘密。不过,这个秘密有时是上天有意泄露出来的,通过一些上天选中的人透露出来。所以,一个人有了写作的冲动时,也会认为是上天选中了自己,所以要对上天的神灵顶礼赞颂。”(引自阿来新浪博客)阿来道出了写作者与写作对应物的神示的关系,也隐喻了他自己创作这部作品的艰辛而又惊喜的心路历程。在小说里格萨尔实际上是两个人,一个是传说中的神圣化的格萨尔,一个是阿来或者说是晋美心目中的人格化的格萨尔。两者有时是矛盾冲突的,有时又是重叠互补的。前者可以不食人间烟火,后者则经常暴露人性的软弱。小说多次让晋美与格萨尔在梦中相会。他们平等对话,惺惺相惜。当格萨尔返回天界后又一次来到晋美的梦中:“我出去巡行时看到好多人受苦,既然我是一个好国王,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食不果腹,流落异乡?”这让我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玛卓夫兄弟》中的一个梦:面对穷困的俄罗斯大地,面对饥饿的村妇怀抱着哭泣的婴儿。无辜的米卡天真地发出一连串的质问:为什么那些穷苦的母亲会站在这儿?为什么娃娃要哭?为什么他们不互相拥抱亲吻?为什么他们不快快乐乐地歌唱?面对人类共同的苦难两个人发出了相同的疑问。所不同的是,米卡醒来后,他顿悟式地承认自己有罪(基督教的“原罪”),而格萨尔则感觉到了天界与神的局限,本来是想为人间带来福祉,可他们提供给人们的却常常是锋利无敌的兵器和无休无止的战争。他的英名虽然获得了人民的传诵,而百姓却依然处于没有尽头的苦难之中。所以,格萨尔最终放弃王位回归天庭与其说是无可奈何,不如说是一种自我的放逐。
格萨尔从神降生为人,又由人回归成神,完成了神话所必须的形而上的抽象化过程。他是原初的英雄时代的一个民族的理想和信仰。而我们所谈论的小说中的格萨尔,却补充了人们想象中的英雄的真实部分。毫无疑问,格萨尔是英雄,如同古希腊神话中的赫剌克勒斯,但他也是反英雄的,即那个富有争议的阿喀琉斯。黑格尔在《美学》一书中这样说:“关于阿喀琉斯,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人!高贵的人格的多方面性在这个人身上显出了它的全部丰富性。’”我以为这个评价和结论对小说中的格萨尔同样合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