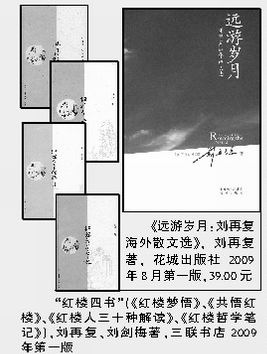父亲在海外已漂泊整整十九年,从第一人生走向第二人生。这种生命转化好不好?这个问题对我而言,回答非常简单明了:好极了。对于第一人生中的世俗角色及其负累,有一个“了”,这就“好”。而第二人生则是全新的开始,尽管“转世难”,尽管经历过连根拔的苦痛与窒息感,但终于使自己赢得一次新的生命的黎明,迎接了
父亲出生于福建南部的山乡里,本质上是个农家子。这种穷乡僻壤,使他天生带有两种性格,一是质朴,二是勤劳。到西方的“花花世界”后,他依然如此,始终保持质朴的内心,既不为苦难所动,也不为成就所移。他的写作,正如王强(父亲的年轻好友)所说,是类似《一千零一夜》那个阿拉伯少女为了拯救生命的讲述,不讲就没有明天。如果说,在国内时写作多少还有功利之需,那么,在海外,父亲的表述则完全是活下去――有意义地活下去的需求。作品不是点缀品,更不是面具,而是灵魂诉说的需要,是生命自明、自证、自救的需要。身在漂泊,心在诉说,漂泊史即心灵史。父亲在海外近二十年所写的文章,是漂泊文章,也是心灵传记。十多年前,父亲出版《漂流手记》的第一卷时,李欧梵教授为之作序,第一句话就说:“刘再复先生的《漂流手记》,是一部心灵的自传。”
李欧梵教授用“心灵自传”概说我父亲的漂泊散文,非常贴切,而把《漂流手记》视为内省文体即内心西游记也非常准确。《漂流手记》的第一卷如此,之后的八卷也是如此。不过,如果把九卷作为一个整体阅读,就可以读出其漂泊心灵在穿越时间的隧道旅程中是有明显变化的,从害怕孤独到占有孤独,从窒息感到至乐感,从家国忧思到宇宙领悟,从非常之心到平常之心,从形下故园到形上故乡,等等,可以看到漂泊心灵并非消极地浪迹,而是在积极地寻求、叩问和提升。这一心灵历程,固然有向后看的忏悔与反思,但更重要的是向前方寻觅的真诚与热情。这一历程,余英时教授准确地表述为“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我觉得,父亲心灵漂泊史的诗意就在朝向自由王国的转变与提升中。
在国内的时候,父亲身兼人文学者与散文作家,既从事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后者的重心是文学理论与现代文学史),又创作散文诗,散文。出国后他仍然是追求学问、思想、文采,一面从事教学和支撑教学的研究,努力打通中国古今文化血脉与中西文化血脉,重心逐步从今向古转移,在“返回古典”的大思路下完成了“红楼四书”(《红楼梦悟》、《共悟红楼》、《红楼人三十种解读》、《红楼哲学笔记》)。在这之前,他还完成了《放逐诸神》(论文集)、《高行健论》、《现代文学诸子论》、《罪与文学》(与林岗合著)、《告别革命》(与李泽厚合著)等学术与思想论著以及《思想者十八题》对谈访谈录。另一方面,父亲则孜孜不倦地进行散文写作。出版了《漂流手记》、《远游岁月》、《西寻故乡》等漂流散文系列。我把漂流九卷视为父亲漂泊心灵的诉说。按其形式的差别,大约可分为五类。第一类是抒情、叙事小品;第二类是游记;这两类集中地自叙漂泊情思,人如其人其行其心,与“漂泊传”之名最为相符。第三类是悟语,其实也是心声,不过因篇幅限制,选的很少。无论是天涯悟语还是红楼悟语,或者面壁沉思时的自语,都是发自血脉深处的个人的声音。父亲仿佛有意创造一种新的语文体,袖珍散文与袖珍论文的结合体,每一节虽只有三五百字,却都有一个明心见性的精神之核,核中有视角,有眼界,有发现,是直觉与感悟的果实。漂泊十九年,父亲写了二千多则悟语,如果能把这两千则悟语细读一遍,就会进入作者漂泊心灵更深邃的内涵。这三类之外,还有许多容易被人们忽略的杂文,这些嬉笑怒骂,不同于“内省”,但也是漂泊心灵的一角,它说明,这一心灵并非自我封闭,它仍然在关注社会人生,谴责黑暗。父亲常说自己是“外儒内禅”,这些杂文应是一种“外儒”的明证。最后一类便是“书信”,父亲和我合著的《共悟人间――父女两地书》中,有父亲的心灵自白,也有我对父亲的认识。父亲私下对我说,此书既是漂泊心传,也是“漂泊心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