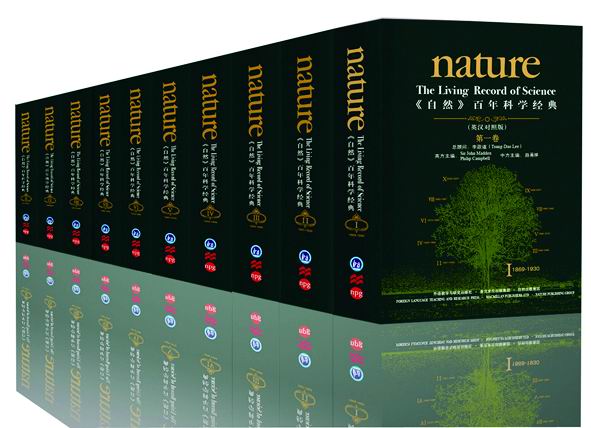
很荣幸我能参与这套论文集的遴选和编辑工作,在此过程中,令我感到困难重重的不仅仅是要重读这些经典的科学论文,还要找出在论文中体现出来的科学规律,科学家以及人类社会之间的相互影响。《自然》杂志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视角去了解科学领域中的焦点问题和前沿问题在20世纪前后是如何演变的,这常常能够反映出当时广阔的社会和政治领域的发展趋势。简单地说,遴选出来的论文为我们展示出了人类社会对于科学的冀求和科学对于人类社会的贡献。
如果科学研究也如同时装一样有自己的时尚和潮流的话,那么在《自然》杂志中也一定会体现出来。上世纪80年代中期高温超导材料(超导指材料处于导电但没有电阻的状态)被发现的时候,很快,几乎没有一期《自然》上没有讨论相关问题的论文。同样的状况也发生在1990年化学家们发现了如何批量制备名为富勒烯的笼状碳分子之后的几年当中。在那之后两年,在编辑的过程中我首次看到了来自长春吉林大学化学系关于富勒烯粉末的工作,不禁对于《自然》的全球影响力发出由衷的感慨。
这样的对科学发展走向的追踪或者设定看上去会有些无法捉摸,但是在任何时刻它对于判断科学上的重要发现都是非常有用的。可能第一个出现在《自然》杂志上的明显的发展走势出现在核物理诞生的时候,核物理学不仅从整体上重建了我们对于物质的微观本质的观点,并立即导致了有深远影响的技术的产生。《自然》从一开始的时候就紧跟这一走向,从1896年伦琴发现X射线,到贝克勒尔提出放射性的概念,从居里夫妇在新元素中观察到放射性,到1899年卢瑟福对元素嬗变的阐述,都在《自然》上及时的报道出来。而1913年卢瑟福的合作者索迪首次提出同位素的概念同样也是在《自然》杂志上。
由于已经成长为一个高度技术性的学科,战后核物理学就在《自然》杂志中消失了。而天文学取代了它的位置成为《自然》杂志中物理科学的主要代表,这是一个具有永久的跨学科感染力的学科,当时正得益于观测方法的快速进步。使用光谱的两个极端:无线电波和X射线(之后也用到了伽玛射线),天文学家们在上世纪60年代观察到了黑洞,星系碰撞和星体的诞生。
与此同时,生物学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利用材料对X射线的散射来确定材料的原子和分子结构的技术,我们称之为X射线晶体学,最早是由亨利・布拉格和他的儿子劳伦斯・布拉格于1910年代在英格兰发展出来的,《自然》发表过几篇布拉格父子关于这项技术的进展及应用的文章。但是将这种方法应用于蛋白酶结构的研究在当时仍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因为在这些结构中含有成百上千个原子,而要从X射线的衍射斑点中解析出他们的位置是极为困难的。最终,在上世纪50年代卡文迪什实验室的领导者――劳伦斯・布拉格的强有力的支持和鼓励下,根据威尔金斯和富兰克林在伦敦进行的X射线晶体学研究,克里克和沃森确定了DNA的双螺旋结构,该结果发表在1953年的《自然》上。
这套选集中一些文章的入选完全是基于它们自身巨大的影响力。其中,克里克和沃森的文章也许是《自然》发表过的文章中最著名的一篇。还有相当多的一些论文,它们也或多或少地开创或者引领了整个研究领域的方向,比如,1963年瓦因和马修斯发现的海底扩张现象,首次为板块漂移学说提供了明确的证据,还有1995年太阳系之外第一颗行星的发现。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是否将那些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文章囊括进本套选集,通常认为这些文章已经失去了它的科学价值而仅仅只有历史意义。但是实际上并不一定如此。它们也许可以用来解释在其他科学领域发生的事情,并且有利于我们去理解当时这个想法是如何被接受的。比如优生论或者通过选择性繁殖对人类基因进行改造的诸多努力等等,这都出现在达尔文的《人类起源》发表至少50年之后。这些论调在当今世界属于被摒弃之列,但是简单地忽略掉它们不仅是对历史的不诚实,而且会曲解当时的生物学家对达尔文理论的解释。
而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的“聚合水”事件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当时前苏联科学家声称发现了一种新的超粘滞状态的水。这个“发现”被证实是荒谬的,也极有可能是由于污染造成的。但是它和发表在1988年《自然》上的假定性的“水的记忆”(也在选集中)不仅仅展现出科学研究是怎样进行的(和它是怎么做错的)而且点明了在水的分子结构的研究中的亮点,例如水的适应性,也即它能够根据表面的形状和溶解的分子去调整自己的性质。
《自然》仍在继续发表最前沿的科学研究。我从我的桌上拿起最新的一期《自然》,除了别的之外,它报道了保存的最好的志留纪的鱼化石(发现于中国云南省);散落在努比亚沙漠里的第一个由曾被观察到的小行星变成的陨石的碎片;在火山喷发的烟柱中发现的微型气旋;分子尺度的机器的结构,它可以在基因携带的信息被翻译为蛋白酶之前对它进行“编辑”。很显然,科学和《自然》杂志都还在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