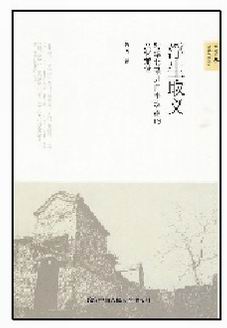 对于大多数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而言,自杀是与恐惧和绝望相关的无奈选择,也是解决问题
对于大多数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而言,自杀是与恐惧和绝望相关的无奈选择,也是解决问题
中国农村的自杀现象基本不是一个医学问题。据研究,中国自杀者中精神病患的人数为63%,远远低于西方国家超过90%的比例。在医学框架之外,要理解“中国式自杀”,唯有回到日常生活,从文化上寻找其真实原因。与西方对待自杀的态度不同,中国人更多将自杀视为一种表达手段,以生命的代价寻求最后的正义。以农村中女性自杀为例,遭到丈夫或公婆的恶劣对待,或言语侮辱,常常能令她们“一气之下”自杀,吴飞称为“赌气”。问题是,为何自杀似乎成为了唯一的表达途径,在中国华北农村中大量出现?农村中是否缺乏表达正义的其他途径?自杀者所追求的无非是尊严与人格,这何以促使人们采取不恰当的方式表达一种美好的价值?
这就要回到家庭政治中来。吴飞将农村自杀的原因大致划分为家庭政治中的“委屈”和公共领域中的“冤枉”。我们发现,农村中的自杀,大部分是“委屈”造成的。即是在以亲密关系为前提和追求的家庭政治中,亲情伦理遭到破坏时人们所产生的一种反应。尽管许多人对“过日子”的艰难很有领悟,但仍会在个人尊严受辱之时选择自杀,很难说这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他们只是在当下将死亡当做摆脱不幸和痛苦的一种方式,为的是获得完整的人格。在访谈中,许多人谈及亲友的自杀,往往表示不能理解,而在面临相同处境时,又同样选择了自杀。因此,可以说自杀仍与农村的家庭结构相关。即使在打破了家庭等级制度的前提下,人们仍未找到在亲密关系中表达正义的恰当途径。在人格与面子的文化约束力之下,农村中的面子有时比生命更有价值,“委屈”比“冤枉”更令人绝望。而自杀就是对委屈的报复或矫正手段。
对生命和正义的理解在农村的日常生活中意味着什么?从自杀的故事中,我们看到充满权力斗争的“过日子”,丝丝如缕的生命的展开,任何一个环节的不顺利,都会引发自杀事件。在人们的谈论中,自杀本身并没有好坏,关键在于自杀的原因。死亡为自杀者赢回的道德资本,乃是死者最后的赌注。很少有人真正批评自杀者的道德,更多的是怀疑他\她受到了何种委屈。在无法求证的情况下,生者往往背负了恶名。“家庭中的正义,就是令每个成员得到应有的尊重和看待,不义,就是对这种伦常的违背”。在这个基础上,农村中的自杀可以说是向往美好生活的极端方式,当个人的消极等待无法逆转生命质量时,自杀的勇气便浮上心头。而自杀者往往获得了最大的尊重。然而这能否算得上一种成功?
另一方面,并不是所有人都具有自杀的权利,或者说,自杀仅仅是正常人的一种特权。在吴飞的访谈中,人们说起“傻子”、“疯子”及边缘人群的自杀时,往往不愿细说,认为没有谈论和研究的必要。因为他们不具备完整的人格,也就不具备完整的获得道德资本的权利。在农村中,只有智力正常,处于完整的家庭生活中的人,才拥有被人正视的资格,即使付出生命的代价,“不正常的人”也难以引起他人的真正关注。可见,自杀在农村中被视为“过日子”的一部分,乃是正常人为了争取道德优势的方式。
中国农村中的自杀,难以从医学和司法的角度给出解释。因为农村自杀事件大多发生于家庭之中,如果不涉及谋杀和纠纷,自杀就不会成为公共领域(医疗及司法系统)中需要处理的问题。农村中的自杀大多是不可预测的,尽管人们在事后会寻找各种解释,但并没有一种有效的干预方式能够真正介入农村生活。书的最后,吴飞介绍了费力鹏教授与北京回龙观医院合作的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谢丽华、许容组织的“农家女”生命危机干预项目,他们尽管从心理学、精神病学的角度获得初步成效,并在农村女性中已培养起一定数目的骨干,但中国农村的自杀干预,远比医生和社会工作者所能预料的更为复杂,其背后包含的文化结构、家庭政治、日常正义,仍需要更深入的研究。华北农村的自杀故事告诉我们,在追寻美好生活的路途上,人们仍然愿意选择最极端的方式,以生命的代价换取人格和尊严。在广大的农村,生命的苦痛往往来源于生活背后的文化逻辑,如此“中国式自杀”,也许是对美好的最后向往,然而,却并不能带来真正意义上的美好。如何表达正义,如何安置日常生活的秩序,如何改变引导自杀的文化格局,仍是自杀研究背后需要解决的重要命题。然而,对于身处城市中的人们,自杀或自杀的意念又意味着什么?当人们怀揣梦想奔波于城市中,美好生活也许并不仅仅意味着各得其所,而是在自我理想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苦苦挣扎,因而承受着更加复杂的痛苦。这样的痛苦带来的更深层的精神危机,无论是否导向自杀,都是都市人群必须面对和纾解的。减少农村与城市的自杀需要不同的制度建设与干预机制。无论我们身处何方,自杀不仅仅是新闻,不仅仅是社会事件,而是与每个人紧密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