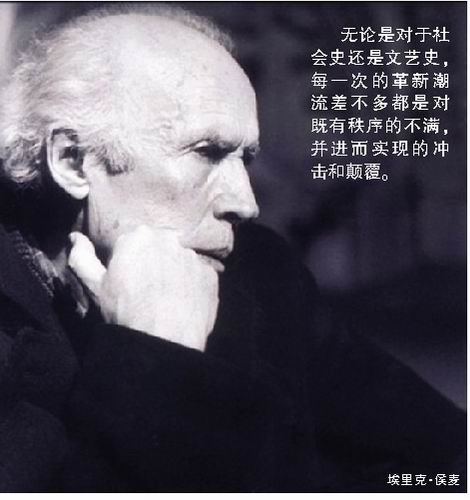

“新浪潮”主将特吕弗、戈达尔等人与媒体记者会面
毫无疑
1920年,埃里克・侯麦出生于法国东部城市南锡的一个天主教中产家庭。他的原名叫让-玛丽亚・莫里斯・谢热,最初的职业是在学校里教授文学课,业余时间以“吉尔贝特・科迪埃”的笔名发表小说。上个世纪50年代初,文学教师谢热出于对电影的喜爱,改行当了职业影评人,加入由著名学者安德烈・巴赞、雅克・多尼奥尔-瓦克罗斯和洛・杜卡共同创办的《电影手册》杂志编辑部。而正是这本杂志,后来和文化工作者亨利・朗格卢瓦担任馆长的法国电影资料馆一道,成为“新浪潮”运动的源头。
无论是对于社会史还是文艺史,每一次的革新潮流差不多都是对既有秩序的不满,并进而实现的冲击和颠覆。具体到“新浪潮”,它所针对的“既有秩序”,就是战后法国电影界所流行的“品质传统”:从20世纪40年代末起,为了与大量涌入的美国好莱坞商业片相抗衡,法国电影界兴起了高投入、明星制的制片模式,拍摄各类流行化题材的“大片”,以精妙的剧情、华丽的画面、影星的倾力演出来吸引观众,以保证票房收益,这些影片就被统称为“品质电影”。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品质电影”已在法国大行其道,同时也成为了《电影手册》年轻编辑和影评人的最大敌人,如弗朗索瓦・特吕弗、让-吕克・戈达尔、雅克・里维特等。他们忠实地宣扬“新浪潮”精神导师安德烈・巴赞所主张的“写实主义”,“电影的创作者们应该‘记录事件’,尊重感性的空间和时间”,强烈反对传统电影观念中过度的戏剧性。他们批评纯娱乐化的、内涵空虚的、缺乏创新的“剧本电影”和“明星电影”,提出了“作者电影”的概念:就如同一本小说或一幅油画一样,一部电影也应该展现出作者(导演)鲜明的个人化风格,不该去讨好评论界和观众,而应该以表达作者自我的理念为最终目的。他们下笔犀利,对古今中外一律批判。像特吕弗发表专题评论,宣称《法国电影已在虚假中消亡》,而一向最激进的戈达尔在钻进电影资料馆、花了三年时间看了3000多部电影之后,更是干脆扬言很多电影都不能称作电影,很多公认的著名导演也都不懂电影。他们还给那些他们认为因循守旧的“品质片”扣上了“老爸电影”的戏谑称呼。某种程度上,《电影手册》逐渐改写了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电影界的观念。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电影青年”会有如此大的能量,是因为他们的想法和行动在那时并不是孤立的:20世纪50年代,正是西方世界各种思想与社会变革风起云涌的时期,特吕弗和戈达尔等人可算是在电影领域恰逢其会。
1958年起,《电影手册》的笔杆子们在“革命”之后终于要有所“建设”,他们开始拍摄自己的电影作品,给所有“不懂电影”的人看看。很快地,一批风格独特、与“品质传统”截然不同的影片诞生了,令评论界和观众感觉耳目一新。《快报》的女记者弗兰索瓦・吉鲁在专栏中首次使用了一个名词来形容这个现象――“新浪潮”。“新浪潮”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运动,只是对当时各种“新电影”的一个笼统概括。甚至特吕弗等人也不能完全代表“新浪潮”,他们被称为“《电影手册》派”,以便同阿伦・雷乃所代表的“左岸派”这个知识分子电影群体相区分。
自然而然地,身为《电影手册》一员的谢热也投身到了“新浪潮”当中,这个时候他已起用了新艺名“埃里克・侯麦”――取奥地利籍导演埃里克・冯・斯特劳亨和英国侦探小说家萨克斯・罗默尔(侯麦)二人名字各一部分而合成。这恰好代表了他一生中的两大追求:电影和文学。而之所以要用艺名,是因为侯麦不想让他那保守的家庭知道自己在“娱乐界”工作。从1959年的《狮子星座》开始,侯麦踏入了他的电影导演生涯。
自1958年巴赞去世之后,侯麦便接替了《电影手册》主编的职位,他仍然坚持巴赞等前辈“作者电影”和“写实主义”的办刊方向。这在“新浪潮”打江山的时代是“《电影手册》派”批判旧势力的武器,然而进入1960年代后,倒反过来成了编辑部里那些“左翼”对侯麦进行批判的武器。他们指责他“落伍”,不肯接受新兴的现代主义和结构主义,侯麦则寸土不让,双方闹僵了。此时杂志创始人之一、握有财政大权的多尼奥尔-瓦克罗斯公开站在了“左翼”成员一边,他们联合起来,把“落后分子”侯麦赶出了《电影手册》,雅克・里维特接任了主编。
其实,侯麦与《电影手册》的关系破裂,似乎从一开始就是注定的。在这个以年轻人为主的编辑群体当中,他的岁数是偏大的。创业年代的同甘共苦掩饰不住侯麦在编辑部内格格不入的事实。侯麦性格比较内向稳重,比之好高谈阔论的那群“小兄弟”,实在是显得过于安静。不过,人事上的不和,毕竟只是一个引子,这场“倒侯”运动的推动原因还是意识形态的差异。到后来,就连尝试主流化的特吕弗都成了昔日“新浪潮”战友们的批判对象。
离开《电影手册》后,侯麦全力地投入到了他的“作者电影”创作之中。他喜欢拍系列片,按其自述:“我不寻找吸引人的题材,而更愿意把同一题材拍至少六遍,这样观众自会理解。……坚持自我,就会有追随者,还有发行商。”侯麦在这里其实是赋予了电影以文学的深刻性。他先后创作了“道德故事”、“喜剧与谚语”和“四季故事”等系列,主题相当集中,都是探讨法国中产阶级的情感世界和内在困境。
侯麦对爱情主题很感兴趣,他偏好这样的故事模式:一个男子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女人之间周旋,如何通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做出最终的选择。例如“道德故事”系列的第一部《蒙索的女面包师》,仅20多分钟的短片,感觉就如同莫泊桑或是欧・亨利的小说。影片的故事发生在巴黎街头,大学生皮埃尔对偶遇的一位女子希尔维一见钟情。二人本来定好了再次约见,可是希尔维却因为摔伤了而失约,皮埃尔无聊等待之时,碰上了对他“有点儿意思”的面包店女工杰克琳,为了填补希尔维的空白,皮埃尔答应与杰克琳约会,但就在他们二人正要如约见面时,希尔维又出现了。最后,皮埃尔取消了与杰克琳的约会,还是与希尔维双双而去,不过心里却留了一丝遗憾。从这部片子开始,侯麦爱情电影里大多数的男主角,都是“皮埃尔”的翻版。影片《女收藏家》里的主人公古董商阿德里安,便将这种“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主义”发扬得更加典型。在自己的电影作品里,侯麦不厌其烦地解析着男性的多情,以及围绕多情而展开的心理纠结、具体行动与生活场景。在这个过程中侯麦从不妄加价值判断,仅仅是表现和讨论。但结局还是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选择的,而且这种选择也往往是合乎社会道德规范的――男主角回到了妻子、未婚妻或者初恋情人的身边。这多少与侯麦正统的宗教信仰有关。
需要指出的是,“道德故事”这个名称,在中文语境中会带来一定的误解。侯麦电影所涉及的“道德”主题,不同于一般层面的意义。他自己的说法是:“法语中有个专门的词‘moraliste’,指那些更关注自己的思想和感情等内在世界的人,例如帕斯卡、司汤达。‘道德故事’中的‘道德’并不是说普通的道德信念和行为,而是思考多于行动的人物。”因此,侯麦电影呈现出的显著特点,就是片中充满了大量对白和代表主角心声的旁白,男女人物总是在不停地进行着自我反省以及与身边人的争论。他们的台词又很少像其他“新浪潮”写实主义电影那样讲究即兴发挥,而是由作者(导演)精心设计和选择,就像小说一样。实际上,侯麦的剧本经常写成小说格式,不用改动多少就可以拿去出版。他既是一位“电影文学家”,也是一位“文学电影家”,两者都是名副其实的。
欣赏侯麦的电影作品,光看一部是不够的,得把一个系列、甚至是所有系列都看完,才能品味出其中的魅力。侯麦的“作者风格”表现为舒缓、执着、细致。很明显地,这与特吕弗、戈达尔等“新浪潮”干将的颠覆性大相径庭。侯麦的批评者们声称他只是在不断地组合和重复,没有多少创造,但侯麦电影的特有质感却也是旁人很难模仿的。他是一位不怎么“新浪潮”的“新浪潮”导演,这场运动其实没有过多地影响他,而只是提供了一个时势,令其得以实践个人关于电影的理念。
重温《电影手册》那场内部争斗,驱逐侯麦,不是“《电影手册》派”分裂的结束,反而是一系列开始。1960年代中后期起,成员之间观念和个性的冲突愈发加剧,一时之间是“人各有志”,“各走各道”。这个本来就松散的“艺术同盟”在实体上已趋于瓦解。两大旗帜人物特吕弗和戈达尔更是公开交恶。导火索是戈达尔过度批评特吕弗的新片,连带着把特吕弗的电影理念都炮轰一番,使得二人本来就渐行渐远的友谊正式终结,从此形同陌路。1980年代初,戈达尔还曾给那些闹翻了的“新浪潮”战友,特吕弗、雅克・里维特和克劳德・夏布洛尔等人主动写信,要求和好,但对这位“老伙计”最了解不过的特吕弗毫不客气地拒绝了,还在回信中建议戈达尔写一本“自传”,书名叫《我就是一坨屎》。
轰轰烈烈的“新浪潮”就这样在繁华与喧嚣之后,渐渐地平息了,但始终不能说是结束。它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甚至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电影艺术的样子。当年那些把“老式”电影界搅得天翻地覆的年轻人,等他们自己也成了“老式”之后,却仍旧坚守着年轻时的理想和信念,包括侯麦。虽然对“新浪潮”的历史百味杂陈,但这位“老大哥”在回首之时依然保持其特有的宽厚:“我们毕竟开创了‘现代电影’的新时代!”不过,更能概括“新浪潮”、以及侯麦与“新浪潮”关系的,应该是他另外一句话,“我们应该敢于反抗潮流”。这是侯麦总结他昔日在《电影手册》那些恩恩怨怨的感慨,也是侯麦一生所遵行的原则。他既敢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一起反抗传统的潮流,也敢于反抗朋友们强迫自己改变信念的潮流,还有后来那一波一波不停地标新立异的“潮流”,也正是在对潮流的不懈反抗之中,侯麦的电影才成其为“侯麦电影”。或许,这种反抗,就是侯麦、还有“新浪潮”留给后人的最大精神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