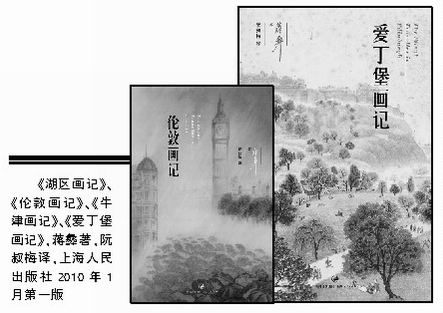
我们称许杰出的人物时,往往会说些套话:学贯中西啦,文武双全啦,多才多艺啦……这类表述已成为谀词,不是严格按本义来使用了,因为身边真正能符合以上内涵者太少,只好降格以求,随口把大帽子批发出去。
但当我们回眸民国时代,却发现那时候当得起这类评价的全才式人物,真是多不胜数。不说众多已为人熟知者,就算在一些冷僻的专业领域,或者寂寂无名地埋没在历史尘埃中的,随便拈来抖落抖落,都有耀目的光彩。――民国是乱世,却有如魏晋南北朝,都是堪追欧洲文艺复兴的群星灿烂的风流时代。
比如这又一位被“挖掘出土”的蒋彝(1903-1977):出身于书香世家,从小随父亲习书画;青年时曾在大学里读和教化学,也曾投笔从戎参加北伐革命军,后来当过三个县的县长;中年只身西行,旅居英美四十余载,以英文写作,讲述西方的故事,却又将中国传统文学、历史、习俗等有机地融入作品,从而饮誉异邦,结交西洋名士,任教于多所世界一流学府,并被选为英国皇家艺术学会会员、美国艺术科学院院士。――这样的人生,庶几才称得上学贯中西、文武双全、多才多艺吧。
蒋彝给自己取号“哑行者”,不幸在本邦一语成谶。“可口可乐”大行其道,却没有多少人知道他是这一妙名的中译者。当然这对蒋彝来说只算小试牛刀,他的最大成就,也是在海外最为畅销的,乃其一系列融诗、书、画、文为一体的独特游记。现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其中四本:《湖区画记》、《伦敦画记》、《牛津画记》、《爱丁堡画记》,让我们得以重新认识蒋彝。同时,蒋彝是“以文化旅者的身份,在中西文明中自由穿行和出入”,“以传统的中国画技法描摹异域风物,以一双温柔的中国之眼敏察东西文化的异中之同”,然则这批隽永的“画记”,对英伦三岛几个核心区域所作的优美展示,乃可视为对英伦文明几组密码的解读,且这种解读是中国化的,更易令我们亲切认同。它们终于“回归”的意义,有论者指为:“他的旅行文字和深具洞悉力的评论扩大了我们的视野,使我们对自己、对外在世界产生全新认识。”――这似乎不能说是夸大其词。
《爱丁堡画记》中有一篇《不实之争》,可算是蒋彝游记的代表作之一,较好地反映了其写作风格:随兴所至的漫步,所遇的风景、人物、动物、植物的细致描写,意识流般联翩的回忆与思索。这些思索并非一般的触景生情,而能达到历史的高度,世界的眼光,以及自我观照的深度;虽然一些引申的哲理说不上有多深刻,但难得的是那份情怀胸襟。最后,那些中国古典文史知识的穿插,那些书画的点缀,固然有向西人讨巧之处,却也十分自然,并非简单的贩卖中国元素可比。这样的文章,难怪会深受西方读者喜爱,风行一时。而我们中国读者,还进而能借他的文字与画笔,领略西洋的风景、风物与风情,亦是一份很好的享受。
像《不实之争》写到的能蒸发氤氲、神奇地把云雾染紫的“苏格兰石楠花”,就很引发我的兴趣。蒋彝另还多次写到这种植物,如同在《爱丁堡画记》中的《旧日情怀》,记他在一个五月初逛皇家植物园所见,首先就是“一大丛一大丛的各种石楠花正含苞待放。一年前我就见过这片华美的紫色地毯……”他说:“苏格兰人一向以石楠花为傲”;“石楠花蜜制成的蜂蜜最好。”他描述这种植物的特征:“沿茎长着一圈圈叶子,一直到顶上,托着一簇铃铛似的小花。”另外在《戒慎恐惧》中则写到:“王子街上有两处地方深具苏格兰风味”,其中之一就是一个老人的叫卖:“幸运的白色石楠花!幸运的帚石楠!”蒋彝还为之画了插图。
于是我去翻英国皇家植物园首席科研官员克里斯托弗・格雷―威尔森原著的《欧洲花卉――不列颠及西北欧500多种野花的彩色图鉴》,里面收录有包括帚石南在内的八种石南,得以从权威的图文中欣赏这种远看如华美地毯、近观乃可爱铃铛的美丽植物。正如蒋彝描写的,它们是矮小的蔓生灌木,有着密集簇生的花串;以紫红色为主,也有罕见的白色花;花期为5―10月。
但这是“石南”,而本书则译作“石楠”。查《中国花经》,确有石楠,也属艳丽的花树,却并非不列颠的野花,而是产于我国秦岭以南;不是一大丛一大丛的贴地小灌木,而是乔木;不是五月初含苞待放然后一直开到十月,而是花期4―5月。更重要的两点:石楠不是铃铛般的总状花序或圆锥花序,而是伞房花序(《中国花经》收有石楠花的绘图,与蒋彝所写所画一对比便知差异,而蒋彝所写所画是与《欧洲花卉》的石南彩色照片对得上的);石楠的花也不是紫红多白色少,而恰恰相反,是白色的(那个苏格兰老人之所以要特别叫卖白色的石南花,正是因这种颜色稀少,才被人视为幸运之花;若像石楠那样全属白花,就不会显得珍贵了)。这一切,都可印证蒋彝说的那种苏格兰名花并非“石楠”,乃是“石南”。这本《爱丁堡画记》的译文基本上流畅洵雅,但这个植物名字显然是搞错了。
蒋彝那篇植物园游记《旧日情怀》还写到盛开的大片杜鹃,像石南花一样,竟也会产生“一层薄薄的彩色雾气”,并说“中国人称此雾气为‘花雾’”。这些杜鹃花让他回忆起去国前一次愉快的家乡之游:与一位年轻女士一起攀庐山,“随意慢慢地走”,默默地看沿途优美景色。有一处山坡开满了各色绚丽的野杜鹃,他们便坐在松树下的岩石上,静静地欣赏。“忽然下了阵雨……我们坐在那儿,看着花儿沐浴在雨中,并吐出彩色薄雾……雨停后,我们仍然坐在那儿,完全忘了时间。我的朋友作了首短诗,我也一样。我们各自将诗念给对方听……”
这幅图景如此美好,以致蒋彝都没有画出来,让我们只凭文字去感受会更好一些。它令我想起汪曾祺晚年忆述他年轻时在西南联大,曾与朱德熙闲步昆明郊野,遇上下雨,在小酒馆里对坐看花,呆了半天的情景;想起阿赫玛托娃晚年忆述她年轻时在巴黎,曾与莫迪利阿尼坐在雨中的卢森堡公园长凳上,撑着伞,互相背诵诗篇的情景。――有幸能拥有这种珍贵的画面,虽然只是短暂的片断,却足以支撑我们的记忆,温暖一生。多年之后,蒋彝重温“旧日情怀”,说到:“当我望着爱丁堡的杜鹃时,那快乐的一天又回到了我心中。”
因为这段前缘,当然更因为“许多美丽的杜鹃品种来自我的祖国”,蒋彝说:“想到这花,我就想到中国;犹如想到石楠(石南)花,我就想到苏格兰。”――也许我们正可以用这两种花来比喻这位“哑行者”:他营造了一片园地,从中国移栽到西方的杜鹃,有着中国的根,也保存了中华文化的花容叶貌,但又被欧风美雨所滋养;同时,这里还开出大片繁盛华美的石南花。它们交相辉映,共同蒸发出的花雾,融汇成幻美的云霞,反哺着中西两片土地。
顺便说说,蒋彝提到石南花应该也原产中国,似乎不确。倒是另一事实,可以让我的同园二花之喻更显贴切:石南,正是属于杜鹃花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