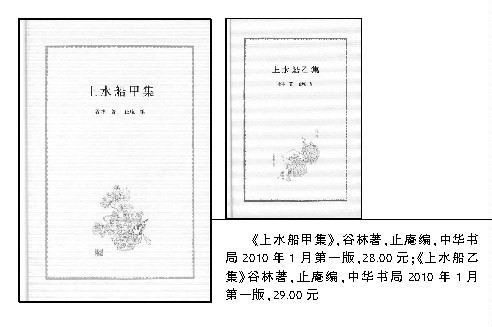
一年后的一月十日,谷林去世一年整,我拿到了由止庵编的谷林的遗著《上水船》(甲乙两集),真可算作对逝者最好的纪念。止庵“编后记”说“这里汇编谷林先生未收入《情趣・知识・襟怀》(1988)、《书边杂写》(1995)和《淡墨痕》(2005)的文章,共计一百七十二篇”。说到《上水船》这个书名,其中还有一段情节。《情趣・知识・襟怀》原来的书名,谷林“曾拟题作‘上水船集’”。出版社害怕影响销路,因改现题,谷林曾对止庵说“实在不得体”(1997年6月5日)。几年前,我不知内情,莽莽撞撞地发言“……我也不是被最早那本书名很平庸的《情趣・知识・襟怀》召唤去读谷林的,这样的书名一望而知是那个时段的产品。”后来才知道谷林先生的委屈“……拜读到谢其章先生的《你不一定非要读谷林,谷林不该是张中行第二》。这回我厚着面皮把报纸送去住在同院的好友子明兄一赏。子明兄往年主持《读书》时,曾拉我去干过一阵子打杂小工。他读罢谢先生那篇大作,竟然向我表示歉意,懊悔是他当年出错主意,把我那本不成器的小书原来自拟的书名,改定为《情趣・知识・襟怀》。”(《求其友声》载2003年9月28日《书友》报)时至今日,迟了二十年的“上水船”终于还是“打桨摇橹”而来,可惜谷林先生看不到了。于此顺带说一句,谷林是位大隐于市的文化老人,处世极其低调,若不是近些年来止庵先生给他张罗操持地出版了好几本书,也许至今读者对他的认知依然是很浅显的程度,更不要说出版带有抢救性质的《上水船》了。
《上水船》我是当一本语文批评书看的,因为我一直很苦恼写不好文章,有挺好的意思却想不出恰当的词句来表达,勉强表达了,总不如意。谷林先生虽然无法手把手地教你,但是他的文章有示范的作用,你可以看到他“曲尽其妙”的能力是多么地令人叹绝。谷林希望作者冶炼文字,他提出一个要求“摆事实,讲道理,说自己的话”。他还有许多话是冲着编辑说的(譬如《编辑改稿一例》),双方应共同提高文字水平。至于图书的发行、印数、版式、装帧等各个环节,谷林都有精辟的见解,讲得你心服口服。谷林在《一文钱的命案》(原载1979年9月7日《北京日报》)中引宋人罗大经《鹤林玉露》里的一个故事,他的评语是“震世骇俗,自图快意”,“草菅人命,恶劣之极”。我以前没读过谷林这篇,只是在小文《一钱斩吏》(2003年)正巧也讲到这个故事,我的说法是“执法过当”,见识就差得不是一星半点了,更何况谷林文章发表在拨乱反正的当口,言近而旨远。
谷林生活中待人温和宽厚,写文章批评起来却是夹讥带讽,不那么客气。譬如《好文章与糟排印》这篇,一个“糟”字,即可想见老先生的不满之情,――文内语气减缓,措词用的是“遗憾”。在《承讹袭谬失真面》里,谷林对于时下报刊杂志所载人物照片常犯的“张冠李戴”错误很是气恼――“书上为那张相片加注时,左右错了位,把右边那位上海虹桥疗养院院长丁惠康指为罗隆基,并把丁院长之相单独放大,印在书的封面上,让他去享受罗隆基的香火”。末一句就近乎挖苦了,虽然这句话是打郑超麟那借来的“让彭述之几十年间享受了陈独秀的香火”(《颠倒的照片必须颠倒过来》)。有年谱将“知堂和南”错识为周作人的笔名,被谷林看破,谷林接着担心以后会不会有人将“闲步道兄”也错为沈启无的笔名之一。当然我们也不妨把这些讥讽看作谷林式冷幽默。
谷林的严苛不是只指向别人的文章,他对自己的批判也非常之不留情面。《敢,还是该?》这文我是以为与鲁迅的《一件小事》具有同一水准的。这本书还有很多短篇幅的考据,都很有意思。考据很难不出错,高明如谷林,亦百密难免一疏,在“周作人的《先母行述》”一文里谷林的“大胆推想一下”,便是很大的一疏,尽管这回的出错九成的责任不在谷林一方。
前好几年止庵就对我说过,找时间一起去看看谷林,他经常去,我从没去过。大前年父亲听我说起谷林,父亲没看过谷林的书,我就把《淡墨痕》借给他看。原来父亲和谷林1945年的时候都在重庆,鲁迅逝世九周年纪念会他们都参加了,父亲说周恩来那天穿白色西装,就是随便坐在台下的一桌,发言时才上的主席台。《淡墨痕》写的人和事父亲都感兴趣,他说能不能见见谷林,我说我也没见过,先写封信吧,不能打电话,谷林不大愿意接电话。此事后来就拖下来了,――我都跟止庵要了谷林的地址,父亲说不去了,两个老人坐在一起交谈可能很困难,是的,父亲的口音南腔北调我都听不准。
后来有两个机会我见到谷林两回,这时老人已搬到航空学院里的房子。我的日记记下了这两回见面。第一回是2007年7月18日星期三:“(前略)止庵拉着我去谷林家。家在北航大院的一角,屋甚窄小,与小方屋云泥之别。谷林才大屋陋,骨瘦如柴,已不能出门,每日只在斗室中走动,脚脱拉掉一只鞋亦浑然不觉,88岁老人晚境以何堪。据说是暂栖于此将迁新楼。老人说我是‘篇篇好’,我以为是揶揄我《你不一定非要读谷林,谷林不该是张中行第二》里的那句‘不是篇篇好’。告辞,正在话别之际,张倩打我手机问身份证号发稿费用,谷林说,你能记住这么多号不简单。谷林坚持要送到大门口,此第一面也许即最后一面。(后略)”
第二回是2008年3月18日星期二:“(前略)自公司出奔谷林家,车坐不下,谭宗远只好牺牲不去了。谷林比去年见时衣冠整齐,只是佝偻的更厉害了。他说《暮年上娱》是近来看的书,看了还会流泪,书都打包了,没法看,答应送给陆灏的周作人的信也找不到了。谷林还问我龙江有联系吗,好久没来了信也不回,是不是讲他‘繁简混用’不高兴了。董宁文拿出册页请谷林为《开卷》百期题字,找笔找墨一阵忙乱。谷林今年八十九,生活由女儿照顾。自谷林家出,止庵要去买碟,我,董,蔡,司机去鲁迅博物馆赴约。”谷林老人去世,我们难过的程度有所不同,我的感想是“若有所失”。有很多话可说,又不知从何说起。幸而我记日记,虽然日记不能准确表达与谷林老人这两次见面我的感受,但是如果没有日记,我也许没有资格对这么高的一位文化老人的去世说上一句话。
《上水船》不妨比作周有光的《语文闲谈》,惜我术业浅陋,不足以发此书深微,只有闲扯几句,心里头实在是喜欢这书的,故敢向大家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