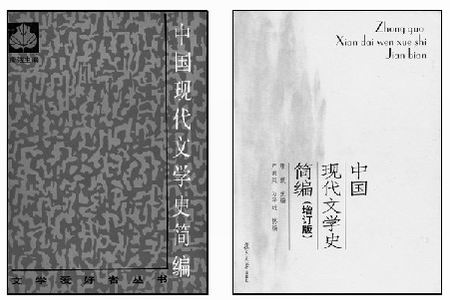
初版、增订版《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
早在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以下简称初版《简编》),是由唐?、严家炎主编的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提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学术研究的日趋深入,对某些作家作品的评价必定有着新的理解和认识,特别是从“史”的角度需要排除“左”的干扰,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于是,原来承担初版《简编》工作的严家炎和万平近对这部教材进行了重新修订和增补,使本书的内容更加全面、丰富和充实。这无疑是现代文学教材建设和学术研究的一件值得重视的事。一
增订版《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已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增订版《简编》)与初版《简编》相比,对某些作家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的评价更加符合实际。
众所周知,最早系统地提出文学改革主张的,是胡适于1917年1月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随后,“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的,是当时急进民主派的代表陈独秀。他在1917年2月发表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中,明确提出“三大主义”,作为响亮口号。胡、陈二人在文学革命中都作出了贡献,他们是战友相互支撑。可在初版《简编》中,字里行间总有贬胡扬陈的痕迹。在增订版《简编》中,肯定了“胡适将白话作为文学改革突破口的主张,是他在关键点上做出的重要贡献”,并指出:当年的陈独秀“给予胡适的白话文主张以坚决的支持”。从而恰如其分地肯定了胡适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
作为一部文学史著,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都应该是信史,真实地反映历史,客观、公正地评价作家作品。然而,由于历史原因,往往对于某些作家作品的评价难以客观,初版《简编》自然也不例外。增订版《简编》改动比较大的是《引言》中“抗战爆发后的文学运动与创作”一节。关键点是对于从国统区来到延安的一批文艺工作者的评价。初版《简编》中,由于“左”的倾向作祟,着重点是对他们如何改造,认为他们的作品错误百出,问题多多,如主观认定某些作品“要‘暴露’延安的‘黑暗’”,“以偏概全,把革命根据地说得漆黑一团”,等等。而增订版《简编》中则强调这些作家的有益思考和他们的作品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指出:“抗战初期来到延安的文艺工作者,大多具有较高的献身热情,愿意将自己的笔服务于抗日战争。随着经验积累的增多,生活观察的加深,他们对文学与政治、文学与生活两者之关系以及怎样更好发挥文学的作用,有很多思考。”不仅如此,还充分肯定了这些作家认真“思考”之后所发表的文章,如丁玲的《我们需要杂文》和杂文《三八节有感》,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以及王实味的论文《政治家・艺术家》和杂文《野百合花》等等。并强调指出:“所有这些文章,都没有把歌颂光明和揭破黑暗割裂开来,或者对立起来;文章的字里行间都有清醒的较为实事求是的深刻分析和坚信革命力量迅速壮大的热诚期待。”这段评述把以往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从而确立了这些作家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应有地位。因为只要我们回溯历史,便不难看出,当年正是这几篇文章屡遭批判。正如增订版《简编》的《引言》所描述的:“在当时严酷的战争年代和极度政治化的具体环境中,这些有意义的文学探讨却被当作危害革命的异端邪说。王实味在1942年夏开始的整风运动中受到批判和清算,被莫须有地戴上‘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暗藏的‘特务分子’等帽子,经长时间软禁,1947年行军途中遭轻率处决。王实味、丁玲、艾青、罗烽等人的上述文章则被视为毒草或政治上的严重错误而长期招致批判,八十年代获得平反正名。”这历史的教训也是一笔财富,值得认真吸取。
在抗日题材小说中,路翎完成于1945年的《财主底儿女们》,是这个时期出现的较好的长篇小说之一,在社会上也有较大影响。可是由于小说的题材涉及知识分子道路问题,当时曾引起争议。初版《简编》虽然指出:“由于作者的思想、生活等多种原因,作品既有显著的成功之处,也有严重缺陷。”但从行文看,着重谈的还是小说的“严重缺陷”。即强调“把具有浓厚个人主义思想的蒋纯祖作为当代英雄加以歌颂,鼓吹蒋纯祖的道路,其实这条道路是一条脱离广大群众、脱离斗争实际的歧路。”而在增订版《简编》中,则增添了这样的论述:“也有人不赞成上述看法,认为它容易导入‘一个时代只有一种典型’的误区。这个问题今后可能还会继续探讨。”把两种不同看法并列,既较为客观,又体现了百家争鸣的学风。
增订版《简编》对创造社作家郁达夫的作品评价也有局部的修改。初版《简编》认为郁达夫30年代初写的《迟桂花》、《瓢儿和尚》、《迟暮》等篇虽然“文笔舒徐清澈,形象新鲜亲切”,“但赞美隐逸生活、表现迟暮心境,同那时风波浩荡的社会现实的距离就远了起来”。而增订版《简编》则认为这些作品在郁达夫的创作中有着“特殊的意义”,并以《迟桂花》为例,认为它写出了“女主人公纯真无邪的美好性格,以烘托男方欲念净化的过程。它们构筑了健全和谐、宁静悠远的另一种人生境界和审美境界,也是作者对颓废美的一种告别”。二
对当年遗漏的作家作品加以增补,使增订版《简编》更为全面和充实。
增订版《简编》足足增补了一节对中国新感觉派小说加以论述。在《穆时英等的都市小说》这一节中,肯定了刘呐鸥、穆时英小说的成就。指出:“刘呐鸥、穆时英的小说,从内容到形式都属于现代都市。……小说的语言、手法、节奏、意象乃至情趣,也有明显的革新和变异。这类作品比较充分地体现了二十世纪文学有别于传统文学的种种特点。”如果说自小生长在日本的刘呐鸥的都市小说上海味不浓,语言也显得生硬的话,那么土生土长的穆时英由于“对上海生活的极度熟悉,创建了具有浓郁新感觉味、同时语言艺术上也相当圆熟的现代都市小说。”从而在人们的心目中有着更高的地位。
当年穆时英发表了一批引人注目的新感觉主义作品,诸如《上海的狐步舞》、《夜》、《黑牡丹》、《夜总会里的五个人》、《街景》、《白金的女体塑像》等等,因而他曾被誉为“中国新感觉派的圣手”。增订版《简编》认为:“二十八岁就去世的穆时英,也许只能算是一颗小小的流星,然而,历史的镜头却已经摄下了它闪光的刹那。”上述评价是公允的,特别是以确凿的史实纠正了穆时英做了汉奸而被国民党军统特工人员暗杀的错误说法,藉以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同样,张爱玲是当年被遗忘的人物,然而她却是一位在当年和此后很长时间国内外颇有影响的现代女作家。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在中国大陆曾一度掀起研究张爱玲及其作品的热潮。为此增订版《简编》在“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文学创作(二)”一章中增补了《张爱玲的小说》一节,专门评价她的小说成就与不足。
张爱玲的中短篇小说着重体现的是上海、香港这类大都市里的两性心理,尤其是女性心理。增订版《简编》把张爱玲小说的成就概括为如下三个方面:其一,在两性心理刻画上“具有前所未见的深刻性”。最典型的人物是《金锁记》中的曹七巧,认为“七巧无疑是新文学中最复杂、最深刻、最成功的妇女形象之一”。其二,另一个独到的成就,“在于意象的丰富与活泼传神”。诸如造语新奇,“通感”手法的成功运用,艺术感觉异常锐敏精微,等等。其三,更为重要的成就还在于张爱玲的现代派小说与传统的民族形式相结合。增订版《简编》认为,她的叙述、描写方面,用的是《红楼梦》式的手法和语言。表面上看,它似乎与新感觉派作家大异其趣。其实不然。这条路子实际上正是新感觉派作家开辟的。“张爱玲终于在尝试运用娴熟的民族形式去表现现代派的思想内容方面,取得了创纪录的成功”“张爱玲虽然不能算是一个狭义的新感觉派作家,但也许可以说在实践现代主义方面是个集大成者。”这样,便把张爱玲小说的独特贡献揭示了出来,从而极大地丰富了增订版《简编》的内容。
当然,增订版《简编》也指出了张爱玲后期创作由于脱离生活所表现出的致命伤:“五十年代所写的《秧歌》、《赤地之恋》等作品,不但内容上不真实,违背生活逻辑,而且艺术上也平淡无奇,失去光泽。”三
通过扩充或重写、改写,增订版《简编》使某些作家作品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各得其所。改动比较大的是关于作家沈从文的创作,初版《简编》只是对此作了一般性的介绍,篇幅仅1800余字。增订版《简编》作了改写和扩充,作为独立一节加以全面评述,达4500余字,不仅分析了他的中篇小说代表作《边城》,而且着重评介了“与《边城》相媲美的另一部地方色彩和乡土气息深厚的”写于1942年的长篇代表作《长河》。认为它“描绘出一幅幅在变动中的湘西农村的风俗图画。”由于“作品多处写到来自近处的压迫者和来自远处的侵略者都给国家和民族制造困难”,也多处“暗示国民党当局视湘西为‘匪区’而阴谋武装镇压”,因而作品送审查机关审查时,被定为“思想不妥”而“多处被删”。这部小说原计划写三卷,第一卷出版时当局百般刁难,迫使作者未再续写。不过,这部小说仍然是沈从文继早年发表的《阿丽思中国游记》、《旧梦》之后篇幅较长的小说作品,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
增订版《简编》对李?人、林语堂及其小说、散文杂文的评介篇幅也有所扩充,使这两位作家均节上有名。对李?人的三部长篇代表作《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第一部)作了较详细的分析和充分的肯定。而对曾有争议的林语堂,对其人有了更多的政治上的肯定,比如他与鲁迅早年的友情就作了更详细的说明。指出:“特别是在‘五卅’运动到‘三・一八’惨案之间的反帝爱国运动的高潮中,他成为以鲁迅为旗手的进步文化阵营的一员,发表不少文章,热情支持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批驳种种诬蔑和攻击爱国学生的歪论,谴责封建军阀及其在文化界代表人物的丑行恶德,发出强烈的民主主义、人道主义的呼唤,颇多浮躁凌厉之气,如《祝土匪》、《丁在君的高调》、《回京杂感四则》、《读书救国谬论一束》、《咏名流》等篇,在当时的爱国运动中产生过积极影响。这几年间,林语堂与鲁迅的个人之间的交往较为密切,在与‘正人君子’的笔墨交锋中相互支持,特别是在女师大事件中,他较坚定地站在鲁迅和爱国学生一边,同当时军阀政府支持下的教育界恶势力作斗争。”正因为这样,两人的名字均被列入军阀政府通缉的黑名单中,随后他们先后离京南下,到厦门大学任教。1927年“四・一二”以后,林语堂虽然“激烈思想”、“激烈理论”逐渐平和,“但对旧军阀仍极为痛恨,对新上台的国民党统治者也有所不满。”20年代末、30年代初,林语堂与鲁迅的个人关系虽然因为偶然因素而中断,他甚至发表攻击左翼作家的文章,但总观其作品“仍有不少针砭时弊、愤世嫉俗之作,继承了‘语丝’时期的反封建精神。”用一句话概括之则是:“林语堂的杂文散文尽管良莠不齐,精芜并存,但在中国二三十年代的杂文散文作家中仍可成为一家。”
关于当年林语堂与鲁迅的关系,福建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原所长,也是承担增订版《简编》工作的学者之一万平近在《对鲁迅与林语堂离合的再思考》一文中说得更为明确:“林语堂说‘吾始终敬鲁迅’,不是绅士式的虚饰话,而是出自学者之口的真心话。”而“鲁迅对林语堂也是尊重的,劝林语堂多译英国文学作品,正是看重林语堂的英语水平和学术修养。”二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上,都有突出的贡献。“从中外文化交流角度说,鲁迅和林语堂所做的译介,恰好起了互补作用。”所以,万平近先生认为:“如果说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宛如源远流长的黄河的话,那可以说,民族感情深厚的林语堂与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的鲁迅,实际上同在这条长河中扬帆前进。”(《新文学比较研究》第59、61、63页)四
严家炎在《增订版后记》中说:“我们曾经想认真写一写包括台湾和东北在内的沦陷区文学,动手以后终因需时太多而只作局部的增补。”正是这部增订后的《简编》尚嫌不足之处。别的尚且不论,仅从当年名噪一时的梅娘(本名孙嘉瑞,现仍居住在北京,笔者与她仍有来往)就很值得认真研究。无论是她16岁出版的中学时期习作集《小姐集》(1936年),20岁出版的小说集《第二代》(1940年),还是她的代表作中短篇小说集《鱼》(1943年)、《蟹》(1944年),当年作为东北沦陷区文学均有较大影响。何况在改革开放以后又先后重新出版了她的《梅娘小说散文集》(1997年,内收小说旧作、散文新作)、《梅娘代表作》(1998年)、《梅娘小说・黄昏之献》(1999年)等。2005年,85岁的梅娘又出版了《梅娘近作及书简》一书。梅娘,是一位生活坎坷而又爱国情深的东北沦陷区著名女作家。而“东北作家群”除了萧军、萧红外,尚有舒群、罗烽、白朗、李辉英、端木蕻良、骆宾其等作家,也应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至于对台湾作家作品的评介,其意义就更是不言自明了。希望此书再版时能够将这些仍被遗漏的作家作品纳入。
增订版《简编》与初版相比,仍然是一部日臻完善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从版本目录学和出版史的角度看,相互比对也有益。就增订版《简编》而言,无论是版面设置还是章节安排,较之初版《简编》都更加醒目与科学,目录也更为准确。增订版《简编》由初版的十二章增至十四章。原书的第十章“反侵略反压迫旗帜下的文学创作”虽然具有时代特点,但显得过于狭窄,而增订版以“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文学创作(一)、(二)”两章代替,并融入钱锺书、张爱玲的小说评价,更符合客观实际。
版本流变和目录的设置在学术研究中是极为重要的一环。已故著名文学史家郑振铎1936年在《中国小说史料序》中这样写道:“‘版本’‘目录’的研究,虽不就是‘学问’的本身,却是弄‘学问’的门径。未有升堂入室而不由门循径者,也未有研究某种学问而不明了关于某种学问的书籍之‘目录’‘版本’的,而初学者,这种‘版本’‘目录’,尤为导路之南针,照迷之明灯。”(《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第86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