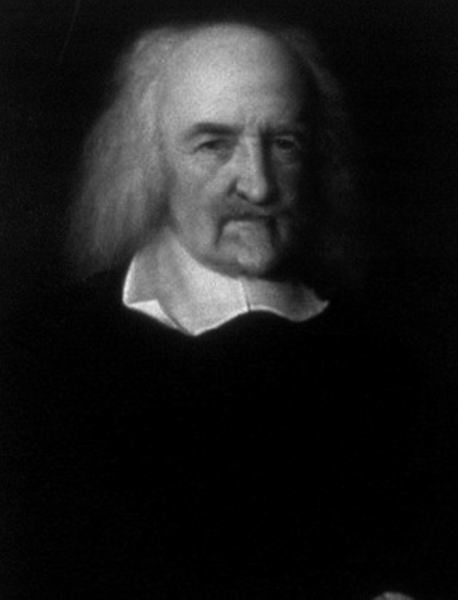
霍布斯
作为17世纪的英国思想家,霍布斯在哲学、政治学、法学、神学诸领域,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但是,在一些中国学者的印象中,霍布斯主要是作为《利维坦》的作者而
《对话》延续了柏拉图的对话体,但又不像柏拉图著作那样:有具体的场景,有具体的人物,人物都有鲜明的性格,甚至说话的神态也栩栩如生。在霍布斯的笔下,贯穿整篇《对话》的人物只有两个:一个是哲学家,另一个是法学家。两个符号化的人物轮流发言,就理性法、主权、法院、死罪、异端、侵犯王权罪、刑罚等7个方面的主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对话》中的哲学家,大体上可以视为霍布斯的代言人。在对话持续展开的过程中,这位哲学家常常居于主导地位。透过哲学家的这种话语优势,我们可以窥探到作者霍布斯的理论宿愿:在法律问题上,法学家的见解应当服从于哲学家的见解。至于《对话》中的那位法学家,则是“普通法从业者”的代言人,他代表了法官、律师等普通法专业人士的立场。两个人的对话,充分展示了在普通法领域中,哲学家与法律人所持的不同立场,他们的分歧虽然体现在不同的法律领域,但却聚焦于一个关节点:对于主权者的不同态度。
在哲学家眼里,主权者至高无上,具有不可动摇的绝对地位;代表王权的衡平法院则具有超越于普通法法院的优势地位。与之相反,代表普通法共同体的法学家,则习惯于以法律理性、技艺理性自居,试图坚持普通法抵制王权恣意的自治传统。哲学家要求普通法服从于主权者、服从于王权,法学家要求普通法具有独立于王权的自治地位;如果说,法学家旨在强调普通法的自治和相对独立性,那么,哲学家则立足于主权者的立场,努力为主权者和王权而声辩。
在“论理性法”一节中,法学家通过引证柯克爵士的《英格兰法总论》,认为法律理性并不是人人都有的自然理性;要获得法律理性,必须通过长期的研究、观察和经验,因此,法律理性是一种技艺上对理性的完善,是一种具有高度专业性的“技艺理性”。法学家的这种主张,显然是希望垄断“法律理性”,排斥“普通法圈子”外面的其他人(包括国王)染指法律事务,入侵法律人的专业领地。但是,这种高筑“专业门槛”的企图,遭到了哲学家的反对。在哲学家看来,法律的知识是通过大量的研习而获得的,“跟所有其他的科学一样,如果它们被研习和获得,它们就是通过自然理性而非技艺理性实现的”。换言之,获得法律知识凭借的是人人都有的自然理性,而不是什么技艺理性。此外,哲学家还认为,“法律理性”是一个含混的词,“我猜它的意思是,一位法官的理性或全部法官的理性加在一起(不包括国王)就是那最高的理性,就是法律,对此我表示反对。因为除非拥有立法权,任何人都不能创制法律”。哲学家强调:所有的英格兰法均由诸位国王制定,法学家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
在“论主权”一节中,法学家提醒哲学家:制定法已经明文规定,国王要约束自己,未经国会同意不得向臣民征款,这样的制定法从爱德华一世开始,就得到了其他各位国王的确认,并最终得到了目前在位的国王的肯定。法学家的意思是:国王尽管在万人之上,却在这样的法律之下。但是,哲学家对此并“不满意”。因为,“平头百姓,如恒河沙数,我不过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为了这些人的福祉,上帝任命了国王和其他主权者”。为了保护百姓免受异邦人的统治和奴役,为了避免内战所带来的破坏,为了人民的安全对全能的上帝负责,国王应当享有征募的权力,不必受那些制定法的约束。因为说到底,法律还是国王制定出来的,“这些国王制定法律时,要么单独依靠他们自己的理性,要么加上国会上下两院的建议,用不着法官或其他的法律专家。因此你看到,是国王的理性(不论其多少),而非法官的理性、博学或智慧,才是法律的灵魂,才是最高的理性”,因此,“法律就是拥有主权的一人或多人的命令,向其臣民公开、明确地宣布他们何者可为,何者不得为”。这就意味着,即使在法律领域,国王的理性也绝对地高于法律人的理性。
在“论法院”一节中,法学家强调了国王与法院之间的权限划分:由于国王已经将他的全部司法权分别委托给两家法院了,因此,如果有人将诉状呈递给国王审判,那么,这样的呈递就将是无效的呈递,因为,国王已经没有亲自审判的权力了,―――其审判权已经转移到法院了。对于这样的“司法自治”,哲学家无法赞同。他认为,国王是一切世俗诉讼和教会诉讼的最高裁判者;法学家的错误,在于没有分清权力的委托与转让:转让权力的人便剥夺了自己对于权力的享有,但是,将权力委托给另一人,以本人名义,在本人监督之下行使,本人就仍然拥有同一权力。国王向法院授予司法权,就是权力的委托,而不是权力的转让。因此,如果有人向国王提出诉讼请求,这种请求是有效的,国王是可以受理的。哲学家的这种态度,旨在排斥法律人对于司法审判活动的垄断。不仅如此,哲学家还对当时的普通法实践,给予了严厉的批判:“现在的人们比过去更懂得对制定法的用语吹毛求疵的技艺,由此鼓动了他们相互睚眦必报。此外,普通法判决的五花八门和自相矛盾确实经常平添了人们胜诉的期望,而按道理这些诉讼根本站不住脚。另一个原因乃是他们对自己的讼案中何谓衡平一无所知。研究衡平者并非百里挑一的人中翘楚,律师们不是在自己胸中寻找判决,而是查找前任法官的先例,……最后,我相信在古代,律师们没有那么贪得无厌、惹是生非;自从和平年代起,人们有了闲暇研习欺诈,并在怂恿争辩的人那里找到了差事。”
随后几节讨论具体的罪与罚,由哲学家主导的系列对话依然坚持同一个主题:对主权与王权的辩护。譬如,在“论死罪”一节中,哲学家要求扩大重叛逆罪的种类,他还自行概括了7种罪名,认为在制定该法之前,就应当属于重叛逆罪。在罪行的证明标准上,哲学家主张,“密谋就是使一件罪行被定为重叛逆罪的惟一根据;因此不单是杀害,连图谋也被定为重叛逆罪”,这样的“低标准”,显然有利于主权者。在“论异端”一节中,哲学家认为,“教义和火刑之间存在怎样的比例关系,二者之间的分配不存在均等、多数和少数。而二者之间的比例关系就是教义造成的危害与强加给神学博士的危害之间的比例关系。其间的分寸,只能由负责统治人民的人来衡量,因此,对违法行为的惩罚也只能由国王来确定”。在“论刑罚”一节中,哲学家批评了普通法传统中的大量酷刑,认为这些“不合理的习俗不是法律,只应当废止。还有什么习俗比惩罚无辜者更不合理的呢?”
通过以上勾画,一个哲学家的形象已经浮出水面:一方面,他批判普通法共同体的自治传统及其理论基础;另一方面,他试图通过对普通法的改造,努力将普通法招安,使之归顺于主权者的羽翼之下。在对话中处于某种陪衬地位的法学家,则类似于柯克爵士的代表:惯于恪守普通法的传统,竭力论证普通法自治、自主的合理性与正当性,但他在哲学家咄咄逼人的攻势前,不仅没有还手之力,招架之功似乎也嫌不够,―――这也不难理解,因为整篇《对话》,本来就出自于一位哲学家之手。
《对话》虽是霍布斯晚年的作品,但在思想倾向上,却与《利维坦》一脉相承:都坚持和强调主权者的绝对地位;都在为王权提供着某种理论上的辩护。这样的理论主张,在现代中国的语境下,容易被斥为保守、落后;除了充当学术批判的靶子,似乎没有多少正面意义。但是,这样的评价显然是偏颇的。透过长达数百年的“英国革命史”,我们可以发现,英国革命的不彻底性、妥协性、渐进性,与霍布斯的理论主张具有很大的关联度。到底是霍布斯的保守理论导致了英国革命的渐进性?还是英国革命的渐进过程塑造了霍布斯理论的保守性格?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究竟如何?对于这些疑问,暂且存而不论,单就霍布斯理论的保守倾向而言,就包含着值得借鉴的积极意义:即使是在变革的时代,也不要忘记对于秩序的维护,以及,对于现状作必要的肯定。因为,现状和秩序是任何变革的基础,如果把现存的一切都否定掉了,把现存的一切全部砸碎,新的制度又将附丽于何处呢?
事实上,在任何一个强大的文化传统中,都需要两种性格的学术理论:守成的理论与革新的理论,前者强调守成的重要性,注重的是革新中的守成;后者强调变革的重要性,注重的是守成中的革新;没有前者,社会可能陷入混乱;没有后者,社会可能趋于停滞。如果说,法兰克福学派早期的批判理论、昂格尔的批判法学代表了革新的理论,那么,霍布斯的保守理论、后来的奥斯丁的“恶法亦法论”,就代表了守成的理论。我相信,只有这两种理论所形成的张力,才可能让一种文明既不乏创新的空间,也能保持基本的秩序。从这个意义上说,霍布斯的《对话》,尽管着眼于为主权者声辩,其理论价值也值得予以重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