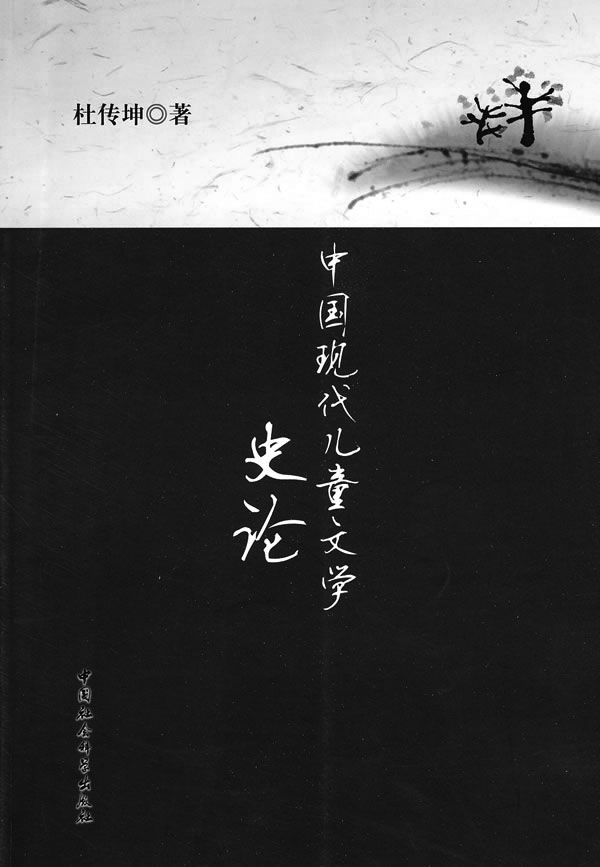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论》是史论。史论,论史,难得的是史识,这本专著的最大成功也在史识。在出发点上,这本书是对成人文学领域“重写文学史”的一种回应。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需要重写,不只在其因为历史
建构论打开了儿童文学研究的崭新视野,从这种新视野出发,《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论》虽只偏重在“论”但事实上已经开始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的“重写”。此前,在儿童文学研究领域,曾有儿童文学产生或自觉于晚清、清末民初、五四及“古已有之”等不同说法,作者认为,这种区分或争论没有根本性的差异,因为它们所持的都是现代性的本质论、决定论。“所谓起源已经不再是一个历史时期的划分问题,而在于区分一种态度,区分一种‘计划’。”因此,作者重写现代儿童文学史,既不想和此前的本质论一样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划定一个明确的起点,也不认为其发展中真有一条理性的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线索。虽然从第二章到第五章作者论述现代儿童文学的发展也大体遵循了时间的顺序,但更多强调的仍是不同“计划”的展开,这些“计划”并不都是前后承袭的发展关系,甚至也不都处在相同的时间轴线上。不仅如此,作者还进一步揭示了这些不同“计划”后面包含的真实意识形态用意。“儿童文学是为了儿童、用于儿童的政治-文化的文学显现。这样一来,儿童就不再是构成世界(本质上即成人眼中的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或者说是最有潜力最有生命力的部分,而是一个成人世界不得不面对的‘他者’。所谓为了儿童的书写也就是为了一个‘他者’的书写。”这样,“儿童”、“童年”、“儿童文学”等等的建构,其实也是一种权力运作,作者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的“重写”便首先成为一系列权力运作的揭示。比如五四时期影响颇著的“儿童本位论”,作者就看出,其后面其实源于卢梭、浪漫主义的文学理想。而当时人们所以弃许多其他与儿童、儿童文学有关的文学思潮于不顾,而单单选中儿童本位论,这和当时一代知识精英的社会、文化理想紧密相关,或者说,正是这些知识精英的权力运作,才使儿童本位论作为五四儿童文学的显学浮出历史的地表。人们按自身的影像构建着作为“他者”的儿童和儿童文学,同时也在构建着自己。
视界不同,不仅看到的“历史”不一样,看到的具体的作家、作品也不一样。在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进行“重写”的时候,《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论》对许多儿童文学作家、作品也进行了“重写”。比如叶圣陶,这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中一个极为重要的作家,鲁迅说他为中国童话开辟了一条自己创作的道路,尤其是其从中国古典文言化出来的典雅而又十分流畅的语言,表现上有着民间文学的特征但骨子里却是非常文人化的、属于中国古典诗词神韵的意境,以后半个多世纪几乎无人堪与比肩。杜传坤在肯定作家一系列划时代贡献的同时,对其作品只是“为儿童”而不是“儿童化”的倾向给予了尖锐的批评。虽然我个人觉得这些评论有点偏苛,但其指出的问题是存在的。在叶圣陶童话中,浪漫主义、唯美主义和写实主义,成人视角和儿童视角,一直都是矛盾的、交织的存在的,且前期和后期还有差别。作为五四那一代的人,他们更多是把儿童文学当作反映、理解“儿童问题”的一种方式、手段来看待的。他们以这样的方式形塑出这样的儿童形象是他们只能以这样的方式形塑出这样的儿童形象,这样的儿童形象是“他者”,但也映照着他们自己的身影。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论》中有些问题也是可以进一步讨论的。“儿童”、“童年”、“儿童文学”都是建构出来的,这种建构是既受“主体”尺度的制约也受“物种自身”尺度的制约。《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论》的着力点在“主体”的尺度,而于“物种自身的尺度”则较简略。“儿童”在文学叙事中有多重含义,如描写对象、叙述者、读者等。读者又分现实读者和隐含读者。我们判断一部(篇)作品是不是儿童文学,首先着眼的是作品的隐含读者。但隐含读者在文本中,只是作家为读者设定的一个位置。作家设置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为什么设置这样一个位置,不完全取决于作家自身的理想、愿望,也取决于现实读者的接受视野及作家对这一接受视野的自觉及认同程度。而这个现实的儿童的接受视野是有很大的客观性的。中国古代儿童文学不能自觉,或者说不能被现代以来这种方式有效地建构,与中国古代社会中这个现实的儿童接受视野并不存在有直接的关系,而清末民初人们所作的工作,也在这个现实的儿童接受视野、儿童文学消费市场的建构上。这样的读者接受视野和读者消费市场的建立也不可能是一个一劳永逸的过程。事实上,从清末民初儿童文学自觉以来,这一过程一直没有中断过。这里不仅涉及到人们的思想观念,还涉及到一些很具体、很技术性的操作,如印刷技术的进步。我们现在看到的儿童图画书,在五四时期不仅无法做到而且简直是很难想象的。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可能不得不考虑这些因素。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论》,杜传坤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11月,39.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