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宗族在中国的发展,会出现南方远较北方强盛的现象?英国人类学家莫里斯・弗里德曼认为,广东、福建等中国东南部地区的“边陲社会”特点,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但香港中文大学科大卫教授的新书《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告诉我们,宗族之所以会出现在珠三角地区,非但不是因为天高皇帝远,反而恰
这场始于明朝的共谋,其内在机制是大一统王朝不断对地域社会政治整合的延续。在宋元时期,王朝对珠三角地区的整合更多是以佛教寺庙的形式体现出来的。明初以后出现的一些因素,诸如里甲制的推行、沙田的开发、文字的普及与科举的兴盛、贸易的发展等等,促使国家与地方社会都开始把宗族作为建立社会秩序的基础。16世纪中叶的地方动乱则是这场共谋的直接契机,不仅王朝国家的里甲制度藉此得以全面推行,成为宗族出现的制度基础;而且地方士绅也通过礼仪的变革,开启了宗族作为一种“文化创造”的发展历史。此后的三个世纪,无论是宗族的发展与普及,还是以宗族的形式参与商业贸易和地方事务,地方士绅都发挥了主导作用,从而使珠三角的宗族发展表现为“士绅化”的模式。明清时期宗族发展的另一个显著特性,是它往往以乡村而非城市的制度出现。民族国家确立以后,当新的国家体制将整合的重心转移到城市,皇帝和祖宗共谋塑造地方社会的现象也就从此慢慢淡出了历史的主流。
莫里斯・弗里德曼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的两部中国宗族研究著作,强调宗族是一个控产机构,从而开创出一种从宗族的角度把握华南乡村历史的研究范式。受其影响,科大卫在第一本专著《中国乡村社会的结构》(The Structureof Chinese Rural Society)中,发现作为乡村联系国家的工具,香港新界宗族的发展与“入住权”有着密切的关系。此后的二十年间,随着视野进一步拓展到珠江三角洲地区,长年的田野调查,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的占有,加之商业史、礼仪等新视角的引入,科大卫将宗族的历史放在地方的和政治的脉络中,重新理解了中国社会从明嘉靖年间开始发生的结构性转变,实现了对弗里德曼宗族研究范式的继承与突破。
范式的创新,体现了本书作者的个人才智。同时,这也是一群“有着共通的兴趣,没有竞争的心态”的学者们集体智慧的反映。过去二十年来,作者与一批香港、内地以及海华朋友们,他们扎根乡土(down to earth),把田野调查视为历史学家的家常便饭。他们关注地域社会的历史脉络,也强调要从地域社会的角度重新思考王朝典章制度的推行。他们逐渐形成了以历史学为本位,同时又大量借鉴了人类学等社会科学的“历史人类学”理论范式。《皇帝和祖宗》一书,无疑为了解这个被学界冠以“华南学派”学术共同体的理路与观点,提供了一份直观而厚实的范本。
无论是“华南学派”的标签,还是本书的副标题“华南的国家与宗族”,似乎都在彰显着“华南”的地域性。然而,本书的作者早在十年前就大声疾呼要“告别华南”。而在这部集结了他二十多年华南研究的大成之作中,科大卫也从实证与理论两方面,再次明确了华南学派对于区域研究的定位:“区域历史的研究,如果不能产生出宏观分析,就会变成狭隘的地方掌故。对于一个区域的优秀研究,会迫使我们对中国其他地区提出新问题,如果考虑周全的话,甚至会迫使我们对中国以外的社会提出新问题。”(《皇帝和祖宗》第351-352页)科大卫教授和他的朋友们有一个伟大的野心,要通过研究人类的活动如何影响区域社会的形成,来重新全面地理解作为大一统王朝的“中国”的历史。在他们看来,“以儒家为主导的大一统只是历史上一个特定的时期,由小部分的人所推广的历史;中国大一统的历史,是由很多人参与构建的历史,要明白大一统的历史,也就是要明白这个参与的过程”(《历史人类学学刊》第六卷第一、二期合刊,第18页)。循此理念,既然边陲之地的故事是天高皇帝也并不远,那么那些早已整合进大一统王朝的化内之地,以至于天子脚下又会是怎样的情形呢?科大卫将会讲述怎样的故事?对此,我们完全有理由对“告别华南”之后的科大卫教授充满期待。
学术书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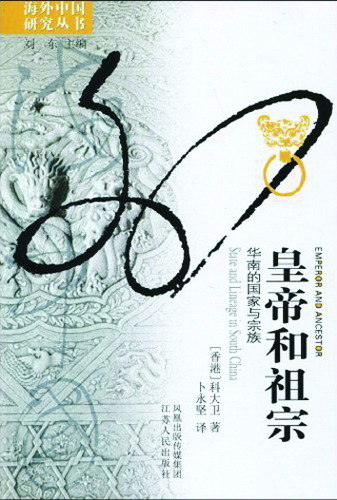
《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科大卫著,卜永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9年11月第一版 32.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