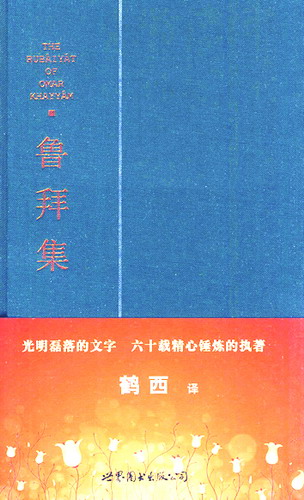翻译界向来有诗不可译的说法。雪莱曾说,“译诗是徒劳无益的”;美国诗人弗罗斯特说,“诗就是在翻译中丧失掉的东西”。可见诗歌翻译之难。但在世界翻译史上有一部译诗集的成功是举世公认的,它就是19世纪英国诗人菲茨杰拉德翻译的波斯诗人海亚姆的《鲁拜集》。《鲁拜集》也吸引了中国许多学者、作家和翻译家从事汉
初闻程译鲁拜,是在陈四益的《关于中译〈鲁拜集〉的补记》一文中。程侃声先生是水稻专家,一生颇多不幸,临终译稿也不曾出版,令人扼腕叹息。译鲁拜的专家黄杲α曾说:“无论是欧玛尔・哈亚姆的原作,还是菲氏的英译,更像是璀璨的钻石,而每一个译者就像是工匠,各自在这钻石上打磨出一个有特定角度的反射面。译者越多,这样的反射面就越多,钻石也就更光华四射。这些反射面还有折射作用,能够折射出一些文学和非文学现象,折射出诗歌翻译在我国的发展历程。”因此今年5月获知程译本出版,作为鲁拜爱好者和研究者的我,欣喜自不待言。
该书定价80元,价格不菲,但装帧漂亮雅致(布面刷金口)。封面上书:“光明磊落的文字六十载精心锤炼的执著”,下面是“鹤西译”三个大字(鹤西是程侃声先生的笔名)。这精美的包装让我觉得会物有所值。但当我细细读过全书之后,心情隐约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失望。
一、苍白的译文
首先是程侃声的译诗。书的封面声称这是“六十载的精心锤炼”,“出版后记”里评论说,“程先生拿出来的译文,都是声音韵律与内容表达上自己满意的”,而网络上的广告则更进一步:“鹤西先生的译本,不是每一首都达到了无可比拟的高度,但是我们说鹤西译本超过以往郭,黄等人的译本,就是因为句子意思还原准确,呼吸感和韵脚好,句子通顺”,“鹤西先生的译稿译者用数十年功力完成的,语言优美流畅,文辞清新,与此前十个译本迥然不同”。
事实果真如此?首先要说明的是,鹤西的《鲁拜集》转自菲译的充其量只有31首,转自Whinfield的倒有44首,后者值不值得转译还是存疑的。鲁拜集英译者众多,但普遍认为菲茨杰拉德是无人能够超越的。郭沫若就曾说过:“‘鲁拜集’的英译,在菲茨杰拉德之后,还有Whinfield、Dole、Payne等人的译本,对于原文较为忠实,但作为诗来说,远远不及菲茨杰拉德的译文。”曾任美国驻英大使的约翰・海伊在1897年的海亚姆俱乐部的讲演中也说:“菲氏译诗的最显著特点之一恰恰是对原作的‘忠实’。简而言之,海亚姆是菲茨杰拉德的前身,菲茨杰拉德是海亚姆的投胎转世。”海伊所用的“忠实”一词并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忠实,即内容和表达跟原文的逼真程度,而是更高意义上的精神耦合。从这个角度而言,菲译是最“忠实”的。这也就是英国东方学家艾伦认为的:菲氏的鲁拜“从纯粹狭义的翻译角度而言,并不是翻译,但从‘翻译’一词最经典的意义而言,毫无疑问这是翻译”。菲茨杰拉德之后,《鲁拜集》的英译本不下数十种,但从没有哪本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真神只有一个,那就是菲茨杰拉德。所以其余的译本需不需要译,这是个问题。如果译作不全是来自菲译,则需注明,而不要在扉页含糊地写:“菲茨杰拉德第五版,鹤西选译。”这样岂不是混淆视听?因为读《鲁拜集》的人都清楚,我们不仅在读海亚姆,也在读菲茨杰拉德!
鲁拜选译本是难以“管中窥豹”的,因为是菲茨杰拉德创造性地把那些原本不连贯的、孤立的四行诗编织成一个始于苏丹塔楼上的晨曦,终于波斯草地上的月光的生命历程,加入自己的天才,使之浑然一体。从菲译中选出31首无疑是以偏概全,特别是全诗中最能体现海亚姆哲学的“酒罐对话篇”,程根本未译。80年前朱湘译了15首鲁拜诗,就含有这9首,可见诗人目光如炬!从这个角度而言,程先生在“译后记”里说“这七十多首,已经足够概括奥玛诗的内容和风格,而不在乎其多少”。多少有些言过其实了。
译本的质量是不是超越了其它译本呢?我们的探讨放在前31首上。先看第1首,即菲译第四版第7首(《鲁拜集》中的诗一般都需以数字表明其顺序,程译本不注明,这是和历来鲁拜英汉语译本相悖之处),程译如下:
来,满上一杯,就着春天的骄阳,
抛掉你悔恨的冬裳。
时间这鸟儿不会飞得太远,
而它啊已开始展翅飞翔。
相比较其它译本,比如郭译:
来呀,请来浮此一觞,
在春阳之中脱去忏悔的冬裳:
“时鸟”是飞不多时的――
鸟已在振翮翱翔。
飞白的译本则是:
快斟满此杯,把你后悔的冬衣
扔进春之火中烧毁:
时光之鸟飞的路多么短哪,
而且你看!它正在振翅疾飞。
相形之下,程译本远远没有郭译本和飞白译本的速度、力度和激情,“展翅飞翔”相比较“振翮翱翔”和“振翅疾飞”,哪个更有力?“时间这鸟儿”跟郭译本大胆借用“时鸟”相比,哪个更富创造性?跟飞白的“时光之鸟”相比,哪个更有历史感?再看其他译本的后两句:
时间之鸟飞还未远,
春禽正凌风展翼。(邓均吾译)
由来时逝如飞鸟,
振翼凌空不可留。(吴宓译)
记取时鸟飞程短,
时鸟此际已翱翔。(李霁野译)
无论是白话的译文,还是旧体诗译本,都优于程译远甚。
我们再来看第2首,即菲译第8首,该首是全集中的精华,特别是后两句“The Wine of Life keeps oozing drop by drop,/The Leaves of Life keep falling one by one.”堪称经典。它极为工整,本可译为中文的对句,因为对仗向来是中诗之长。可是在程的笔下,成了:
生命的酒在一滴滴地流淌,
生命之树的叶子正一片一片凋落飞纷。
第二行比第一行多出5字来,破坏了原诗的平衡感。再看其它版本,郭译本是:“生命的酒浆滴滴地浸漏不已,生命的绿叶叶叶地飘堕不停”。施颖洲的译本是“生命之酒不断涓涓渗注,生命之叶不断一一飘沦。”黄克孙的译本是“酒泉岁月涓涓尽,枫树生涯叶叶飘!”李霁野的译本是“生命琼浆涓滴逝,人生绿叶渐飘零。”邓均吾译本是“生命之酒一滴滴在渗出,生命之叶一片片在飘零”。各家都在尽力体现原诗的对仗,所用的词语也体现原诗的美感,相比之下,后来者的程译最缺乏诗意。
再随便看一首吧,比如第40页的菲译63首,程译如下:
哦,对地狱的恐惧,对天堂的希望!
至少一件事还是真的――此生正在飞翔,
只有这件事是真的,其他都是说谎;
曾经开放过的花儿已永远凋亡。
比较1922年就发表的郭译:
啊,地狱之威胁,天堂之希望!
只有一事是真――便是生之飞丧;
只有此事是真,余皆是伪;
花开一次之后永远凋亡。
我们发现两个版本雷同之处甚多,连韵脚也惊人相似。只要是不同的地方,便是逊于原译的地方,比如“飞丧”改成“飞翔”。只要是添加的地方就是累赘的地方!比如“只有一事是真”改成“至少一件事还是真的”。这样的译诗能称得上“完美”?不由让人怀疑:是“六十年的锤炼”,还是“六十年的延展”?
而这绝不是孤例,比如程译第16页的诗和郭译第28首的雷同,第18页和26页的诗远逊于黄杲α的译本,第32页的诗远逊于李霁野的译本。鲁拜爱好者找来一一比对,自不难看出。这些都在告诉我们一些译诗的基本道理:后来者未必居上,花费的时间长不等于高质量。
二、不够专业的注释
程译鲁拜还有一个重大缺陷在于注释者尚欠专业,起码他不是对《鲁拜集》下了大功夫的研究者。据广告说,“这一次由熟悉英文、法文和中古波斯文(巴列维语)的刘乐园先生对于常人不能解的英文语句做了全新的注释约四十余处,旁征博引,均为前人所未发。有的诗句的考证和解读,就是英美两国的《鲁拜集》研究者也没有认识到的”。北大有研究《鲁拜集》孜孜不倦的学者,如张鸿年、张晖,还有年轻学者穆宏燕,但是刘乐园在鲁拜研究界声名不显。纵观全书,可以看出,这位注释者对《鲁拜集》还不够深入。
首先是他对《鲁拜集》的考证不够深入,致使行文失之粗疏。比如他在“出版后记”里写到“近百年来无论是英美国家常见的英文注释本还是中国或日本的诸多译本的理解都存在很多问题”。这“近百年”就很不准确。事实上《鲁拜集》早在1869年就引起了学术界的评论,在19世纪最后10年更是注家蜂起,达到高潮。海亚姆狂热的风起云涌集中在1890至1910年,怎么也是百十年前。另外“出版后记”里还说到“钱锺书先生早年也曾译过《鲁拜集》,不过译稿没有公布”。事实上从《槐聚诗存》中我们得知,早在1937年,钱锺书曾写有一赋,赋前有序,序中涉及到《鲁拜集》第12首的英译和法译,但这跟“钱锺书先生早年也曾译过《鲁拜集》”可是两回事。对于钱锺书素有研究的郑延国曾评论说:“老人家(指钱锺书)兴许还有点遗憾:要是当年他也能像现今的柏女士(柏丽)一样,拨冗将Rubaiyat译为中文的话,肯定能使国人多拥有一本别具风味的《?醅雅》(钱锺书对rubaiyat的译名)了”,亦可佐证。这些细节反映了他学术态度不够严谨,虽有“大胆的假设”,却缺乏“小心的求证”。
再说注释的内容,也并非无懈可击。比如第27条,讲的是因为陶土由人变来,所以水经陶罐就变苦了。他的注释说“波斯古代诗歌里讲到”,其实还可以写得更准确,这个典故来源于波斯诗人阿塔尔的《鸟儿大会》,菲茨杰拉德在翻译《鲁拜集》前后也曾译过《鸟儿大会》,所以就把阿塔尔的东西张冠李戴放进译诗中来。第28条注释者用洋洋洒洒几千字讲cypress一词,唯独没有提到关键一点:“翠柏优美,不过你的身体比翠柏优甚”这个比喻来源于菲茨杰拉德阅读的一本波斯语入门书:威廉・琼斯的《波斯语语法》。并且,是菲氏自己把这个比喻放进诗歌里来的,海亚姆原诗里并没有。第29条谈到,注释者谈到“khayyam出生于一个制毯匠家庭”,而事实上他的姓“海亚姆”意思是“帐篷制作者”(tentmaker),可“帐篷”绝不是“毯子”,不知注释者说的“制毯匠家庭”根据何在?可见三个连在一起的注释都或多或少存在缺陷。
最不可容忍之处是注释者对其他译本肆意批评。比如他批评黄克孙的翻译“有一种五或七言打油诗体的译本,自以为得计说是‘遗貌取神’,其实完全不着四六,彻底丧失了《鲁拜集》集中伊壁鸠鲁主义哲学”,这种批评我们看不到真诚,看不到严谨。黄克孙的译本“遗貌取神”并非自夸,而是淡江大学宋美?教授评论的。钱锺书对黄译颇为夸奖:“黄先生译诗雅贴比美Fitzgerald原译。Fitzgerald书札中论译事屡云‘宁为活麻雀,不做死鹰’,况活鹰乎?”钱锺书认为黄的译本把原作译活了,没有辱没菲茨杰拉德。哈佛大学教授杨联?也题诗云:“我爱黄君寄托深,能翻旧调出新音。诗肠九转通今古,四海东西一样心。”余杰曾写过:“黄克孙先生译《鲁拜集》,字字含香。其中有一首小诗意境空旷寥远,我时时吟诵。诗云:‘绿酒朱唇空过眼,微尘原自化微尘。今朝我即明朝我,昨日身犹此日身’”。黄译鲁拜最脍炙人口的一首如下:
一箪疏食一壶浆,一卷诗书树下凉。
卿为阿侬歌瀚海,茫茫瀚海即天堂。
黄译此诗的时候,年方二十出头,正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物理学的学位。我们再读一首黄克孙自己写的诗:
长空万里碧无瑕,轻度孤云薄似纱。
想是蓬莱羽仙驾,乘风飘到玉皇家。
黄写这首诗的时候是1942年,那一年他14岁。可以说黄是一位天才型的诗人,其一生从事物理学,与海亚姆的精神颇有相通之处(海亚姆是有名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总体而言,黄译的确是堪媲美菲译的佳作,不知在注释者笔下为何变得如此不堪?我们在推出自己的东西的时候,是不是非得要把别人的说得一文不值?
这位注释者也下过一些功夫,他谈起注释中的9处困难,将其比喻为“九个地雷”,并说“一百多年了,这九个地雷,美国英国没有人能扫掉”,又说“我们不敢说自己多么了不起。但是,我们为了扫掉这九个地雷,做了15年的语言上的准备工作,我们在十年前就注释过鲁拜集,因为当时程度不够,暂时搁浅,又准备了十年,调动了哈佛和UCLA以及北京大学一线同行的研究力量,才把这九个雷解开。我们不敢说自己的工作无可挑剔没有漏洞。但是,至少,我们真刀真枪回答那九处疑难,一百年以来第一次,将九个地雷全部扫掉了”。这显然又是言过其实。英美对《鲁拜集》的注释汗牛充栋,早在百年前就有了汇聚多种欧洲语言的“百衲本”出现,连每个字在哪一版的哪一行的索引都已出版,更别说其中涉及的每个典故的来源。注释者要发如此“豪言壮语”其原因不外有二:一是广告需要,二是无知者无畏。
至此,我想结论已经很明显了,那就是:精美的包装下苍白的内容,澎湃的豪情中内荏的实质;菲译《鲁拜集》是经典,但眼下的程译本似有炒作之嫌。《鲁拜集》值得研究,也欢迎新的译本,但我们需要的是实事求是的研究,是具有创新意义的译本,是懂得“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学者和译家。套用今年北京的高考作文题,可以说《鲁拜集》翻译和研究既需要“仰望星空”的远大理想,又需要“脚踏实地”的工作态度,不知这一版本的当事人做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