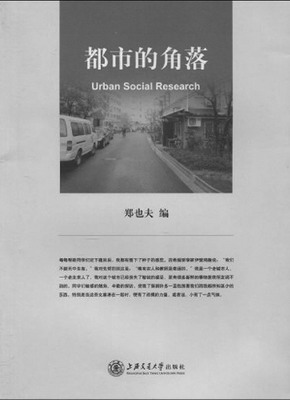
几年前,看郑也夫教授为他的学生们编的社会调查实录《都市的角落》,在他的前言中,饶有兴趣地读到:“2001年末,我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出席一个工作会。我向同仁们介绍我所指导的学生们从事的城市调查。我说,这些
社会学是怎样的一门学问?有人说:社会学就是一些学者故意用大家都不懂的概念去说本来大家都懂的事――这个社会学者多半是不能接受的。社会学早已在现代社会科学殿堂里登堂入室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社会学者不仅习惯了以自成学科体系的理论和方法自誉,也已经惯常于依靠概念、逻辑、数据、模式等等来描述“社会事实”、说明“真相”或“关系”。所以,像郑也夫这样的社会学教授,花那么大的精力,去指导学生们做既不以理论或对策为目的、也不以学术性为标榜的城市社会调查,然后与学生一起编写出一本又一本一般读者能看懂、但教师不一定能拿去报课题项目或学术奖的调查文集,就隐隐然成了一种需要点解释的学界另类现象。
“意义”,这个词在今天已成为所谓现代性反思的深奥主题,也是哲学家思考的玄妙问题。与此同时,我们这些普通的人们,似乎正在失去由个体去面对这个问题的勇气和思考这个问题的能力――或许根本自始就很少被赋予这种意识。以社会学教师为职业,除了由行政和学界来评价并给以地位报酬的“理论的、方法的”贡献(以及各表其意的“社会贡献”),还有什么样的“意义”是我们所需要的,是我们该念兹在兹的?
笔者私下里有时会用“开社会学之眼”来形容大学社会学教学的目标――让学生学会用自己的眼睛、去发现社会学意义上的事实。但到底何谓社会学之眼、又如何可开?终是乏言可陈。这目标可望而不可及,对学生、对教师都只能是种想象的境界、甚至是种自寻的折磨吧。
但其实也并不是完全找不到解惑之参照。读郑也夫教授与他的学生们的调查集,在感到新奇、亲切的同时,我们不难感受到那种以开启学生心智和潜能为志业的教学意图和方式――让学生在接受理论方法训练的同时,自由地选择自己真正关心、且深具社会学探索意义(这个由指导老师帮助把握)的问题,然后走入社会,去看去听、去建构有关城市社会的经验事实。于是,我们看到,那些在社会学论著中通常被概念所抽象、被类别所归纳、被结构特性等等所化约的千姿百态的城市景象――就像编者以“市场万象”、“生民百业”、“大国小鲜”、“粉丛乐迷”、“学子外传”等分标题所呈现的那样――被翔实生动地观察、记录下来。读者看过去,虽处处是社会学的视野,却依然像是社会自身。于是我们会慨叹:原来我们身处其中的城市,所谓的“社会群体”、“阶层结构”、“社会生活”、“城市生态”等等,竟然可以被这样呈现出来。
笔者注意到,在介绍这样一种教学方式的宗旨的时候,郑也夫教授提到了“认知者的乐趣”,还提到了“社会学家的责任”(《众生的京城》“前言”)。作为同行且同样从事城市社会学教学和城市研究的人,笔者自认是多少可以理解,这些看似常识之谈,而如今在我们的大学里,却是一份怎样的奢侈!是的,所谓开启“社会学之眼”,首先要做的,是致力于培育自己以及学生具备作为研究主体的健全的心智,包括人之良知、求知之欲,还有社会学的想象力,以及对“田野”“社会”的敬畏之心。诚然,今天大多数的社会学教师,都在辛辛苦苦地带着学生们做繁忙的调查研究,城市研究也差不多成了一门显学。可是我不知道,今天还有多少老师,会这样将教学本身当作主业来做,倾心地去指导学生做与教师自己的科研项目全然无关、也不以研究报告、学术论文为写作意图的社会调查?“得天下英才而教之”,是孟子所谓“君子三乐”之一乐,似乎也是郑也夫教授用以自勉的信条。可是知识人疏于此道久矣。
可以想象,践行这样的教学方式以及教学生涯,教师会受到来自于大学制度的业绩要求的压力,同时还会受到来自于学界的有关“学术意义”的质疑。据郑也夫教授介绍,这些年他确实也一直被来自于他人和他自己的这类疑问所追赶。就像在本文开头提及的那次伯克利会议上,虽然他诚恳明志在先,后头依然还是被学者们一再地有问及:“这些东西的意义是什么?”“它们与新闻记者的东西有什么差别?”
学术规训理应是大学教学(特别是所谓“研究型教学”)的任务,包括让学生跟着导师做有“学术的价值”和“现实的意义”的研究,让学生学写规范的学术论文。结合这样的任务,更为了应付压得教师们喘不过气来的课题、论文任务,兵来将挡、水来土淹,今天我们的大学已经建设、装备起了各种教学科研的高效能流水作业线。在这些流水线上,大量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们,顶替他们的导师,已赫然成了可以熟练制作各种“学术产品”的一线生产者。
身处这样的时代,笔者有时不免会悲观地想象,多少年之后,由今天聪敏的学者们靠着时髦概念组装起来的各种学术论著,在后人眼里,多半是会不知所云的吧。倒是这些记录了芸芸众生的生活细节的学生调查文集,或许会成为后人窥视今日社会、与今人对话的宝贵文献,也未可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