宾夕法尼亚州印第安纳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长江学者、该书主编之一的王希认为,留美历史学者群体是一个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他们成长的年代既是一个“革命时代”,也是一个“纯真时代”。收入书中的文章“凝聚着一群在特殊历史时段和空间中走到一起的中国历史学人的磨难和思考,它们记载着一代人的理想、信念、奋斗与成长”。
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联合举办的新书发布会暨中美历史学者恳谈会上,哈佛大学历史系主任、历史系美国研究讲席教授莉斯贝特・柯恩(Lizabeth A.Cohen),纽约大学校座人文讲席教授、历史系教授托马斯・本德(Thomas Bender),纽约大学历史系教授赫利克・查普曼(Herrick E.Chapman),北大历史学系教授牛大勇、李剑鸣、朱孝远,以及《在美国发现历史》的部分作者――芝加哥大学东亚艺术史讲席教授巫鸿、康奈尔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兼、爱荷华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刘晓原、圣地亚哥大学历史系教授孙绮、美国罗文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晴佳、澳门大学历史系教授魏楚雄、主编王希教授等人,就美国和欧洲史学现状、中美史学研究生培养机制和过程及其利弊发表了不同意见,同时也讨论了21世纪史学研究和教学面临的挑战。
本报记者现场采访了该书主编及几位作者,相信他们对自己的学术历程,中美史学界现状及其他一些问题的解读和剖析,会带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双重身份对学术思维的影响
读书报:在异国求学、工作的人,对于美国而言是“他者”的身份,而对于本国来说,身份也与出国之前不一样。请问几位是如何定位、看待这种双重身份的?
巫鸿:我想从学术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作为历史学家,总有一个个人主观的存在,我们说的都不是客观真理,而是有特定的背景和经验。这些特定的文化经验,在我来说,就变成了一种学术的方法论。这种特殊的经验是不是会产生一种独特的观点来看新的事情,比如中国的学者以他们的观点来看美国史,他们的角度可能是美国学者忽略的,但这些很难绝对地说就是中国学术或是美国学术。我觉得这种“双重”、“混杂”已成为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的经验,甚至不出国,也会变成“混杂性”的个人主体性。由此发展出一种史学观念,这样看到的就不单是中国问题或是美国问题,而是全球的问题。这种“混杂性”让我们看到更多有意思的事情,对我来说,就是在教学和写作中,转化为一种方法论和叙事性,让它更有建设性,而不是被动地将自己分成两半。
陈兼:“自我定位”是一个不知不觉中不断被提出的问题。我想起1999年世界杯女子足球,中国队和美国队决赛的点球大战中,美国队把中国队的一个球给扑出来了,我当时极为愤怒。我的美国同事说:“你是谁啊?这是我们美国队打败中国队,你那么悲伤干什么?”前两天我看加纳队和美国队比赛,加纳队打败了美国队,我也非常沮丧。你说,韩国队、日本队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可我就是希望韩国队赢。这是一种讲不清的情绪。那么在课堂里面,这就是一个大问题。在美国教学的时候经常碰到“we”这个词的使用问题,讲到“美国”时,你是用“we”,还是用“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我发现自己不知不觉中更多地用“we”,但是到中国来要怎么用?这些事情从理性的角度来讲,很难讲清楚。但在实践中却不断出现。
朱孝远:“identity”的问题很难解决。但我觉得这也有好的一面。中国人有个习惯,就是将差异变成对立,要么是东方,要么是西方,要么是好人,要么是坏人。其实真正优秀的东西超越时间、地域和题材的限制,是国际性的。身份问题也是同一个道理。
读书报:“插队知青”、“工农兵大学生”、“留美研究生”、“美国大学教授”,从您身上的这些标签可以看出那一代人的人生履历。而您早年在内蒙插队的经历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后来做“边疆研究”的学术选择。中国文化和西方学术环境对您有什么样的影响?
刘晓原:我们这一代对中国传统文化最为隔膜,或者说是在对传统文化扭曲的批判中长大的。因此,中国文化的影响主要是指出国以前在国内的经历在我们身上和思想深处留下的不可磨灭的文化刻痕。这是一种不大说得清楚的东西,也许只能说我们这些人不管在国外呆多久,从骨子里说还是中国人。反映在学术研究中,就是我们的学术关注还是一种中国人的眼光,问题意识还是一种中国人的出发点。中国学术有自己的优秀传统。我的“工农兵大学生”经历虽然是另类的“教育”,但当时有位老师的一句话――“太史公曰:孤证不立”――使我终身受益。但是20世纪以来,中国的学术环境变成了政治环境的附庸,学者的独立思想空间窄而又窄。在国外除了接受严谨的治学训练外,还有一片属于学者的天地,在这个天地里学术思考可以不受任何外在权威和压力的左右。
重新进入中国,感觉更困难
读书报:您去年回国任教,对国内学术环境有什么具体的感受?
王希:我回来虽然只有一年半,但感受和经历已经可以写一本书了。刚才巫鸿教授讲到我们这批人出去的过程比较漫长,经历了求学和工作的过程。求学和工作是两种不同的经历,我想这是我们这批人非常特殊的地方。求学时,你是来自中国的学生;但当你成为学者或教员时,就不再是这种认知了。你的思维方式、知识结构、行为举止等很多方面,已经跳出了一个中国人的框架,这就带来了一个所谓的双重意识(doubleconsciousness)问题。在美国你觉得自己是中国人,在中国别人又把你看成是美国人,两边都不讨好。尤其我们回来后,有时说话不注意,带有英文字,有人就会很反感,说你是“假洋鬼子”,其实这可能是一种不经意的习惯。这都是一些小事情。更重要的是,你生命的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像巫鸿和叶维丽――都是在另外一个学术环境中度过的,即便处处小心翼翼,你还是无法让人理解你。回来以后,我个人的感受是重新进入中国的过程,比当初去美国更艰难。
所谓“重新进入”,是指我们曾经离开中国,在国外长期求学和生活,现在回到国内工作,重新进入国内的学术、政治和社会体制。去美国的时候,我们比较年轻、单纯,敢闯,尽管有中美文化差异带来的“文化震荡”,但适应起来并不困难。另外,美国社会也比较开放、宽容,比较注重和承认个人的努力,机会比较多。所以,熟悉之后,“进入”比较容易。重新进入和融入已经离开了20多年的国内社会,自然会遇到一些现实的困难,但更多的困难来自个人的心灵体验。中国在过去二三十年里发生了巨变,我们自以为回到一个熟悉的社会,但很多时候却发现现实的中国远不是我们记忆中的中国,有时甚至感到很陌生,一些在国外生活时被有意或无意忘却的记忆被重新唤起。想象的中国与现实的中国发生强烈的冲撞和错位。还有一点,我们在另外一种学术体制下拼搏多年,突然面对国内的学术体制,并且要做出某些妥协,但又不甘心违背自己的原则,自然感到十分困难,所以“更为艰苦”。
读书报:巫鸿教授在文章中提到,张光直先生在哈佛退休时,面临取消“中国考古”专业的问题,其中提到了相关领导的影响。目前,中国高校里行政对学术的干预已造成一种负面的压制因素。您能不能讲一讲美国的经验?
巫鸿:我对国内学界的情况不太了解。美国各个大学的情况也不太一样。比如本书中有一篇文章谈到芝加哥大学“教授治校”的问题,由教授组成“参议院”来参与管理。还有很多学校是由校长、教务长来主持的,教授参与很少。现在我们也感觉到校方的控制越来越严,教授的力量越来越小。很多学校要解决的问题是教授的声音怎么进入校方的决策层。张先生那件事情比较复杂,和这个问题还有一些不同。
魏楚雄:原来我在美国一所大学教书,可能其他大学也都有相似的体制,校长、副校长等行政人员都要由一个独立的公司――跟学校没有任何关系――根据教员的意见每年做考评。这个做法的效果非常好,就是由教员来监督校长或副校长,做出的考评将会决定你的聘任合同和对你的评估。
我们现在怎样研究历史
读书报:您说在中国做历史,具有非常宽广的前景。国内史学领域的学者和学子听了这句话,应该很受鼓舞。
陈兼:从道理上来说,我觉得在中国做历史的前景真的应该是非常宽广的。中国人太喜欢、也太重视历史了。世界有哪个国家或文明像中国那样,历朝历代都将“修史”当作头等大事来对待(所以才有二十四史)?而实际上,读史以及“以史为鉴”也成了一种构成中华民族“特质”的基本要素。在今天的“后革命时代”,如何面对并消化中国“革命时代”巨大的正、负面的历史遗产,是一个带有根本性质的挑战。问题在于,现在你一眼望去,外面的历史书实在是太多了,但大多是抄来抄去,很少有原创性之作。那么,“搞历史的人”到哪里去了?又该怎么办?很多年前,孔华润(WarrenCohen)曾对我讲过一句话,很有启发:“写一部好的历史,就是讲一个好的故事,同时把故事的意义讲出来。”若真能做到这一点,在中国做历史应该有很好的前景。读书报:全球化时代成长起来的学生,在兴趣、思维方式和对历史的认知都与过去数代人极为不同,史学教育中出现“代沟”现象。此外,电子化资源的出现和信息传播的即时化,也对传统的史学教学方式提出了挑战。您是怎么看待这些问题的?
姚平:史学教育中的“代沟”和传统的史学教学方式所面临的挑战是一个普遍现象,中国有,美国也有。美国的历史教师经常在网上论坛中讨论这些问题,特别是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Online(H-Net.com)。也可能是因为上网发表意见者一般对电子化资源和信息革命持热衷态度,他们的结论往往是比较积极的。我相信电子化资源的出现和信息传播的即时化对传统的史学教学方式起到了很好的辅助作用。我教的所有历史课都使用网络教学管理系统,它不仅能使我与学生们保持密切联系,而且还能使我给学生提供更多的(传统的史学教学所无法提供的)历史知识和资料。这些功能减少了实际讲课时间,使我有时间组织学生讨论、促使他们去思考深层次的问题,如对历史的认知的变迁。读书报:您的研究领域是史学史,这让您能够更多地从“局内人”的角度来审视史学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您指出中国学者在美国做历史面临很多“陷阱”,可否就此谈谈?
王晴佳:中美史学的发展轨迹不同,文化传承更是异样。我们这一代人,受到了两方面的教育,而因为终极学位来自美国,往往不经意地就会以美国方式为准,其实这是需要自我警惕的。一个国家的学术发展,还是要以自身的传统为定位,进而吸收外来的影响。如果一味采取“拿来主义”,结果恐怕不会很理想。出版这本书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为了与中国学界交流,而不是想提供一个“样板”。我(们)深知自己知识的有限和不足。
读书报:书名叫做《在美国发现历史》,与保罗・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有异曲同工之妙,是否受到了后者的启发呢?
王希:2008年夏末我们完成项目构思的初稿时,拟定了几个书名,《在美国发现历史》列在首位。是否受到启发,我想应该有吧,因为柯文的著作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名字也起得好。但我们的“发现历史”与柯文书追求的主题不尽一致。我们的“发现”更多是构建一种对中国、美国、世界和我们自身的认知,强调的是“探索”的过程。我们所“发现”的既包括“历史”本身,也包括“做历史”的过程和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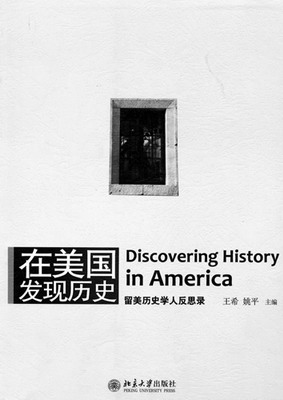
《在美国发现历史――留美历史学人反思录》,王希、姚平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6月第一版,58.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