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52年10月,耶稣会传教士圣方济各・沙勿略到达中国。虽然他并未能真正进入中国进行传教活动,但他仍然为后来大规模的传教士来华拉开了序幕。在此之后,一批又一批的传教士陆续到达中国,将“上帝的福音”传播到这个神秘的东方世界。
传教士来华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现象。在我们过去的研究当中,
近些年,对传教士的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学者们开始认识到,虽然在近代中国屈辱命运的形成过程中,部分传教士的确在不同程度上扮演了不太光彩的角色。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近现代时期又是东西文化交流的重要阶段,西方文明大量传入中国,中国人开始了解西方、学习西方;而西方人也在通过自己的感受去了解这个在他们看来古老而神秘的东方民族。在这样一种东西文明相互了解、相互交流的过程中,作为到达东方的先行者,传教士这一群体在很多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主体的迁变:从德国传教士到留德学人群》(叶隽著,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年8月,以下简称《迁变》)一书,正是从这样的视角来分析近代传教士在华活动的一个范例。而且,该书的着眼点还不止于此,作者将分析的对象进一步拓展到德国学术4文化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以及相关学科的建立和发展,指出,在这一过程中,文化传播和学科构建的主体,存在着一个从德国传教士到中国留德学人的转换。
读罢全书,收获甚多。该书在研究对象(德国传教士与留德学人群)、研究角度(大学4学术制度)、空间场域(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德文学科)等的选择上,都有着独到之处。作者在全球背景中对德国学术4文化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和学科规制的建立进行考察,在中德学术界间自由转换,全书逻辑严密,语言颇具韵味,令人读来兴味盎然。
而最令笔者感到颇有启发的,还是本书的主题,即文化传播过程中这种主体的转换。
利玛窦的传教经历
明清以降,西方工业文明开始由传教士带入中国,但并未引起中国主流知识分子的重视;至近代,中国国门被迫打开之后,对西方的了解和学习、中西文化的交流和交融,才真正进入一个高潮。在近代早期,文化交流的重任主要仍然由西方传教士们来担当,因为这一群体无论是从规模人数上,还是从与中国的接触程度上(包括时间、范围、深度等等),都较其他西方在华群体而言更有优势。而随着中国自身的警醒、尤其是大量留学生的出现,中国对西方文化的被动接受变成了主动学习和创造,留学海外的学人们,逐渐担负起了融合东西文化的重任。
出现这种主体的转换并非偶然。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并没有特别深刻地感受到来自西方的冲击和威胁,对中国的传统学者们而言,也就没有主动学习西方的推动力。而到了鸦片战争之后,在当时的历史大背景之下,西方文明的强势迫使中国的学者们“开眼看天下”,对自己的文化传统进行前所未有的反思,并最终将西方文明确定为自己的方向。在民族存亡危机的强大刺激下,“经世致用观念之复活,炎炎不可抑”。不再“万马齐喑”的学者们开始主动求知识于西方,以挽救民族之命运。正是这种主体意识的觉醒,使得中国学人们后来能够从西方传教士的手里接过东西文化交流和交融的接力棒。
除此之外,我们还不应忽视的一点,就是西方传教士前期所做的准备工作,也就是他们在传教过程中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以及在中国传播西方文明的各种努力。
众所周知,利玛窦是最早来华的传教士之一。当他从澳门进入肇庆开始传教活动的时候,他并不是直接向中国人生硬灌输自己的教义,而是采取了种种方式来接近中国人,使自己首先从感情上得到认可:“他穿上了和尚的法衣,称教堂为寺庙;为了能吸引人们到教堂,在接待室里陈列了从澳门带来的当时西方所制造的时钟、时晷、浑天仪等物;又在墙上悬挂了一幅为汉文标明地方的世界舆图。利玛窦最初为了迎合中国士大夫的自大心理,他故意地‘把地图上的第一条子午线的投影的位置转移,把中国放在正中……’”而随着他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利玛窦又发现,“在他与中国官方和文人交往的过程中,身披和尚袈裟反而诸多不便。于是从一五九四年起,他改穿儒服,戴上儒冠,并自称是儒者”。
不仅在外表上进行改变,利玛窦更进一步追求精神上与中国人的接近。1595年,利玛窦的《天学实义》(后更名为《天主实义》)一书刊印出版,在书中,利玛窦大量引用儒家经典文献诗、书、礼、易的内容,用以证明基督教与儒家思想其实是同一的。
至于利玛窦对西方科学技术的介绍,更是勿庸多言。
利玛窦的这一套方法,被后来的一些在华传教士们沿用。这一部分传教士们不仅食汉肴、着汉服,从外表上与中国人接近;更重视学汉语、读汉典,从思维方式和精神生活上与中国人接近;在此基础之上,他们还设立医院、开办学校,将西方文明中从技术层面到精神核心的内容都逐渐介绍到中国。通过这些方式,他们得到身边普通中国人的接受,得以融入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最终达到宣传其宗教教义、扩大其宗教影响的目的。而他们出于传教需要所进行的这些活动,恰恰打开了西学东渐的大门。
从花之安、卫礼贤到蔡元培、冯至
而《迁变》前半部分所重点分析的花之安与卫礼贤二人,更是这一部分传教士当中特别突出的两位。也许是德国人严谨踏实的行为风格所使然,也许是由于当时的德国在华优势远远不如英法等国、因此需要从其他方面多下功夫所使然,花之安与卫礼贤二人,对中国文化传统已经不再是简单停留在了解层面上,而是开始进入到更深的研究层次上了。而他们的成功之处、或者说优势所在,正在于他们深入到了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当中,深入到了普通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正如《迁变》作者所说:“与纯粹的专业学者……相比,传教士显然不具备丰厚的学养;可如果就对中国本土的深入认知而言,大学者们之优游书斋,当然也不可能与传教士在中国乡土里的‘摸爬滚打’相提并论。”(第24页)实际上,费孝通先生早就指出:“文化的深处时常并不是在典章制度之中,而是在人们洒扫应对的日常起居之间。”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再把花之安和卫礼贤这样的人看作单纯的传教士,而都承认其作为汉学家的历史地位。
由于有了这样一部分传教士或主观或客观所进行的文化相互了解和交流的前期工作,就为后来中国主体性因素―――留学生的出现和崛起做了铺垫与准备。
第一是从人员上。叶书中多次提到一个颇具意味的场景:1923年,卫礼贤受聘于北京大学之时,其顶头上司、德国文学系主任杨丙辰,正是当年在自己创办的礼贤书院中学习的学生。虽说这让我们不由得感叹机缘之巧合,但也正如作者所指出的,杨丙辰留学德国,未尝不是受到早年间卫礼贤的影响。而如果再将我们的视线稍稍扩展,有中国第一位留学生之称、日后促成了近代历史上著名的官派幼童赴美留学之事的容闳先生,其幼年的启蒙教育就是在德国传教士郭士立的英籍夫人所开办的学校以及后来的马礼逊学堂中完成的。也正是这一时期的学习经历,为容闳后来赴美留学、并带领更多中国少年留学海外的人生奠定了基础。
第二是从知识上。从16世纪中后期开始,至20世纪初,西方传教士已经在中国活动了300余年。在此期间,除了上帝的旨意之外,传教士还为中国带来了大量西方工业文明的各种知识。这其中既有技术之用,也有观念之体,虽然也许缺乏系统性和深入性,并且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但仍然在客观上为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们了解西方世界提供了一个有效途径。正是有了这些知识准备,留学生群体在承担起西学东渐主体的重任之后,才得以在此基础之上进行新的文化创造。
叶隽先生敏锐地把握到了近代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传教士―――留学生”这一文化传播主体的转换,并具体地从德国学术4文化资源对中国现代学术规制生成的作用力度这一视角,为我们梳理出了一条“花之安4安治泰―――卫礼贤―――蔡元培―――傅斯年―――冯至”的线索,从而揭示出,这种“主体的迁变”,是近代以来,西学得以真正被纳入到中国文化重建进程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文化外交”当如何进行
对“主体的迁变”这一命题的提炼,其意义并不仅仅在于本书尾章中所指出的,在于学术规制生成的核心内容、“留德学术群”的研究、“学术互动史”的提出。从更现实的角度来说,“主体的迁变”,为我们今天的文化外交工作开辟了一个新的思路。
尽管“文化外交”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在冷战时期,远远晚于传教士来华这一历史现象。文化外交的定义是,“由一国政府所从事的、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的对外文化交流行为被称之为‘文化外交’(CulturalDiplomacy)”。因此,从广义上来说,近代传教士群体所进行的这种有着国家支持、服务于政府对外扩张政策、并且在客观上促成了西方文化向外传播的传教活动,完全可以被看作是一场文化外交。实际上,卫礼贤本人就指出:“从早期传教士到各个国家就表现出两面性:一种是宗教性,一种是文化性。”
在以文化外交这一新的理论视角来解读传教士来华的时候,就会看到,这一历史过程、尤其是其所引发的“主体的迁变”,对于我们今天开展文化外交,颇具借鉴意义。
首先,是对文化外交接受国本土文化的态度。卫礼贤对于效果不同的传教活动进行总结的时候就谈到:“如果一个眼界狭窄的人来到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就对几千年的文化传统进行挑战,指责它的丑恶,即使他胸怀世界上最美好的动机,仍不会得到上层开明人士的支持”。文化传播者必须对接受国的本土文化持有尊敬之心,在东西方文明冲突激烈的近现代是如此,在全球化口号不断被唱响的今天,更是需要如此。与政治、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强的趋势所不同的是,全球化进展越向深广发展,各文化传统就越是会产生出一种要保留自己特色的强烈要求。文化的共性与特性都在发展,在此背景下进行文化外交绝非易事。相互的尊敬与了解,必须成为文化外交的基本前提。
其次,是文化传播的手段。文化外交的形式有很多,但究竟怎样才能取得效果?在这一问题上,传教士们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如前所述,以花之安、卫礼贤为代表的一部分传教士,在其传教过程中,并不是生硬地直接向中国人宣讲教义,而是将从感情上接近传教对象作为基本路径,在外表上、语言上、甚至生活习惯上、思想方式上与中国普通老百姓靠拢,先赢得他们的好感,再进行宗教的宣传。“1866年,当第一批中国大陆布道团传教士从上海动身去内陆城市的时候,男人们穿上了长衫,剃掉了额发,梳起了大辫子,女人们则盘起了发髻,穿上了宽松的旗袍。”更有甚者,南方浸礼教会的夏洛特・迪格斯・穆恩说“她按照当地人的习惯吃饭、睡觉和穿衣,但她‘不喜欢中餐,也喝不惯茶叶,然而参与社交是赢得人心的一种方式’”。改变装束、改变生活饮食习惯,这些都只是一种表象,其中所包含的实质性内容,是对对方国家文化传统的了解和学习。这种了解和学习本身,其实也正是树立自身形象、取得对方信任的一个过程。
再次,是文化外交的目标。有学者提出,文化外交的核心目标是“劝服”,即“激起他人接受或放弃某种观点,从而采取符合劝服者的意愿、有利于劝服者的利益(或许有利于、但不是绝对有利于被劝服者自身)的行动”。“通过劝服,往往会引起心理和感情上的向往,理性上的认同,从而一国的价值观被另一国的民众所接受。”如果将这种“劝服”更具体化、或者说更理想化一些,其实,文化外交所追求的理想目标,正是《迁变》一书的主题―――“主体的迁变”。即,通过各种手段,使文化外交的受众能够从被动地接受异己文化,转变为主动地学习异己文化,甚至主动将异己文化运用到本国文化新的建构和发展当中去。当达成这种“主体的迁变”之后,文化外交的双方国家之间自然也就很容易形成认同,最终达到改善双方关系的目的。
今天,各国政府在进行对外交往的过程中,越来越重视软实力所发挥的作用,文化外交的地位也就日益凸显。从这一点来说,“主体的迁变”这一命题的提出,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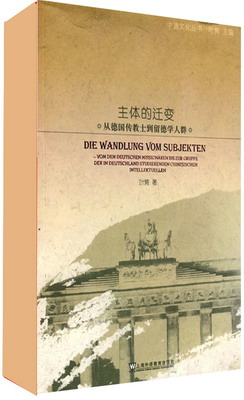
《主体的迁变:从德国传教士到留德学人群》,叶隽著,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年8月第一版,23.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