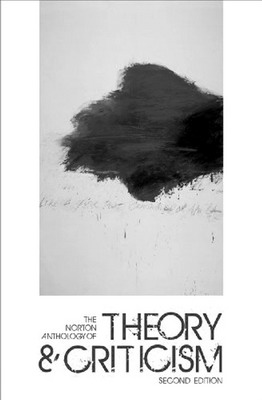
《诺顿理论与批评选》书影
一、超越后现代重新厘定大国文化形象
李泽厚:你多年前研究后现代主义,记得十几年以前你送给我你的《后现
王岳川:后现代、后殖民主义中的确有些东西值得人类思考。但是在艺术上,后现代大抵丧失了新锐的价值思考,而剩下些脏乱差的视觉暴力的东西,一些违背人性甚至反人性的东西。可以说是二战导致艺术家产生文化对抗性和虚无感,他们的理论是:社会生活如此肮脏、血腥,所以艺术不再是美学而应该是丑学。北京有一个“798艺术区”,不知道先生去过没有,很多人看过以后做噩梦,里面的恶心的东西确实很糟糕,完全仿造西方一战、二战的颓废艺术、虚无艺术和美国的流行艺术、波普艺术。现在,我们在北京大学提出“守正创新”的观念,反对一些人守邪追新、守歪超新、守怪求新,我们提出守正创新的“正”是正宗、正脉、正统,然后是“正大气象”!当今世界,日常生活的审美消解化已经弥漫周遭,消费主义全面扩散遍布地球。我举个例子,央视的节目是否保留主要参考收视率,但是收视率分布很不科学。一些文化层次较低的人会喜欢比较俗的节目,而大部分的白领、金领、知识分子却没有收视率的点击权,他们丧失了文化话语权。结果节目就越来越低俗,越来越没有正大气象。如果各电视台还是用西方那一套以点击率、收视率为准的消费主义模式,其结果将是中国文化在电视上劣胜优汰,大国形象荡然无存!出版图书也是这样子,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使一些人丧失学术良知和基本判断力。
李泽厚:看来文化犬儒主义和文化自卑主义弊病容易旧病复发啊。但是我呆在美国,美国是后现代主义的大本营,所以我有时候也关心一下这方面的东西。我注意到,美国后现代主义反权威、反中心、反价值、反文化的倾向这些年有所收敛,一些艺术家开始提出“回归古典”、“回归精神”、“回归价值”。但是,看来国内一些人反倒有些拾人牙慧地继续推进后现代主义的那些东西。他们最好出来看看,才知道什么是一个民族文化中最重要的,肯定不是舶来品!
王岳川:对此,我提出“正大气象”的新世纪美学原则。我觉得今天“汉唐气象”已经没有了,“孔颜气象”也正在失效,还剩下一点卑微不堪的晚清破败气象。中国学者扎堆去研究晚清,我认为问题很多。书法也是这样,现在晚清、民国的书法拍到天价,有两个原因:一是这些作品还在,二是后代流传有序,唐朝的已经拿不出来了,所以晚清作品就被炒作成天价,结果附带把晚清败国之象的东西变成了新世纪中国的正面形象。同样,电视上播清宫剧太多!真正对西学非常了解同时对国学经典非常精通的人并不多见,而且他们正在丧失其思想者地位和在文化软实力中的重要性。
李泽厚:国内真正有点国学功底的人不太多,应该更潜心地研究真学问,最终对人类有价值的还是真正的学问。
王岳川:你写了《中国古代思想史》,可以看出你对中国古代思想史下了功夫,同时对中国现代性问题也作了思想探索。目前中国的大学不重视古代经典和文化思想源头,中学课文里古代诗文越收越少,一些名篇都被淘汰掉了,当代连周杰伦的歌词都入选了课本。这种文化断根、文化虚无的做法后患无穷。中国经典难入课堂、中国书法不入教室的文化短视现象,实在值得学术界、教育界人士关注。
李泽厚:我感觉最近几年不少家长送孩子读古文,尤其是学前的孩子。
王岳川:国内办了一些私塾班,要送孩子去背“四书五经”,“四书”还可以记诵,“五经”很难背的,谁能把《春秋》背下来?
李泽厚:我认为现在背“五经”没必要,唐诗宋词可以背一下。我们这一代都是课堂教育,背那些古文,不难的。新一代处在信息社会中,《唐诗三百首》背熟就够了,《易经》不用背。
王岳川:我认为仅仅背诵古代经典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在全球化时期将中国思想、中国精神整合成当代对人类有启迪意义的思想。我在做一项工作,将中国先秦到清末的经典著作100本、20世纪学术大家的著作100本、新时期以后反映中国文化生态的著作100本组织中外英文专家翻译成英文。这样可以将中国思想文化整体介绍给西方读者。我们也可以将你的著作精编一本20万字的书译成英文,请你授权翻译出版。尽管先生认为西方了解中国要100年,我这样想,酒好也怕巷子深,人家可能不感兴趣,但是我们要主动输出。
李泽厚:刚才给你看的那本英文版厚书(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诺顿理论与批评选》第二版)收入了我的一篇文章,是西方专家编选的全球美学家的代表论文,收入了我的文章(《美学四讲》),出乎我意料。编选者是美国很有名的学者,编选出版世界范围内的重要选本。说明中国美学家已经进入世界美学的视野。
王岳川:这是值得高兴的事情。但是一本选本还不够,还需要我们主动地输出。我总在想,西方视角下对中国的观察不能代替13亿中国人的思想,5000年的中国文明更不能被忽视。全球文化的美国化将是人类文化的退败。好在随着中国的崛起,一元中心和二元对立的时代正在终结,我们可以期盼未来超越文明的冲突,进入文明的共存和互惠。
二、汉字文化在新世纪的重要价值
王岳川:我注意到,你十几年前曾总结出中国发展的四个问题: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你不认为经济能直接决定政治、文化,市场经济也并不必然地带来现代民主。但现代民主却以经济为前提,否则便不稳固。反之,如果没有现代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一切恐怕都难以保障和持久。
李泽厚:是的,我认为,在经济发展之后必须注重个人自由,在社会正义基础上有必要提出政治民主。中国崛起最终不仅仅是要在经济上崛起,而更重要的是要在文化上崛起,这才是真正的崛起。
王岳川:西方文明受东方文明影响很大。从历史上看,西方文明既不是一种连续性文明,又不是独立成熟的文明形态,而是深深地受到东方文明影响的文明形态。西方现在不可能忽略中国文化的存在,这是因为在世界失衡与人类动荡中,东方文化有助于文化精神动态平衡,人类求和谐发展的需求使得中国文化必然走向前台。
李泽厚:西方文化从源头上与东方文化密不可分。就文字而言,中国文字不是语言的书写,跟西方不同。因为我没研究语言学,我没法评论,我只是提一些看法而已。中国文字和西方不一样,中国是文字统治着语言,西方则是文字跟着语言变,是语言中心主义的,所以现在西方人都不懂11世纪英语。
王岳川:所以五四时期钱玄同们要废除汉字是多么危险的事情。从中国20世纪不断修订汉字、简化汉字和汉字拉丁化倾向中,可以看出历史上错误的引导。钱玄同等人在1916年左右提出的“废除汉字说”其实是从日本人那里抄来的。我们知道,公元645年,日本的“大化革新”可以说是“全盘中化”,就像明治维新“全盘欧化”一样。经历了一千多年之后,日本终于明智地终结了“废除汉字说”和全盘拉丁化的鼓噪,确定了两千多汉字作为日文常用汉字。作为汉学载体的汉字,对于日本近代文化的发展以及对整个“汉字文化圈”的发展意义重大。
李泽厚:很可笑,汉字是废除不了的,汉文化是去不了的。但在繁简体字问题上我主张简体字。书法可以写繁体。
王岳川:中国废除汉字问题同样很严重。中国文化和艺术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是“东亚汉字文化圈”国家的重要文化地基。在日本废除汉字后,1945年美国要求朝鲜半岛废除汉字,当时韩国以写中文为高雅,结果韩国和朝鲜废除了汉字,连书法都用韩语的拼音。之后新加坡、越南、中国台湾的汉字使用也受到影响。曾经中国台湾的中小学课本中古代诗、词、文比重占70%,后来变为60%。中国台湾的学者说,他们发现内地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学课本当中的古诗、词和文仅占全部内容的30%。这值得我们深思。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太过“现代”了,现代文学、现代美术、现代音乐等,却忽略了传统经典的传承续接和守正创新。汉字在一次次的简化过程中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
李泽厚:这的确是值得整个民族文化界思考的大问题。
王岳川:那些“去中国化”的冷战思维应该终止,那些“废除汉字”的想法已经没有市场。中国汉文字极为丰富,《中国汉字大辞典》收录中国汉字9万多个。
李泽厚:汉英辞典上5万多都用不了,所以中国不简单。中国文字很广大,所以我认为秦始皇很大的功劳就是这个。
王岳川:秦始皇的五大贡献已经丧失了四项:“车同轨”,早已过时;“度量衡”,已经失效;“修长城”,而长城内外是家乡;“吞并六国”,而六国早就不复存在。但是“书同文”仍有中国文化传承意义和国家统一意义。
李泽厚:造字以后慢慢和语言接轨,这个东西要好好研究,而且我认为语言是要表达情感的,一些以前没有、后来才有的,比如感叹词什么的,这些东西怎么样和文字结合起来?甲骨文之前的符号到战国文字,时间漫长。如前所说,中国是文字统治着语言,而不是语言统治着文字,不是口头语言的文字书写,字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可是现在这个题目没有人去做。而且关键问题是文字怎样和语言结合起来。
王岳川:中国文字使得各民族具有文化认同感和文化亲和性。中国文字是仍有生命力的“东方魔块”。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需要重新认识自己在世界文化中的位置,不仅意识到中国文字的长久生命力和汉字文化圈的文化辐射力,而且意识到中国不应该满足于人类物质生产加工厂的地位,也不应该基于若干个人财富积累走一条非可持续发展道路,更不是要谋取利益的最大化而导致价值沦丧。中国应发扬东方伦理文化精神,通过个体的文化修为,促使民族文化逐渐走向自觉、自信、从容、高迈,不再渴望中国文字拉丁化或中国文化走向“西化”。
李泽厚:我认为学者们应该花大力气将中国传统精神讲透彻,传承文化精神才是硬道理。但对中国传统不应继承“形”,而应该继承“神”。我不参加国内的国学、儒学活动的原因,就是那大抵是一些“形”的东西,不外乎就是一些仪式性的东西,还包括一些空论道之类的东西,所以国内学人“文化宣言”什么的,我明确表示不赞同的。我注重将仍有强大生命力的中国文化精神传承下去,同时不排斥吸取外来文化的营养。
王岳川:我们已经触及到中国文化深层结构问题,你刚才讲“形”、“神”的问题很有意思。我认为,中国儒家文化在政治制度方面丧失了鲜活的生命力:第一,儒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已经失效,不管是作为治国方略,还是“内圣外王”,都随着西方现代性的进入而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第二,儒家思想必须在反躬与个体心性修为中,放弃意识形态的诉求。其实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应该扪心自问是否还有“学术者,天下之公器”的气概?心中是否还有“天下”?手中还有没有“公器”?第三,儒家思想尤其是中庸思想遭遇西方“竞争哲学”和“丛林法则”的挑战,坚持宽厚中道的儒学在充满竞争的现代社会中遭遇到了危机。直面当代儒学三重困境,不难看到,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学将会慢慢地淡出历史,而作为第二层面的个体心性修为的儒学和第三层面的重视反身而诚、精神生态平衡的儒学,可能具有更宽更大的国际意义和东方文化复兴的意义。
李泽厚:你的看法很有道理,点出了问题的实质。其实从礼乐文化开始,以儒家为主,儒、道、骚、禅相辅的华夏哲学、美学、文艺以及伦理政治,都建立在“心理主义”的基础上。“心理主义”的核心不是理智认识,不是道德伦理,不是上帝神灵,而是情感本体,是“情理交融的人性心理”。这一点很重要,情理交融的人性心理才是儒学仍有新生命的地方。以儒家精神为主体的中国文化在新世纪怎样发展,的确值得好好研究。
三、美学观照下的中国书法文化精神解读
王岳川:你作为美学大家,对艺术有什么样的实践和爱好?
李泽厚:我对青铜器、绘画很感兴趣,尤其是诗词方面算是强项吧。我认为搞美学的总是要对某一门艺术有比较深的造诣,才可以做得比较深。
王岳川:我注意到你家里墙上有很多你拍的照片,是不是你对摄影艺术很感兴趣?
李泽厚:我喜欢拍照片,但并不专业,我每到一个国家就会拍很多照片。我横跨欧亚大陆,走了很多地方,我最欣赏的是柬埔寨,吴哥文化很有魅力,值得学界重视,中国很少去注意、关注,这方面的内容很重要。
王岳川:我看见你的墙壁上有几幅书法,你喜欢书法吗?你作为美学家对书法怎么看?你研究华夏美学,对青铜器等谈得比较多,但对书法好像谈得比较少。
李泽厚:我喜欢中国书法,但是对书法研究不深,更谈不上书法实践。但是我特别喜欢书法那种自由状态,那种飘逸超迈的境界,还有书写内容对中国文化的深刻表达。但我只是喜欢,没有深究。人应该有自知之明,我没有研究的不敢乱下定论。
王岳川:其实你在谈论宗白华先生的时候,就已经触及到了中国书法。宗白华先生的中国立场使得他更多地关注中国文化、中国艺术乃至中国书法。
李泽厚:是的。我坚持认为中国美学“四大主干(儒、道、骚、禅)”说。我对中国美学的特点曾概括为四个方面,即“乐为中心”、“线的艺术”、“情理交融”、“天人合一”。而“乐为中心”后来发展为我的“乐感文化”;而“线的艺术”主要指的是表情的艺术,就是以音乐、舞蹈、书法为代表的艺术。而书法作为“线的艺术”最能表达中国情绪。
王岳川:我记得你曾在《美的历程》中说:汉字是象形文字,是“净化了的线条美―――比彩陶纹饰的抽象几何纹还要更为自由和更为多样的线的曲直运动和空间构造,表现出和表达出种种形体姿态、情感意兴和气势力量,终于形成中国特有的线的艺术:书法”。
李泽厚:是这样,书法是表达情感的形态,无论是草书还是行书,而楷书的形式感更强一些。我曾说过:唐代绝句(入乐)、草书(线条)、音乐、舞蹈这种“音乐性的美”,将中国传统重旋律、重感情的“线的艺术”,推上又一个崭新的阶段,也真正成为“盛唐之音”。
王岳川:在我看来,古代书法能够反映时代之音,而当代书法对时代而言已经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形态,同样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在其他艺术全盘西化的症候中,东方书法不应成为西方二流艺术的模仿,也不能认可西方中心主义的艺术风尚成为人类唯一的审美方式的做法,而是要重视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重新组合之后而生成的一种新书法。
李泽厚:书法在古代有重要的人文价值和审美价值,但我担心的是在这个“电脑时代”似乎书法的实用功能减少了。
王岳川:但是书法的艺术功能和文化功能却增强了。只不过国内书法界比较混乱,需要加以厘定。就美学意义而言需要厘定书法症候的是:书法唯技术主义、书法唯美术主义、书法唯精英主义、书法唯视觉主义、书法唯本能主义、书法媚外主义、书法消费主义、书法拜金主义、书法部落主义、书法市场主义。
李泽厚:书法问题这么复杂,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加以认真清理。宽泛地说,我仍很重视美学与伦理学跨界研究,我认为人的情感不同于动物的情感,而是一种文化伦理情感。中国文化既不是理论也不是单纯的实践,中国美学既不是名词概念的堆积,也不是艺术经验的汇合。中国美学讲的是陶情冶性,它有一个塑造生命意识的过程。所以中国讲究心斋、养气、道器、虚实等等。其实我讲人的自然化,在这一结构中间培养着“情”。当今世界有很乱的东西,也有可持续下来的东西,我们需要的是耐心。
王岳川:的确如此,全球化时代,当西方人用西方的思想统率了全球,要全球同质化变成一体时,东方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东方应该清理自己的精神遗产,让这个世界不仅有西方的法律精神,还要有东方的德教精神。人类的未来不是由西方说了算,而是应该由东方加入自己的文化声音,将单维之声变为多元之声。人类才能互相倾听,互为体用。

李泽厚先生游历世界各地时拍摄的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