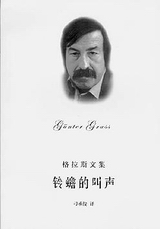 爱情与死亡被奉为文艺创作的两个母题。可是,一名鳏夫与一位寡妇之间产生爱情的开端,会不会缺乏青春勃然气息缺乏新鲜感?他与她最终又在一起车祸中双双罹难的结尾,能不能诱惑人们想像力的悠长
爱情与死亡被奉为文艺创作的两个母题。可是,一名鳏夫与一位寡妇之间产生爱情的开端,会不会缺乏青春勃然气息缺乏新鲜感?他与她最终又在一起车祸中双双罹难的结尾,能不能诱惑人们想像力的悠长
无从得知小说《铃蟾的叫声》写作初始,作者是否考虑过这些问题。然而,《铃蟾的叫声》作为书名,却营造有几分神秘的象征意义,在德语中“铃蟾”这种蛤蟆,与“悲观者”同义。悲沧,有几分凄然的色调就这样从头到脚染遍了小说。
小说开头两位未亡人之间爱慕之情的产生,还不能算色彩黯淡。那是在离教堂钟楼不远处的市场一角,在这浪漫又世俗的邂逅后面,布景有大丽花、菊花和紫菀的多重色彩,有牛肝菌的鲜肥和香菜的气味……他与她在花贩的切花桶里挑拣着,他与她不约而同都钟爱铁锈红色的紫菀。付钱时,髭须灰白、身着粗花呢上装和灯芯绒裤子的鳏夫掏出德国马克;散发浓郁香水气息、有金红色靓丽头发的寡妇,花的却是波兰钞票兹罗提。小说发生地和人物身份逐渐显露,这份爱情诞生地是波兰海港城市格但斯克―――二战前这座城是德国西普鲁士省首府但泽。是战争改变了它的国籍归属,战争也酿成了波兰、德国民众间的复杂心态。
《铃蟾的叫声》的主题,就如此影影绰绰地从远景推成特写,仿佛是电影镜头一般,先显景色,又见人物,再凸出人物与景色的关连,呼唤出这些人与物的涵义。这部小说从两个人物的当前生活状态延伸出去,沿着他与她感情生活的重组路径,德国人和波兰人以及东欧各国人们在20世纪90年代“柏林墙”倒塌后,德国统一那个时期东欧政治风云的变幻。对于鳏夫和寡妇而言,他们的邂逅、相悦,谈情说爱,是个人命运的推演;对于欧洲这片土地,以格但斯克为代表而言,他与她的爱情只是小说叙述情节中一个开头,在这个序幕后,涌动着以人们为代词的思绪和行动,那是起伏不定的无数人命运的流动、变迁。
《铃蟾的叫声》作者是德国著名作家君特・格拉斯,尽管他写完这部作品七年后才得到诺贝尔文学奖,但是从《铁皮鼓》开始他选择但泽、也就是格但斯克作为小说开展的地点,这份执着仿佛从未动摇过。在《铃蟾的叫声》里,他打出爱情的幌子,用一个看似平淡无奇、似乎有几份玫瑰色温情的开端,引出有沉郁气息的文学思索。他执笔似刀,切割战争啃啮后东欧各民族历史积淀的结节,剖析腠理,毫不心慈手软。他没有放弃德国文学传统的思辨,只是未采用枯涩的学斋研究程式。至于《铃蟾的叫声》的小说主人公,及其周围人物形象是否生动,个性是否鲜明,在他看来毋须过多纠缠。他只是固执,有几份急切地用人物遭际,构建故事,诠释这段历史,以至自个突兀闯进故事的情节中,扮演鳏夫亚历山大教授的中学同学角色。当亚历山大教授不在场或不方便叙述时,这个中学同学就出场来个越俎代庖。
鳏夫德国美术史家亚历山大・雷施克教授和寡妇波兰工艺技师亚历山德拉・皮亚特科夫斯卡,手持铁锈红色的紫菀,来到公墓,悼念自己的已故亲人。这是万灵节的时光。公墓成了他与她对话的旁证,也诱发了两人相互间的好感,或者说爱情的萌芽就是在公墓的沉重氛围里得到了滋润?!
正是公墓,引发了他们共同合作、经商的思考―――建立一家德国―波兰公墓公司,使众多被战火相逼,离开故土的人们,能叶落归根、魂归故里。尽管他与她的这份奇思妙想,有强烈的可操作性。而且又符合战后德国与波兰等民族之间的和解愿望,但是小说结尾却安排了雷施克与皮亚特科夫斯卡愤然辞去了公司里的职务,在一次车祸中一同罹难的结果,而且他与她是长眠在异国的土地,真是有强烈讽刺意义的结尾。
如果用有宗教色彩的词语表达,雷施克和皮亚特科夫斯卡的相爱、结合、这段暮年的爱情,可以视作对民族和解愿望的“祭献”,他俩的辞职报告是在五月铃蟾的叫声里完成和递交的。小说如此描写,与其说是作者的冷酷,毋宁说是格拉斯的冷峻,他看到了当今世界在嚣闹的市声后潜伏着危机―――伴随个人良好愿望,滋生的却是个人无法驾驭的局面。因为历史过于沉重?还是人们欲望过于强烈?小说没有也无法给出答案。
《铃蟾的叫声》[德]君特・格拉斯著刁承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