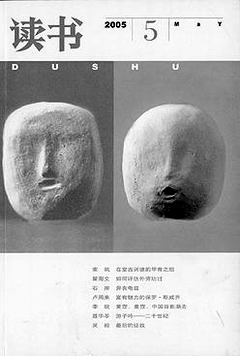

说到当代的读书类期刊,首先要谈的当然是《读书》,尽管近年来它受欢迎的程度已大不如前。“读书”这个名称,表面看来没有什么特色,哪个地方
 其次是上海的《书城》,用一个“城”字来命名一份读书杂志,可能只有上海人才想得出来,一百年来所形成的那种国际大都市的抽象理念与感性气质,是这个命名的深层文化心理根据。“城”与“乡”相对,它的主要内涵就是不土气,就是洋派,这个主题在《书城》杂志的内容中表现得十分彻底。比如,它的很多栏目都是由当代最先锋、前卫的诗人、艺术家、影视评论家来主持,主旨则是要开创一种新鲜、刺激、时尚化的、与西方直接接轨的当代读书风尚。一般人看到《书城》,第一反应往往是“这办给谁看呢
”事实的确如此,如果在一般的城市,这些东西根本没有读者。然而在上海情况就不同了,不仅是《书城》,各种时尚杂志都有可观而稳定的发行量。它既与上海出版人和读书人的审美价值取向相关,同时也与上海那种“得现代都市文化风气之先”的百年传统相吻合。在上海即使是上了年纪的出版人,在出版理念上也都很开放,比如上世纪80年代策划了《文艺探索书系》的高国平先生,就坦言希望出的书一定要有点“新奇”,甚至是“怪怪的”。上海这个城市文化性格当然也有问题,由于从一开始就追逐于、附属于西方都市文化的生产模式,所以很少能产生属于自己的原创性话语,形象与思想,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追新”有余而“沉潜”不足,末流则由“好奇”而沦落为“肤浅”,这在《书城》杂志中也有鲜明的表现。
其次是上海的《书城》,用一个“城”字来命名一份读书杂志,可能只有上海人才想得出来,一百年来所形成的那种国际大都市的抽象理念与感性气质,是这个命名的深层文化心理根据。“城”与“乡”相对,它的主要内涵就是不土气,就是洋派,这个主题在《书城》杂志的内容中表现得十分彻底。比如,它的很多栏目都是由当代最先锋、前卫的诗人、艺术家、影视评论家来主持,主旨则是要开创一种新鲜、刺激、时尚化的、与西方直接接轨的当代读书风尚。一般人看到《书城》,第一反应往往是“这办给谁看呢
”事实的确如此,如果在一般的城市,这些东西根本没有读者。然而在上海情况就不同了,不仅是《书城》,各种时尚杂志都有可观而稳定的发行量。它既与上海出版人和读书人的审美价值取向相关,同时也与上海那种“得现代都市文化风气之先”的百年传统相吻合。在上海即使是上了年纪的出版人,在出版理念上也都很开放,比如上世纪80年代策划了《文艺探索书系》的高国平先生,就坦言希望出的书一定要有点“新奇”,甚至是“怪怪的”。上海这个城市文化性格当然也有问题,由于从一开始就追逐于、附属于西方都市文化的生产模式,所以很少能产生属于自己的原创性话语,形象与思想,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追新”有余而“沉潜”不足,末流则由“好奇”而沦落为“肤浅”,这在《书城》杂志中也有鲜明的表现。
可与《书城》作比较的是长沙的《书屋》,这个名字很容易使人想到一间斗室,尽管不够气派,没有大都市花里胡哨的霓虹异彩,但正如钱锺书先生所说,真正的学问在荒江野屋、二三素心人那里,这里却有一份难得的镇定、从容与自信。这与长沙近两三百年来所承接的湖湘文化传统有关,它的深层是一种“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强悍文化心境,即使不能做“中心”,也不愿意沦为随波逐流的“跟班”。《书屋》里的文章,明显有这种湖湘文化的气质。
 再次是南京的《古典文学知识》。这个杂志办得时间不算短,它的名字也最堪玩味。一说到“知识”二字,就知道它没有独立的价值立场与深远的文化理想,再加上“文学”两个字,就显得更加雕虫小技,而把政治、经济等重要话题弃之不顾,再加上排在最前面的“古典”二字,就完全像是一位私塾先生的事业了。它的言外之意是“不愿意接触现实”,只希望在一个小小的安乐窝中自娱自乐地打发时光。这种文化性格的形成与南京的城市发展史直接相关。从建城那一天开始,南京就是一个国家兵工厂,历史上著名的吴王夫差与越王勾践,都曾在这里制造过青铜兵器。同时它也是遭受兵戈蹂躏最多、历史记忆最为悲惨的城市。久而久之,在总是充满大喜大悲的南京文化中,就孕育出一种节奏缓慢、温柔富贵、“躲避崇高”、沉迷于日常生活的诗性情调。这是《古典文学知识》小心翼翼,从一开始就希望回避现实或不对重大问题说三道四的根源。另一方面,这也是因为他们对生活所求不多,只要守住“古典文化”这一块就可以“俯仰自得”了。与之可以一比的是一些地望偏僻的报刊,一般说来,在南京文运昌盛的时代,它们很可能尚处于蒙昧状态。但它们好的一面是没有历史负担与文化创造的条条框框,因而在新一代文化人心中激发的是一种从边缘走向中心,从穷乡僻壤走向广阔世界舞台的顽强意向。
再次是南京的《古典文学知识》。这个杂志办得时间不算短,它的名字也最堪玩味。一说到“知识”二字,就知道它没有独立的价值立场与深远的文化理想,再加上“文学”两个字,就显得更加雕虫小技,而把政治、经济等重要话题弃之不顾,再加上排在最前面的“古典”二字,就完全像是一位私塾先生的事业了。它的言外之意是“不愿意接触现实”,只希望在一个小小的安乐窝中自娱自乐地打发时光。这种文化性格的形成与南京的城市发展史直接相关。从建城那一天开始,南京就是一个国家兵工厂,历史上著名的吴王夫差与越王勾践,都曾在这里制造过青铜兵器。同时它也是遭受兵戈蹂躏最多、历史记忆最为悲惨的城市。久而久之,在总是充满大喜大悲的南京文化中,就孕育出一种节奏缓慢、温柔富贵、“躲避崇高”、沉迷于日常生活的诗性情调。这是《古典文学知识》小心翼翼,从一开始就希望回避现实或不对重大问题说三道四的根源。另一方面,这也是因为他们对生活所求不多,只要守住“古典文化”这一块就可以“俯仰自得”了。与之可以一比的是一些地望偏僻的报刊,一般说来,在南京文运昌盛的时代,它们很可能尚处于蒙昧状态。但它们好的一面是没有历史负担与文化创造的条条框框,因而在新一代文化人心中激发的是一种从边缘走向中心,从穷乡僻壤走向广阔世界舞台的顽强意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