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狗年春节一过,1926年生人的方汉奇就到了“杖朝之年”了。这个年纪的老人,本应该在家里享受含饴弄孙之乐,但他仍然“退”而不“休”,不仅保持着每天工作14小时以上的习惯,还在《清史》纂修工程中承担了编修《
狗年春节一过,1926年生人的方汉奇就到了“杖朝之年”了。这个年纪的老人,本应该在家里享受含饴弄孙之乐,但他仍然“退”而不“休”,不仅保持着每天工作14小时以上的习惯,还在《清史》纂修工程中承担了编修《
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新闻史学会名誉会长,方汉奇常常被人们称为新闻史学界的“泰斗”,他却说,如果将中国新闻史比作一条浩瀚的长河,我只不过是一个在这条长河之中溯流探源、艰辛跋涉的旅人。
“记者梦没做成,最后搞上了新闻史,坐了一辈子的‘冷板凳’”
1926年12月,方汉奇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他的外曾祖父林启和外公林松坚都是学贯中西的学者,母亲曾是鲁迅的学生。幼时所受的良好教育和适逢乱世的外界环境,使得方汉奇十分关心时局。上高中时,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一个学者的书房里发现了十几种报纸,那锋利的文笔和充溢的爱国激情对他触动很大,“邹韬奋、范长江、彭子冈、浦熙修、萧乾这些名记者,都是我十分敬佩的。”从此,他开始如饥似渴地搜集当时出版的各类报刊和名记者的报道,并对记者这一职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46年,方汉奇在上海考大学,“我报了5个大学,全是有新闻系的,三个志愿也清一色填报新闻系。宁可考不上,也不考虑别的专业。”但是,由于数理化成绩不好,总分太低,几所名牌大学都落选了,最后,方汉奇考上了校址设在南京、苏州两地的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
夙愿既偿,他全身心投入了大学四年的专业学习中。学习之余,他继续收集报纸,上大二时,他还把苦心搜集的1500余种报纸拿出来办了个报纸展览。伴随着集报活动的开展,方汉奇在报史研究方面的才华也逐渐展露,引起了系主任马荫良先生的注意。
1950年,方汉奇大学毕业,已调任上海新闻图书馆馆长的马荫良慧眼识珠,邀请方汉奇到该馆担任研究馆员,负责《申报》史的整理工作。方汉奇感于师恩,应邀而往,从此他就一头扎进了《申报》的故纸堆,从1872年的创刊号一直看到《申报》停刊,一干就是三年。“我那时住在图书馆,白天晚上都与这些旧报为伴。新闻是历史的记录,通过这些报纸我好像把清末民初的社会历史经历了一遍,心里非常有底,对我后来从事中国新闻史的教学、研究,一辈子受用。”
“真没想到,我的记者梦没做成,最后搞上了新闻史,坐了一辈子的‘冷板凳’。”老先生感慨地笑了。
| 2006年2月26日 第9期总第9期 责任编辑邓凯 电话:010-67078807/8979 传真:010-67078118 邮箱:[email protected] |
 |
1953年8月,应北大中文系副主任罗列之邀,方汉奇来到未名湖畔,在北大中文系主讲新闻史。当时的新闻史研究在我国还是一片尚待开垦的领地,全国从事新闻史教学的只有复旦大学的曹亨闻先生和方汉奇两人。“那个时候连一本通用教材都没有,涉及到现当代部分的内容更是一片空白。往往是下个礼拜要讲的课,这个礼拜还没有备出来,没米下锅啊,要找米!没办法啊,只好到图书馆、档案馆去查,连暑假也不闲着。就这么紧张。”方汉奇一边讲课,一边扎进图书馆、资料室,从浩如烟海的故纸堆里精心选择资料,为新闻史的研究奠定了一块块基石。寒暑易节,燕园中风光无限,但一心治学的他连午休时间都抽不出来,哪里有心思野游骋怀。由于长期伏案工作,他上衣两肘总被磨得由光而破,由破到烂,他倒好,干脆准备了无数套袖备用。
“经过三五年这样的积累后,讲课算是上正轨了,可是政治运动又开始了。”1958年,方汉奇随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并入人大新闻系。1960年在反右倾、反现代修正主义的政治思潮中,人大新闻系也开展了“学术批判”运动,方汉奇因坚持近代无产阶级报纸与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报纸存在历史渊源的观点,被视为阶级立场问题,成了批判对象之一。
十年浩劫中,方汉奇又被打成“牛鬼蛇神”,挂牌游街、大小批斗会,然后当小工、打扫厕所。没有条件进行学术研究,他就埋头做着史料的收集整理工作。他白天当黑帮,挨批斗,晚上回来还猫在冰冷的小屋里坚持读书。别的书不让看,就啃《资治通鉴》,照样做卡片,甚至连《小学生字典》都反复研读,“平日里有些恍恍惚惚的字认不准,字典帮了我这个忙。”
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方汉奇不仅丝毫没有想过放弃,反而自得其乐地沉浸在自己的精神家园里。他说:“我不怕坐冷板凳。范文澜常说的‘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字空’;董仲舒曾经做到的‘三年不窥园’,都是新闻史研究工作者应该有的思想准备。一个人甘于坐冷板凳,不争名于朝,不争利于市,才能安下心来做学问。不怕慢,就怕站。这些年来,应该说,我没闲着。”
“《进奏院状》是世界上现存的最早报纸”
1976年,随着“文革”的结束,已届知天命之年的方汉奇重新焕发出学术的青春,他以昂扬的姿态投入到紧张的教学研究中。1983年1月,他发表论文《从大不列颠图书馆藏唐归义军进奏院状看中国古代的报纸》,振聋发聩地提出:“中国报纸始于唐代”;“《进奏院状》是现存的中国最早的报纸和现存的世界上最早的报纸。”
“《进奏院状》是北大历史系向达教授上世纪30年代在英国求学时,在当时的伦敦不列颠博物馆首先发现的,它是斯坦因从我国窃走的7000件敦煌文卷中的一件。后来,他在《唐代文化与西域文明》一书中提到了《进奏院状》,但是没有展开。”
凭着深厚的专业素养,方汉奇敏锐地意识到,这份罕见的古代报纸实物将对我国古代报纸起源研究产生极为重大的意义。“我的一个学生孙文芳在新华社当记者,在伦敦常驻,我就委托他替我到不列颠图书馆查《进奏院状》,他誊录后还替我给原件照了相,现在新闻史课本里用的《进奏院状》的照片,就是他当年拍的。”
得到这份“进奏院状”的誊录件后,方汉奇不避繁难,开始了逐字逐行的疏证、辨析。“进奏院和邸是个什么关系?进奏官和邸吏又是什么关系?为什么说朝报、邸钞、阁钞、杂报、状报、除目、京报等是古人对封建官报的异称?”
就这样,他一个一个问题地深入探讨,一路溯源而上地苦苦追寻,条分缕析,层层剥笋,终于使缠绕着《进奏院状》的一个个疑窦渐次消弥。经过严密的考证,方汉奇推出了自己的结论:现藏不列颠图书馆的这份《进奏院状》,是一份唐僖宗光启三年的官方报纸,同时也是现存的中国和世界上最早的报纸,并由此证明了唐代是中国开始有新闻事业的朝代。
这一论断不仅澄清了中国报纸究竟起源于何时这样一个命题,而且订正了戈公振率先提出的汉朝起源说。否定别人也许不难,否定权威则太不容易。关于这一点,方汉奇有自己的原则,他说:“做学问要有胡适‘于不疑处有疑’的独立思考精神,更要有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从事新闻史的教学与研究,对新闻史中的人物也好,报刊也好,事件也好,在叙述和评价时,都应该力争作到实事求是。作到一切都有根据,作到‘言必有徵,无徵不信’。”
“戈公振是高峰,我只是历史长河中起传承作用的一个小链条”
从1927年戈公振出版《中国报学史》算起,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工作至今已开展70余年了,而推动新闻史学发展,使之成为当代公认的重要学科,离不开方汉奇的努力。人们爱戴这位学长,不仅因为他有着一以贯之的敬业精神,严谨踏实的治学作风,更有着谦虚平和的高尚修养,奖掖后进的人格魅力。
“我有一句座右铭‘人之彦圣,若己有之’,就是说别人学术上有了成就,就如同自己拥有一样,对年轻人要多扶持,对同辈人要多借鉴,不要得红眼病,不要嫉妒人家,应该有这样的襟怀。我希望年轻人能超过自己,超过自己的学生才是好学生。”
方汉奇曾三次登门劝说现任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所长的尹韵公读博士。1985年,还在攻读新闻学硕士的尹韵公只身沿着1935年范长江撰写《中国的西北角》时走过的路线进行考察,采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纠正了在新闻史学界长期形成的认为范长江的这次采访是为红军北上抗日做准备的错误说法,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尹韵公在历史学方面的才华引起了方汉奇的注意,在他即将毕业的时候,方汉奇三次前往其宿舍鼓励他继续深造。忆及这段往事,方汉奇说:“当时愿意念新闻学博士的人,有这方面追求的人,还不多。我觉得他脑子比较活跃,思想敏锐,能发现问题,具备做学问的这一条件,所以我就三番五次动员他继续读下去。果然他后来很有创见。”
正是基于方汉奇的薪火相传,半个世纪以来,方汉奇的学生中新闻名家辈出,其中不仅有范敬宜、郭超人、陈锡添等新中国新闻事业的杰出代表,更有一大批走上教学岗位的优秀新闻教育工作者,他们已成为共和国新闻事业的脊梁。方汉奇也已经成为我国资历最深、教龄最长的新闻史教学研究工作者。为了表彰方汉奇对新闻教育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1996年方汉奇被授予我国新闻教育界的最高荣誉――韬奋园丁奖一等奖。
人们赞扬他和戈公振先生是中国新闻史领域的“两座高峰”,他却不这么认为:“戈公振是高峰,我只是个小丘陵。他是奠基人,我只是做了一点后续的工作。一个学科需要有历史的传承,我只是历史长河中起传承作用的一个小链条。”
“新闻工作者要永远保持对新事物的新鲜感和好奇心”
和大多数学者古色古香的书房有些不同,方汉奇的书桌上竟然摆着两台电脑,一部台式机,还有一部笔记本。别小看这两台机器,它们可是方汉奇工作的好帮手。
说起当年学电脑的经历,方汉奇有些掩饰不住的兴奋,他很可能是人大70岁以上的老教授里最早使用计算机和互联网的一个。“我是1996年开始用电脑,刚开始是让学生把最简单的操作程序写在本子上,我自己用‘一指禅’照着练习。1998年我开始上网了,上网以后,才知道网上的世界很精彩,所以一上去就下不来了。”
谈起互联网的妙处,方汉奇兴奋不已,他说自己每天都要浏览人民、新华、新浪等网站,也少不了光顾一下Google和百度。“我到网上去看新闻,主要是希望扩大一些信息量,捕捉媒体上没有报道的或者漏报的一些信息。网络是全天候的,可以24小时沟通,还可以互动,这些优点都是平面媒体没有的。”
如今,方汉奇先生仍然保持着旺盛的激情和活力,每天日程安排得满满的,连大年初一也不肯休息。他说:“教师是个需要不断学习、不断提高的职业。现在我就觉得时间不够,书看不过来,报纸看不过来,杂志看不过来。我每天早上6点多起床,除了看与研究课题相关的书籍和历史文献资料之外,还要看近十种报纸杂志,同时还要听广播、看电视、上网、收发手机短信和彩信。”
“什么?您还会发彩信?”这可又让我吃了一惊。
“对呀。新闻工作者总是在和陌生的事物打交道,因此要不断学习,要永远保持对新事物的新鲜感和好奇心。”
■人物小传
 |
|
丁聪所作的方汉奇素描 |
方汉奇,1926年12月生于北京,祖籍广东普宁。1950年毕业于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后并入苏州大学)新闻系。1950年至1953年任上海新闻图书馆研究组馆员,同时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新闻系讲授新闻史专题。1953年调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任教,1958年调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任教。1972年至1978年再度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任教。1978年起,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任教至今。
方汉奇在高校从事新闻史教学研究工作近55年。1979年被评为副教授,1983年被评为教授。1984年起与王中、甘惜分同时成为我国第一批新闻学博导。曾任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中国新闻学会常务理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现任中国人民大学荣誉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顾问兼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新闻史学会名誉会长,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16所大学的兼职教授。
方汉奇从事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工作半个多世纪,成果卓著。主要著作有《报刊史话》、《中国近代报刊史》、《报史与报人》、《新闻史上的奇情壮采》、《方汉奇文集》等,主编有《中国新闻事业简史》、《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三卷本)、《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三卷本)、《中国新闻传播史》、《大公报百年史》等。先后发表《从大不列颠图书馆藏唐归义军进奏院状看中国古代的报纸》等学术论文140余篇。曾两次获吴玉章奖新闻学一等奖,一次获高校文科优秀教材一等奖,两次获北京市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一次获北京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奖,1984年被评为全国一级优秀新闻工作者,1987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1987年、1997年两次被评为北京市优秀教师。1991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 成果解读
方汉奇1981年出版的《中国近代报刊史》被公认是自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之后“50年来第一部有影响的新闻史专著”。新闻史学界认为,戈公振以《中国报学史》开辟了我国新闻史整体性研究道路,方汉奇的《中国近代报刊史》则以其考证之精良、体例之完备、总结之全面、持证之客观,树立起了新闻史研究应当遵循的科学的方法与思路,是我国新闻史研究走向成熟、科学的标志。
方汉奇主编的三卷本《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在1996年问世,全书263万字,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涉及面最广的中国新闻通史著作,被誉为中国新闻史学成果的集大成者。除此之外,《报史与报人》、《中国新闻事业简史》、《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等都成为中国高校的经典教材。已发表的论文有《从不列颠图书馆藏唐归义军进奏院状看中国古代的报纸》、《中国近代传播思想的衍变》、《一代报人成舍我》、《章太炎与近代中国报业》、《中国新闻传播事业100年》等140余篇,其中部分结集出版《方汉奇文集》。
方汉奇的研究成果不仅填补了空白,更为新闻史研究的框架体系、方法内容作出了示范,是新闻史研究领域的一座高峰。他创立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的体系,成为目前中国高校该领域教育的标准。目前国内高校使用的新闻史教材,大多以方汉奇创立的体例为蓝本;他培养的学生正活跃在中国新闻史教学与研究的前沿。
■回声
方汉奇教授是我国当代历史新闻学的大家,也是中国新闻学术界的权威。业内人士普遍认为,由方汉奇、宁树藩、陈业邵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是继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之后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又一座高峰。
――中国新闻史学会
新闻史研究,在新闻传播领域的研究中相对来说难度更大,因为它需要更长时间的去坐冷板凳,去搜集大量的资料,要做大量梳理研究的工作。方先生几十年来如一日,克服了种种困难,取得了这样大的成就,不仅仅是从学科发展方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对新闻传播研究做出了杰出贡献,更有价值的是为年轻的一代,为学子、后来者树立了一个楷模和榜样。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方汉奇先生是我崇敬的老师。不论是在“左”的思潮横行的年代,或者是在今天社会有些过于物质化的情况下,他都始终如一地研究被别人看起来非常冷门的东西。挣不了大钱,也出不了大名,但是为了自己学术的目标,这样不懈地追求,这种精神特别值得崇敬。
――人民日报原总编辑范敬宜
■人物影集

与甘惜分在一起

七个兄弟姐妹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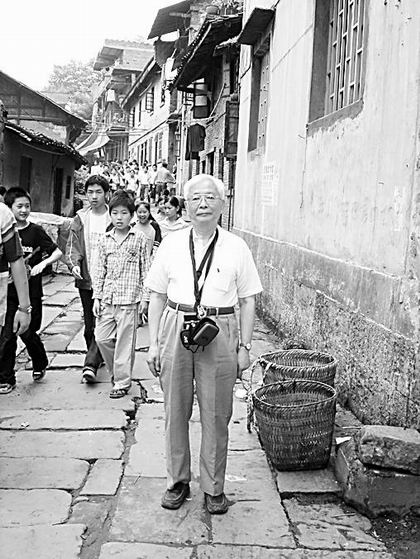
在重庆寻访

在人大宜园家中

与博士生研究论文写作
(本版照片均为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