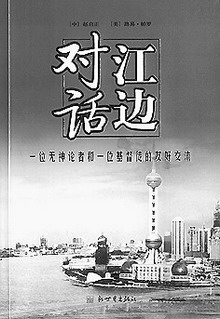 由新世界出版社新近推出的这本《江边对话:一位无神论者和一位基督徒的友好交流》,实际上是两位特殊身份的人物之间的三次对话记录。对话的主人翁一位是美国颇具影响力的宗教领袖路易・帕罗,另外一位则是时任中国
由新世界出版社新近推出的这本《江边对话:一位无神论者和一位基督徒的友好交流》,实际上是两位特殊身份的人物之间的三次对话记录。对话的主人翁一位是美国颇具影响力的宗教领袖路易・帕罗,另外一位则是时任中国但是,在认真读完这本对话录之后,我们会吃惊地发现赵先生最终却将这些敏感的问题、这些风险和挑战转化成了高度凝炼并富有哲理的知识,使读者不期然地意识到东方与西方、宗教信仰与非宗教的思想体系之间仍然存在许多相互补充并可以和谐共存的精神内涵,一般中国读者因之而可以获得对宗教更为多元性的理解,一般西方读者也因之而可以获得对中国更为深层和全面的了解。
关于宗教的基本性质和文化内涵,赵启正先生从对西方宗教的核心教典――《圣经》的分析和总括入手,精辟地阐明了基督教的四个基本旨趣:“一是上帝无时不在,无所不在,是全知的,是全善的,是全能的;二是人是有原罪的,所以不能和上帝沟通;三是上帝派耶稣来和人沟通;四是人不要企图主导自己,要靠耶稣和《圣经》来主导自己。”(第10页)同时他也认同宗教是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在解答人类普遍关心的宇宙生成论和人生价值论问题,承认基督教与希伯来、希腊和罗马传统文化存在密切的传承关系,其在这些民族甚至人类文明的语言、文学、历史、建筑、生活伦理方面都具有积极的意义,甚至还特别引述了已故的奥地利总统所讲的、发生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故事来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相互说明: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德国军人往往采用“一、二”随机报名的方式将报名“一”数的人处死,结果一位报名“一”数的人说,自己有七个孩子,不愿被枪毙,一位神父就站出来说:我没有孩子,让我来替换他吧。这种宗教性的献身精神与孟子的“舍生取义”的精神是一样高尚的伦理精神。以赵启正先生这样的教育背景和社会身份,能够这样理解宗教的普世伦理价值,是足可以让人击节叹赏的。而且,我还以为,赵先生在这里的分析涉及到了各种宗教作为一种民族文化传统形式长期存在的原因,即其具有普世的伦理性质,所以基督教的“爱你的邻人”,儒家的“德不孤,必有邻”都可以普世的伦理原则对待之,“邻”正好揭示出了“爱”这种“德”的伦理的普遍意义,所以西方人说“Loveme,love mydog”(爱屋及乌),中国宋儒说“观鸡雏可以观仁”,“绿满窗前草不除……欲常见造物生意”,讲的都是“邻”的伦理普遍意义。因此,赵先生也很自然地推论出基督教的伦理中有“你们愿意人怎样对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对待人”的“黄金律”,孔子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可以相互补充的规范性伦理。这样的领悟比起过去将基督教的教堂自诩为“上帝之城”,把孔夫子贬低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真是别开生面,因为现代西方人知道教堂更应当是“公民道德孵化器”(incu-batorofnationalmorality),现代中国人也更多地认同司马迁对孔子的评价:“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前些日子,北大一教授以孔子与某名演员有克磅之比而遭遇中国人普遍的反感,亦可证明中国人具有圣贤崇拜的宗教情怀,其伦理价值取向就是司马迁说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关于宗教所涉及的敏感的政治问题,赵先生并没有取巧而回避,反而是表现出了真诚的历史感和坦率的现实感。他结合中美两国的历史,指出在为国家的独立和人类的正义事业中,存在着普遍的伟大牺牲精神,这也包括二战期间牺牲在中国战场上的美国自愿者,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受到了宗教的公义精神所激励的。同样,他还就西方宗教界普遍关心的中国人权问题发表了坦率的看法:“我想,人权问题,世界各国都不完美,美国和中国也不例外。如果人类的人权都十分完美了,上帝就没有任务了,人类自己就不必努力了。”(第53页)我认为他在这里将“人权”与“上帝”联系起来,语气也多诙谐,但其中由不乏哲理的深意:照西方宗教和哲学的传统看,“上帝”和“人权”都可以归入柏拉图式的“自在性理念”,而现实中的经验事实都是不完美的,是对完美的理念的“拙劣模仿”(poorcopies),所以,实际上现实中的任何国家都存在不同程度或不同性质的“人权问题”。因此,就这些现实中不完善的人权问题加以确实地改进,要远比相互指责更具有建设性。还有,在赵先生的历史感和现实感中,我们也可以体会到他对宗教现状所具有的常识感(commonsense)――这一点几乎是公认的政府新闻主管理应具备的“基本素养”。他说:“当今世界有20亿基督教徒,有10多亿非宗教人士。从20世纪60年代起,有许多人提倡宗教间的对话,这非常重要,但不应该忽略宗教人士和非宗教人士的对话。有神论和无神论者之间互相理解,对于世界的和谐必有贡献。”(第66页)这些话表明,中国政府的意识形态虽然是“非宗教的”,但它对于宗教的理解和政策却并非是“反宗教的”,而是坚持“宗教自由的”与“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的”。
在讲过赵先生的“历史感”、“现实感”和“常识感”之后,我还觉得他的谈话充满了“幽默感”(senseo fhumor)。英国人常说:“幽默感是诙谐的思考加深情的体谅”(thinkinginfunwhilefeelinginearnest),这大概是并中国人的“雅人深致”和“名士风流”二美之全吧。立此标尺,我们可以对照以下这两段话:
赵:如果您不嫌重的话,我送您每人一套英文版《中国的宗教》。书很重,上帝让您受累,但不是惩罚,是给您快乐。(第57页)
……
赵:如您所说,如果真的有天堂,到了天堂,我们的样子不会变吗?还能认识吗?
帕:完全可以。如果我们在中国已彼此认识的话,到了天堂,我们会更聪敏,肯定能彼此认识。我一定会到天堂去找您的。
赵:我们要约定一个见面的密码吗?
帕:到那时,我可以给您我的名片。
赵:如果我们的模样变了,我说“密西西比”,您回答“扬子江”,就算对上了。
帕:好主意。
赵:这是我们共同想象的美丽的故事!(第110页)
阅读这样的谈话,我们很难说“充满幽默感”会是对赵先生的“溢美之词”吧?
当然,从赵先生谈话中我们也不难看出他的科学家品质以及中国式的无神论教育对他的影响。因此,他毫不隐讳地说,不能像科学实验那样被证实的人格神上帝是不能被接受的;“爱你的敌人”这样的宗教旨趣也是绝难为他所认同的。这倒是表现了赵先生“守身以诚”的个性和“爱憎分明”的原则性。依我看,赵先生对宗教实在论和对某些宗教伦理价值的怀疑,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不过,我们在理解这些道理的同时,仍然可以为宗教的实在论和伦理观保留一些灵性空间,即我们不仅仅是从经验科学和逻辑理性的立场看待这些命题,而是从人类的感情或直觉因素方面来体会这些宗教命题,看看它们在实证和理性之外还有没有表达人类情感的深意。这样,也许我们就更容易理解为什么在科学和理性如此发达的当代社会,仍然有那么多的人具有宗教情怀,甚至某些大科学家和大哲学家也不能例外。英国无神论的大科学家罗素曾经在“怎样避免愚见”(HowtoAvoidFoolishOpinions)中说,“如果有人对你说2+2=5或者冰岛在赤道上,除非你的算术知识或地理知识与他一样的浅薄,你才会与他愤怒争辩,否则你应该同情他。”这就是“同情无知”,它的立足点不是理性,而是人类普遍应该具备的情感,这情感倒是类似于基督教的“爱你的敌人”和《老子》“报怨以德”的思想,我看这也就是无神论者或者怀疑论者身上潜藏着的宗教情怀。以此个人浅见质诸赵先生,以为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