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发表86周年,也就是说,新红学已走过86年风雨路了。
新红学是20世纪红学史上影响最大、而命运又最多舛的一个红学流派。“新红学”这一称谓,出自顾颉刚《红楼梦辨・序》:“我希望大家看着这旧红学的打倒,新红学的成立,从此悟得一个研究学问的方法,知道从前人做学问,所谓方
新红学的方法是科学方法,这是它区别于索隐红学的最本质的特征。1910年代,陈独秀等高举“赛先生”大旗,大力提倡科学精神;而《科学》杂志以任鸿隽、杨杏佛、胡明复等为代表,也竭力宣传“科学方法万能”的观点,主张科学方法适用于一切研究。《红楼梦考证》是胡适在科学化运动大潮中,运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中国传统人文学术的一种尝试。胡适提出他的科学方法:
……撇开一切先人的成见;处处存一个搜求证据的目的;处处尊重证据,让证据做向导,引我到相当的结论上去。我的许多结论也许有错误的,――自从我第一次发表这篇《考证》以来,我已经改正了无数大错误了,――也许有将来发见新证据后即须改正的。
这种方法的哲学基础是“实验主义”(Pragmatism),它有两个主要特征:历史的观念,实验的态度。后来,胡适又将其表述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今人席泽宗院士曾详阐其科学性。
新红学之“新”,不仅“新”在其研究方法,更“新”在其研究内容。胡适将红学的考证内容限定在作者、版本、时代三个方面。他通过考证,将《红楼梦》的著作权还给曹雪芹,并搜辑到大量作者及其家世的材料,使后人对曹雪芹这位“奇人”有一个基本的了解。而对“续书”的研究、脂砚斋的研究以及“探佚”等,都是由作者研究衍生出来的。因为不相信后40回是曹雪芹写的,才有所谓“续书”说;要探究曹雪芹写的后40回是什么样子,才有所谓“探佚学”。至于胡适对作者生卒年的研究,则大体厘清了《红楼梦》创作的年代。1954年批判胡适的时候,胡适总被指责没有研究18世纪的阶级斗争;孰不知,“18世纪”这个时间,正是胡适考证出来的。在版本研究方面,胡适将其划分为脂本、程本两大系统,又命名并初步研究他生前出现的戚本、甲戌本、庚辰本等本子。大体上,胡适研红的前期,在作者方面贡献最多,后期,在版本方面贡献较多。
无论是研究方法,还是研究内容,都是迥异于索隐红学的划时代的贡献(有研究者说,“新红学的本质是实证与实录合一”,这并未切中要害)。也主要是这个原因,学术史家总把新红学视作现代学术的起点。这既是《红楼梦》的光荣,更是新红学的光荣。
新红学有一个争议极大的观点:“自传说”(最初的表述是“自叙”)。它是胡适根据曹雪芹的传记材料与红书所叙提出来的,是针对索隐家的“叙他”、“他传”提出来的,是实证范畴的具体问题。没有“他传说”,就不会有“自叙说”;如同没有索隐红学就没有“新红学”一样(新红学本脱胎于对索隐红学的批判与反动)。二者的研究方向根本相反:索隐的方向是“逆入”,新红学则是“顺流”。两派都用的是“考证法”。但新红学派侧重于考证作者、时代、版本,而索隐则侧重于考证小说情节;索隐从虚入手进行研究的,因此没有根据,只好靠猜谜,只好靠附会,而新红学则是从现有的材料入手,以事实为依据,处处尊重证据,相信证据,讲求无征不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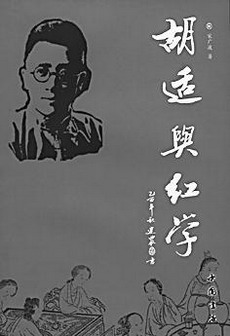 由此可知,索隐与新红学,简直是“水火不容”。晚年的胡适,甚至拒绝批评索隐派的论文,他说:“方法不同,训练不同,讨论是无益的。”但有的研究者却提出:《红楼梦考证》既是“新红学”的开端,也是“新索隐”的开山之祖,甚至把胡适与刘心武联系起来,说刘心武承袭了“新红学”积弊;又说,新红学“有反科学的一面”(而胡适却反反复复强调,要“创造科学方法的《红楼梦》研究”),这实在令人费解。其实,新红学与所谓新索隐,毫不搭界。最近,常产生这样的感想:研究红学史,须先从微观研究入手,只有先把每一个重要人物及其著作研究透彻了,才能做成一部权威的红学信史。拙作《胡适与红学》,就是本人对“胡适的《红楼梦》研究”所做的初步探讨。
由此可知,索隐与新红学,简直是“水火不容”。晚年的胡适,甚至拒绝批评索隐派的论文,他说:“方法不同,训练不同,讨论是无益的。”但有的研究者却提出:《红楼梦考证》既是“新红学”的开端,也是“新索隐”的开山之祖,甚至把胡适与刘心武联系起来,说刘心武承袭了“新红学”积弊;又说,新红学“有反科学的一面”(而胡适却反反复复强调,要“创造科学方法的《红楼梦》研究”),这实在令人费解。其实,新红学与所谓新索隐,毫不搭界。最近,常产生这样的感想:研究红学史,须先从微观研究入手,只有先把每一个重要人物及其著作研究透彻了,才能做成一部权威的红学信史。拙作《胡适与红学》,就是本人对“胡适的《红楼梦》研究”所做的初步探讨。
新红学因反对索隐派而产生,这早已是公认的事实。但将其放在更广阔的学术背景下加以考察,还有三大背景是为后人重视不够的,即新文学运动、国语运动和整理国故。如果将新红学的产生与胡适早在留学时期就倡导的白话文学运动和在新文化运动高潮中提出的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就会发现:由胡适来开创新红学,这是多么一件顺理成章的事――那简直是必然的。因此,有研究者根据胡适与汪孟邹的通信而提出《红楼梦考证》是“被逼出来的”说法,不能不说有点牵强。
无论是拥护新红学的人,还是反对它的人,几乎都不否认这样一个论断:作为新红学的开山鼻祖,胡适是20世纪红学史上影响最大的一个人。1961年,胡适说,40年来新红学的发展,只是作者、本子两个问题的新资料的增加而已。而今,80多年过去了,这话似乎还没有完全过时。就拿红学界名望最大的周汝昌、冯其庸二公来说,周老自然是公认的真正继承胡适的“集大成者”,无论新红学的优点还是缺失(如贾曹互证),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地继承下来了;冯公也是啊,冯先生在其整个红学研究中,以作者、版本研究分量最重、贡献最多,近年又多次强调要在作者、版本、文本三个方面多多用力――他们不都是在沿着胡适开创的路前行吗?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难道《红楼梦》研究就只能在作者、版本两个圈圈里打转转吗?所以这样说,并不是说这两个领域都研究明白了,不需要研究了;事实是,有好多具体问题仍待进一步深入探讨。我们的态度是:继承胡适、发展胡适、超越胡适。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开始有更多的人从更多的角度来从事红学研究,可惜迄今为止尚无突破性的成绩出来。再上溯到上世纪50年代,俞平伯先生曾试图超越新红学的种种罅漏和时代局限性,力图开辟《红楼梦》研究的新境界。其实,无论是胡适、还是俞平伯,都有勇于修正错误的勇气,这也是作为原创的“新红学”的一种品质。胡适对曹雪芹卒年的不断修订,俞平伯对“自传说”、对“《红楼梦》文学造诣不高”等观点的修订,都体现了这一点。
新红学的产生和辉煌,属于20世纪。80多年来,它伴着风雨,一路走来,经历了太多的艰辛和曲折。到了今天,在新的世纪,实在需要有一个像胡适开创新红学那样的人出来超越胡适了;虽然,这很难。
《胡适与红学》宋广波著中国书店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