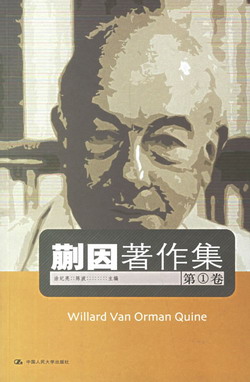 蒯因是当代美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家。谈到美国哲学,人们自然会想到实用主义。的确,实用主义是美国的本土哲学,正如儒家和道家是中国的本土哲学一样。但美国的实用主义并不是铁板一块、一成不变的。从实
蒯因是当代美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家。谈到美国哲学,人们自然会想到实用主义。的确,实用主义是美国的本土哲学,正如儒家和道家是中国的本土哲学一样。但美国的实用主义并不是铁板一块、一成不变的。从实
不过,我在这里主要不是谈蒯因在美国实用主义哲学中的地位,而是试图从蒯因的观点出发,谈谈语言和逻辑在哲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我主要讲三点:第一,蒯因把“语义上行”作为判断句子真值的重要前提,这既是延续了维也纳学派的思想传统,又是对哲学研究性质的一种重要规定;第二,正如几乎所有的分析哲学家一样,蒯因不是因为做了哲学家才去研究逻辑,相反,他是从逻辑研究中找到了哲学发展的突破口,逻辑研究是他形成哲学思想的主要根据;第三,蒯因对科学始终怀有一种崇敬的态度,无论是他早期的逻辑思想还是晚年的自然主义科学观,无不透露出他的科学主义倾向。虽然科学主义在当代哲学中已经遭到了很多的指责,但对我们来说,强调一切从科学的观念出发仍然是需要我们大力提倡的哲学研究思路,是我们的哲学研究中最为缺乏的思想进路。
“语义上行”的观念并不是蒯因的首创,但他的重要贡献是,把一切被看作是与事实有关的命题都放到语言分析的显微镜下,首先接受语义分析的考察。不了解分析哲学的读者可能会认为蒯因的这套做法有些“大题小作”,是在玩文字游戏。当然,事实上并非如此。只要是认真阅读了蒯因的著作,我们就会发现,蒯因的这套做法多少有些“煞费苦心”:他的目的其实不仅仅在于指出揭示句子意义的一种基本方法,在我看来,更为重要的是试图说明,一切我们通常认为的哲学问题其实都可以通过这样的“语义上行”的方法加以解决。这就是说,在蒯因看来,哲学研究的核心不应当是去解决世界的真实存在问题,而是考察我们对世界的存在本身所形成的语言系统。由于这样的语言系统与它们所描述的世界之间存在着重要的或本质上的差异,所以,我们对语言系统的考察并不意味着我们对世界的考察。哲学是对语言系统的研究,而不是直接简单地对世界的研究,这个观念不是蒯因的创造,而是来自维也纳学派,更主要地是来自早期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但蒯因从逻辑的观点出发,把语言分析作为哲学研究的核心内容,这就为哲学的语言转向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自蒯因哲学起,当哲学家开始讨论哲学问题的时候,都需要首先考察所要讨论的命题的意义,而不会像传统哲学家那样依然专注于对世界存在的思考。我把这种对语言转向的完成活动看作是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标志。虽然蒯因之后仍然有哲学家强调“语义下行”,但没有哪一个哲学家会否认“语义上行”的重要作用。
我始终认为,哲学与逻辑的关系以及逻辑在哲学研究中的作用,需要我们反复强调。因为哲学离开了逻辑就无法存在。无论我们如何理解逻辑的含义,有一点是我们共同承认的,即对思想的清晰表达总是以符合语言的逻辑要求为前提的。蒯因早在1940年的《数理逻辑》中对逻辑的作用就给出了清晰的说明:“它为处理话语最基本的成分提供了清晰的技术。它给科学带来了也许还包括在严格性和明晰性上的贡献――使科学的概念更加清晰。概念的明晰不仅可以用来揭示已有的科学假说、迄今尚未揭露的结论,也可以清除挡在科学进步道路上的细微错误。”(第1卷,第82页)。在1950年的《逻辑方法》中,蒯因甚至更加明确地表示,逻辑不仅规定了科学命题的意义,而且规定了作为科学大厦基础的整个数学的基本原则。他写道:“……在逻辑所达到的更高之处,人们会发现,通过一些自然的阶段,逻辑把我们引入到数学”,“逻辑理论的某些不突出的扩张使我们进入到一个领域……它的确有一种特殊的抽象实体作为主题。这些实体是类;类的逻辑理论,或集合论,被证明是纯数学的基本原则。从它可以产生出全部经典数学”(第2卷,第15页)。这些说法虽然体现的是蒯因一贯坚持的从逻辑推导出数学的逻辑主义纲领,但它们明确表明了逻辑在蒯因哲学中的核心地位,同时也表明了逻辑对哲学研究的关键作用。的确,对逻辑在哲学中的重要作用,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最后,我想简单谈一下蒯因的科学主义问题。“科学主义”这个词如今似乎被看作是一个贬义词,等同于所谓的“唯科学主义”的意思,甚至认为这种科学主义应当为人类目前所面临的环境问题、社会危机以及战争危险等承担责任。在当代哲学中,蒯因被看作是科学主义的典型代表。虽然我们可以从哲学上指出这种科学主义的弊端或缺陷,如“把自然科学特别是精确科学的精神、方法与手段推广应用于哲学认识论的研究,只承认能为这种方法所研究、所把握的东西,其他一切飘忽不定、不易捕捉的成分与要素统统加以拒斥”,但我们更应当看到,作为一名逻辑学家,蒯因的本意就是希望能够以严格精确的形式语言表达我们的思想,把我们对世界的经验概括上升为一种理论抽象。在蒯因看来,一切科学理论的基础都在于经验观察,包括了我们从外部世界得到的感官刺激,但科学本身却并不是这种刺激或感觉语言的总合,而是把我们的感觉加以系统化或理论化的结果。他明确地说,“把我们的过去经验与当下经验相连接并引发我们预期的记忆,本身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对感觉输入的记忆,而是对本质上的科学假设,也就是物理世界中的事物与事件的记忆。”(第6卷,第565页)这样看来,蒯因心目中的科学主义其实并不完全是一种极端的“实证主义”,更应当把它看作是一种以逻辑主义为特征的理性主义。例如,他自己就反对实证主义坚持对经验内容的最终检验,认为这恰恰“妨碍了科学的进步”。他甚至这样说:“确实,下述情况经常发生:一个与所有的检验点相距遥远的假说,提示了可以检验的其他假说。这必定是值得检验的假说的一个主要源泉。”(第6卷,第590页)可见,蒯因的科学主义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责难的所谓“唯科学主义”,他对科学的推崇和尊重恰好表明了他所从事的正是一项合乎理性的事业。从现实意义来说,蒯因提倡的科学主义精神也正是我们目前的哲学研究中需要大力提倡和发扬的内容。
《蒯因著作集》涂纪亮、陈波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