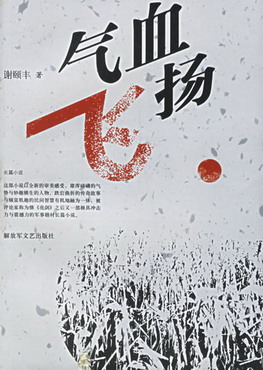 谢颐丰的长篇小说《气血飞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表现的是八路军监所的犯人们在一场关乎民族生存的战争中灵魂的涤荡与生命尊严的萌发的故事,在已有的众多抗日题材的作品中,无论题材的选择还是故
谢颐丰的长篇小说《气血飞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表现的是八路军监所的犯人们在一场关乎民族生存的战争中灵魂的涤荡与生命尊严的萌发的故事,在已有的众多抗日题材的作品中,无论题材的选择还是故
“犯人”,这两个字在很多人眼中,无疑是被烙上了罪恶和耻辱印记的,应该在狱所的管理下,悄无声息地改造自己的灵魂,以求早日出狱得到自由。而人们对这群人的关注也是极其有限的,偶尔冒出来的一点好奇,也常常就在稍纵即逝的瞬间过后,遗忘于自己的忙碌之中,自然是乌飞兔走,两不相干。
然而,当这群犯人的身份不再那么普通,当他们是抗日民主政府的犯人,当一切本应像往常日子那样理所当然地继续发展却又被突然打断――当抗日民主政府遭到鬼子的扫荡,当关押他们的监狱遭到敌人的袭击,当管理他们的所长在掩护他们撤离时不幸牺牲,当负责带领他们重返组织的看守腿部中弹,当他们突然脱离了管制,一切就突然变得不再简单了。
此时的犯人们,可以说是被动地处于人生最为关键的一个岔路口,但是他们同时又拥有选择以后人生道路的主动权。生存意志是人类性的,在严酷的战争状态中,当生与死横在面前的时候,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尤其是人的心理变化,是极其复杂、更加微妙的。为了活着,人的选择有可能在瞬间发生质的转变,或者走向伟大,或者走向渺小甚至卑贱,良知与丑行常常就在一念之间。更何况这又是一个十分特殊且复杂的群体,他们身份各异,甚至劣迹斑斑,有做过小偷的,有当过土匪的,有嗜赌如命的,有抽大烟上瘾的,还有曾经给鬼子当汉奸的……
作者的高明就在于他巧妙地设置了这样一个特殊的情境――特殊的人群在特殊的年代必然会有特殊的故事。生欤死欤?系诸一发。小说就在这样的选择性悬念中跌宕展开,也向我们昭示了故事的发展必将伴随着一场场残忍而艰难的内心搏杀。
强烈的求生欲望和人的很多本能反应同潜在的道德意识在每个犯人的内心复杂地交织和纠缠着。是抓住时机逃离犯人队伍从此隐姓埋名乐得逍遥快活,还是冒着危险返回谷山监所继续保持犯人身份接受劳动改造,抑或转身投敌卖点情报谋个一官半职享受荣华富贵?于是,有人迷惘了,甚至企图偷了同伴的钱财远走高飞;有人投敌了,竭尽所能踩着自己难友的身躯求得飞黄腾达;有人动摇了,一边偷偷出卖情报,一边又在同伴面前演着“苦肉计”,两边讨好,以图双管齐下,稳留后路;但更多的人还是选择了留在负伤的马看守身边,昔日在抗日民主政府中接受的教育和改造,如今监狱所长、看守和战士们的拼死掩护,已经使他们心目中“犯人”的概念逐渐淡化消解,取而代之的是无比骄傲、自豪、光荣的抗日战士的精神与豪情。
当然,生的挣扎是真实而且迫切的,在《气血飞扬》中,作者突破了英雄与犯人的身份界限。想到敌我双方力量的巨大悬殊,曾经是犯人的王二糊涂和曾经是监所看守的李成文都开始左右摇摆,他们既给敌人当内线,却又对敌人隐瞒了一些重要信息,他们都希望能给自己留下更加保险的生的道路。他们都一直活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但本应成为英雄的李成文却一错再错,最终身败名裂,而王二糊涂则在马看守和其他犯人的感召下,最终用自己的一死掩护了同胞,使自己卑微的生命重新获得尊严,而他们身份与灵魂的错位,也让我们从一个独特的视角看到了战争中人性的颤栗与升华。
英雄,曾几何时,是“敢为天下先,一击定万民”的非凡之士,平民百姓何敢妄称英雄,更何况是一群犯人!经历了死亡的恐怖与战火的考验,他们更加深刻地反省了自己以前的行为,也重新认识了生命的价值。他们在战争中洗涤着自己的灵魂,往日的恩恩怨怨,都在同仇敌忾中化解得无影无踪。曾经被列为“罪行”的偷盗赌抢各种绝活被他们巧妙地运用于同敌人的周旋斗争中,他们的机灵、智慧甚至有时透出的匪气,常使事态发生出人意料的大转折,他们偷鬼子的洋行,炸敌人的炮楼,端伪军的据点,劫日伪的法场,他们的抗战传奇纵横开合,妙趣横生,让人击节赞叹,心下大快。他们释放出来的狂放的生命力更如火山喷薄般一发不可阻挡,虽然他们既不是八路,也不是民兵,又不是游击队,但他们的爱国心和英雄气却毫不逊色给任何人,面对日寇惨无人道的酷刑折磨,他们或横眉冷对,或破口大骂,飓风难摧,气势如虹;赢得战役的胜利,他们会大碗喝酒,大口吃菜,毫无顾忌地畅露心扉,或侃或谈或哭或笑,甚至还吹着大牛,汪洋恣肆,酣畅淋漓;他们在战争中也赢得了自己的爱情,尽管那爱情尽染死亡的鲜红与悲壮。一寸河山一寸血,尽管他们没有任何正式编制,只有一身的草莽气息,但即使师出无名,却也壮怀激烈,甚至昂扬赴死。他们生命的价值也因此而变得悠长、久远,一直伸展到天地的尽头,历史的尽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