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阎崇年,清史、北京史研究专家,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著有《努尔哈赤传》、《袁崇焕传》、《清朝通史・太祖朝》、《清朝通史・太宗朝》等学术著作。近日,其《中国古都北京》一书由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出版。全书记录了50万年来北京地区的世事变迁,尤其对元明清三代帝都的演变作了细致的描述。全书随文插入北京风物照片、图片资料达700余幅,照片均为严钟义等摄影师专为此书实地拍摄。虽是通俗读物,其文其图却体现出作者严谨的学术风格。 |
前门箭楼箭窗有多少?这么简单的问题,会错吗
一档“百家讲坛”栏目、一部《正说清朝十二帝》,让阎崇年从学术圈走近普通百姓。然而,他对北京史的研究,至今仍然很少为公众所知。自曾祖一代便居家京华的“北京情结”、曾任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所长的学术背景,使他在清代北京史研究的“一专”之外,还遍览各路学术精英的研究成果。尽管如此,写作《中国古都北京》这本通俗读物,对他来说,却不轻松。
“这本书里写到的所有现存明清古迹,我都亲自实地探察过――坤宁宫萨满教祭祀的大锅,直径多少、深多少?我不仅去看,还带个尺子去量。探察,每每让我们有‘新的发现’――前门箭楼的箭窗有多少?书上有记载,这么简单的问题,会错吗?我们一个个数,书上说的,就是差一个!安定门外的黄寺塔,包括一些著名学者都称其为‘清净化域塔’,‘化域’作‘王化外域’讲也解释得通,可没有这个词啊?我们去实地看,当时天已经黑了,我们就用手摸,确认不是‘化域’,而是‘化城’。又去广济寺查《法华经》,终于查到了‘化城’的出处。
“在书里,有一些与众不同的看法。比如清代八旗兵驻防北京的方位,有人说是按‘五行’布阵的。努尔哈赤懂‘五行’么?其实,清军入关,一路向南。敌人在南边,攻城掠地时自然北面最安全,所以皇帝直属的黄旗在北;东西次之,所以他的两个儿子分掌的白旗、红旗在东西两侧;南边是敌人突围、救兵驰援的必争之地,最为危险,交给了努尔哈赤侄子执掌的蓝旗。方位不同,实际是亲疏有别。驻防北京的八旗兵,不过是延续了过去的传统。”
在《中国古都北京》中,很多看似不起眼的段落,实际上都是从阎崇年先生几百万字的学术成果中萃取而来。与那些靠网上资料拼拼改改,“重在包装”的所谓“文史读物”相比,自有天渊之别。细细品味,读者不难体会。
二手材料靠不住,我也吃过亏
学术功力,就是在一次次文献研究和实地探察中,被积累起来。与阎崇年先生交谈,能够强烈感受到他的学者气质――自信,却不自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明代于谦的这首《石灰吟》是写进了教科书的名篇。阎崇年在引用这首诗时却意外发现,所有著述都说此诗出自《于谦集》,遍寻《于谦集》却找不到这首诗。为这一个“小”问题,他花了一年多时间,查遍北京、上海、宁波天一阁的孤本善本,最后得出结论:此诗不是于谦写的。这在学界引起轰动。
 “现在,我们亟须克服为学的浮躁心态。现在很多学校要求在读研究生要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两篇学术论文,有的甚至规定历史系的研究生要在《历史研究》上发一篇。读博士,只有三年时间,怎么能完成呢?即便完成了,学术水准能保证么?我研究了一辈子清史,现在算下来,平均每十年才能在《历史研究》上发一篇文章。不到两万字的《张吉午与〈康熙顺天府志〉》,我花了近四十年才发表。
“现在,我们亟须克服为学的浮躁心态。现在很多学校要求在读研究生要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两篇学术论文,有的甚至规定历史系的研究生要在《历史研究》上发一篇。读博士,只有三年时间,怎么能完成呢?即便完成了,学术水准能保证么?我研究了一辈子清史,现在算下来,平均每十年才能在《历史研究》上发一篇文章。不到两万字的《张吉午与〈康熙顺天府志〉》,我花了近四十年才发表。
“二手材料靠不住,我也吃过亏啊。‘西北明积雪,万户凛寒飞。惟有深宫里,金炉兽炭红。’在‘百家讲坛’讲光绪的时侯,我引用过他的这首《围炉诗》。备课时,没找到一手材料,我特意找了三种不同的文献核对。但没想到还是错了。讲完后,有读者来信,提出诗韵不对,第二句的‘飞’字可能错了。我马上请故宫专家帮我查查原始档案。果然是‘风’不是‘飞’。我觉得不踏实,亲自去查,又发现一处错误,不是‘凛寒飞’,而是‘凛严风’。这件事给我很深刻的教训。”
在“百家讲坛”,每讲一次,就如同进一次“炼狱”
“百家讲坛”改变了阎崇年的生活;而“遇到”阎崇年,也改变了“百家讲坛”的“命运”――听了阎崇年的初讲,“百家讲坛”决定变“一人一讲”为“主讲人制”,由此从收视率的倒数第二,一跃名列前茅;甚至,在某种意义上,阎崇年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阅读趣向――2004年秋天,《正说清朝十二帝》刚一问世,在北京书市“意外”掀起热潮,不仅开创了“正说”先河,也被认为是开启今天日益高涨的“读史热”的发轫之作。
“在‘百家讲坛’,每讲一次,就如同进一次‘炼狱’。没有研究的当然不能乱说,还要琢磨讲法――讲‘筋骨’,大家听起来没意思;讲‘血肉’,节目时间有限。怎么办?绞尽脑汁。”
不过,也有回报。
“首先,要讲新东西,‘新说’会推进自己的研究。比如,讲‘鸦片战争’,以往的主旨都是‘落后就要挨打’。我通过分析认为,鸦片战争失败有必然因素,但更多是偶然因素。道光帝的三次决策失误应当承担主要责任。
“其次,是来自观众的挑错。比如,我讲兴城‘在辽西海湾,离海12华里’。马上,有观众来信,是专家,还特意附上详细的地图解说,告诉我,兴城位置的准确说法是在‘辽东湾西部’。很多这样的例子,对我的研究都是促进。”
“闻错则喜”,阎崇年先生一方面在再版中不断修正;一方面,对提出意见的读者,全部赠书感谢;留下电话的,坚持一一回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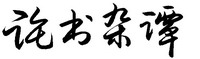 “不必苛求历史学专家都写普及读物,但专家受过长期的专业训练,写出的作品更加扎实。历史学的发展经过‘为神服务’、‘为君服务’、‘为民服务’三个阶段。我想,今天的史学工作者应该多腾出一些时间和精力来,为普通大众服务。”
“不必苛求历史学专家都写普及读物,但专家受过长期的专业训练,写出的作品更加扎实。历史学的发展经过‘为神服务’、‘为君服务’、‘为民服务’三个阶段。我想,今天的史学工作者应该多腾出一些时间和精力来,为普通大众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