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城市能否让生活更美好,不仅仅是看这座城市的硬件,更重要的是要考察这座城市居民生活的幸福指数……
――题记
你认识多少邻居?
如果从一个城市的“细胞”来观察上海的变迁,或许长宁区周家桥社区
仅仅还是在1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片棚户简屋和杂草丛生的旧厂房,在上海人的眼中是典型的“下只角”。那些搭建的简易棚屋,相互勾连,七拐八转,又没有门牌号码,走进去如同进了“迷宫”。如果没有本地“土著”引路,你会找不到返回的路。可是现在去看看,这里矗立着一栋栋崭新的中高档商品房――仁恒河滨、上海花城、圣约翰、虹桥河滨、春天花园、虹桥万博、天山河畔……房价从原来的每平方米数千元,飙升到了每平方米两三万元。
变化的不仅仅是住宅建筑,更重要的是居民成分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人们用“新社会阶层”来描述住进这些中高档楼盘的居民,他们是企业家、IT精英、职场白领、职业经理人、外企“打工皇帝”、高级会计师、律师、外籍人士……
物质生活条件翻天覆地的变化,有没有使居民的幸福指数有新的提升呢?这个问题还真不好回答。街道和居委会的干部、工作人员发现,随着棚户简屋的消失,过去那种端着一碗大排面串门聊天,邻里之间鸡犬相闻、相互照应、其乐融融的古朴民风也消失了。“远亲不如近邻”成了不再重现的图画。居委会的干部上门走访,按响门铃,门打开一条缝,屋内人用狐疑的目光打量着访客,冷冰冰地说一句:“有事找我的律师去”,门便咔嚓一声关上了。
因此,居委会工作人员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新型的邻里关系:“门对门,不相闻,同住小区陌路人”。
其实,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欧美一些发达国家,这是一种如同艾滋病一样普遍蔓延的现代城市病。美国一位学者称,现代社会快节奏、高强度、重压力的生活方式,改变了古老的人际交流和沟通方式。研究资料显示,人的孤独、冷漠、陌生感会促成犯罪和反社会行为。
如何改变这种老死不相往来的新的邻里关系,成了周家桥街道和下属居委会领导、工作人员备感头痛的新课题。他们为此不断探索社区邻里关系的新模式,历经数年,居然大有成效。他们的经验不仅值得上海其他社区,或许也值得世界很多发达国家城市借鉴。
新近有一家媒体对这里的居民生活情况进行抽样调查,其中一个问题非常耐人寻味:你在小区里认识多少个邻居?如果让我来回答这个问题:非常遗憾,我住进某花园小区已经有一年了,但小区里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周家桥社区被调查到的居民是怎么回答的呢?
――顾成倬(70岁,退休前为某外企总经理,现住上海花城):“可多了。业委会的同仁(他担任业委会副主任)、读书小组的书友、还有我们花城黑板报的‘秀才’们……在小区里认识我的人比我认识的还要多,见了面都叫我一声‘老顾’!”
――赵光贤(80岁,退休前为某研究所副所长兼总工程师,现住圣约翰名邸):“约摸有五六十个吧。主要有三类:同住一栋楼,特别是同一层的邻居;通过参加小区读书小组、文娱活动、早锻炼认识的;通过参加小区工作,如巡防工作结识的朋友。”
――朱莉苓(67岁,退休前为工程师,现住仁恒河滨花园):“那可多了!拳操队里20多个人,读书会的20来个人,还有楼里进进出出的邻居们,总共好几十个呢。”
……
笔者在采访一些居民时,他们表示自从住进了周家桥社区,就不想搬到别的地方去了。如果有能力再买房,还想买周家桥的。这样的归属感是如何形成的?
这是另一种传奇。是比棚户区变成高档商品房和高级商业区更为神奇的奇迹!
两个不同的“群体”
陈丽云是2007年入住周家桥天山河畔花园的。她先生经营着一家医疗公司,为了支持先生的事业,她只好放弃自己的工作在家负责带养孩子,当起了年轻的全职太太。她每天的工作就是早晨开车把孩子送到幼儿园去,下午三点多再把孩子接回家,把饭烧好等全家人共进晚餐。还有大量时间干什么呢?没有事干。常常感觉很无聊。手上拿着电视机的遥控器,不停地转换节目……
是什么把她吸引出家门,从“无聊”中解脱出来的呢?两个字:活动。任何号召和动员之类的行政手段都不会奏效。而“活动”也必须是居民十分感兴趣的。小区里有个俱乐部,所有成员都是小区里出现的一个新兴群体:全职太太。跟她差不多大年纪的居委会主任童明琪介绍她参加:“小陈,来吧,这里很开心哦!”陈丽云能歌善舞,就参加了俱乐部的合唱部,现在成了合唱部的部长。这里根据会员的兴趣爱好分成不同的部门:议事部,专门负责筹划俱乐部的各种活动;爱心部,专门做一些帮助老年人量血压、普及健康常识的事情,以及当某地发生重大灾害时组织捐助活动;厨艺部,交流烹饪的经验;制作部,制作小工艺品义卖,卖来的钱用作助学帮困;还有一个很受欢迎的教育部,这里有英语班、日语班、韩语班、沪语班,参加者全凭兴趣,不是为了升学,也不是为了求职,学习变成了毫无功利目的的快乐事业。沪语班最热门,因为很多全职太太都是新上海人,她们想尽快掌握上海方言。担任老师的也是精通各类语言的全职太太,她们义务教学,与别人分享自己的知识,自己也获得一种充实感。
在参加俱乐部前,王娟成天缠着先生,不让他出门,因为她不能忍受一个人在家的那种寂寞感,她学不会如何享受孤独。他们全家原来生活在湖州,因为女儿从英国留学回来到上海外企工作,夫妇俩卖掉了湖州的房子,入住到上海天山湖畔。先生被太太“缠”得无法出门,生意也荒废了,感到如此下去总不是办法,就带着太太到居委会,让她报名参加全职太太俱乐部。王娟进入俱乐部后,认识了很多女友,大家一起又唱又跳,拥有了自己的精神空间。她老公就安安心心做他的期货生意去了。
陈丽云对笔者说,工作时的群体与加入俱乐部后又融入的新群体,给人的感受完全不同。工作时,要考虑处理好与上司、同事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甚至充满一种相互提防的敌意。而社区群体是一种没有功利、竞争的人际关系,在这样的群体中身心得到高度放松,真正享受到了生命的快乐。
在这里,由于社区居住人员的特点不同,他们在居委会的组织下结成了不同的兴趣团体。仁恒河滨花园在周家桥是高档社区,这里有来自52个国家的居民,人称“小联合国”。这些居民平时都独往独来,相互间语言不通,大多都感觉自己没有任何事有求于人,没有跟陌生人交往的欲望。如何也让他们享受到社区生活的乐趣呢?居委会负责人金惠惠想到的办法,也是开展能够吸引老外的各种活动。比如开办汉语班,免费提供老外学习中文的机会。这个班一开班,就吸引了很多老外。因为他们深感头痛的就是生活在中国上海,却不懂中文,连出门叫出租、跟中国同事间打招呼都很困难。汉语班老师是曾旅美40年的美籍华人,精通英语汉语,他教那些初学汉语的老外完全游刃有余。不久,从英国留学归来、有海外汉语教学经历的滕小姐,听闻小区开办汉语班,主动要求担任第二位义务教员。各种不同肤色的“学生”通过一起学习中文,拉近了邻里关系,让小区成了其乐融融的小小“地球村”。
这里还开办有国画班,居委会定期请上海美术家协会的画家来教授国画技法;沪语班、茶艺班、元宵猜谜……这些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活动,如同磁石般把老外从公寓楼里吸引出来,带来了欢声笑语。
“新上海人候鸟俱乐部”――这个名称乍听让人费解,其实只要到杨家宅社区来走一圈,就明白它的内涵了。在周家桥,这是一块“硕果”仅存的老城区,住在这里的居民四分之一是租住的各类临时打工族、创业者、淘金人,有外来务工人员、有开门面小店的小老板、有到处找工作的大学生。因为这里房子离市区近,租金又相对低廉,他们像候鸟一样飞来,过一阵子又飞走了。有的事业有成,“飞”到更好的地方去了,也有的受挫又“飞”到别处去“觅食”了。
由于这里的人员处于不停的流动之中,居委会就成立了“新上海人候鸟俱乐部”,所有的活动也根据居住人员的特点展开:举办法律知识讲座――因为这里发生邻里纠葛矛盾的很多;请厨师来教他们学烧上海菜――从品尝本帮菜的味道开始融入海派文化;请老师来教他们学上海话――让他们在上海尽快找到“阿拉”家的感觉。特别是到春节时,居委会在活动室架起煤气灶,自己动手为“候鸟”们烧年夜饭,每个孩子还能拿到一份压岁小红包。每到此刻,他们如同回到了故乡,内心充溢着在老家过年的温馨感。
另一个居民社区的情况跟杨家宅很接近,只是这里流动人口少,孤寡老人多,于是一支由小区10多位女医护人员组成的“女知联服务队”活跃在小区,她们定期为老人量血压、提供健康咨询,甚至登门为卧床的老人打针、吊水。长丰地段医院护士长张开明是服务队的发起人之一,她把家中电话和手机电话号码提供给居委会,常常在深更半夜,她接到老人打来的紧急求助电话,就立即起床赶过去。后来有不少男医生加入了这支服务队,“女知联”索性更名为“医疗志愿者服务队”。
曾经在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担任歌唱演员的常燕和她同样痴迷唱歌的先生顾长龙,于2002年7月一住进大家源社区,就感受到一股扑面而来的热浪。从小区活动室传出的朗朗歌声唤醒了他们沉寂已久的歌喉。他们很快加入到合唱队,并成了大受欢迎的领唱演员。他们白天在单位工作,晚上参加小区合唱队排练,诙谐地说“白天为生存,晚上为快乐!”“快乐的事业”拉近了邻里之间的距离。
在周家桥还有被称为“美丽人生三部曲”的“准恋人俱乐部”(单身男女组成)、“准新人俱乐部”(由准备结婚的恋人组成)、“准妈妈俱乐部”(由已婚准备生育的年轻妻子组成),人们可以在这里享受到人生三阶段所需要的特定服务。
超越“共享社区”
笔者从一份资料中了解到,为解决人与人之间隔膜、冷漠、以他人为“陷阱”、同住小区却形同陌路的现代都市病,从上世纪70年代起丹麦就萌发了一种名为“共享社区”运动。后来这一新兴的运动,扩展到了欧洲很多国家,以及北美和澳洲。目前,在丹麦大约有5%的居民住在“共享社区”里。在美国民间专门有一个“共享社区联盟”组织,在全美有很多秉持“共享社区”理念的群体。
“共享社区”最重要的理念是“主张邻里之间重要的是相互支持、了解及分享。”美国佛罗里达州热衷于“共享社区”活动的戴夫・芬尼根说:“共享社区会有定期的聚餐,我们这个社区的成员都可以参加,有人做志愿者提供服务――准备饭食以及饭后洗碗。”美国学者泰・布克斯曼批评推崇“个人主义至上”所产生的弊端:“你可以说你独立获得了现有的一切,但是难道你不需要朋友吗?而大多数美国人回到住宅区,泊好车后则不看身边的邻居一眼。”而“共享社区”的理念之所以开始风行于西方社会,正是因为他们力求在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之间寻找一种平衡。有人比喻:“共享社区就像一个扩展了的大家庭。”
美国“共享社区联盟”主席里克・莫克勒说:“我们都是社会动物,都害怕被所有人抛掷到一旁无人理睬。在一般的社区里,你遇到热情的邻居和极其冷漠的邻居的机会是均等的。但是在共享社区里,人们都有着相同的理念,你不用再看邻居难看的脸色了。”
周家桥街道把他们在社区开展的一切活动命名为“会所文化”。他们的很多做法都与“共享社区”理念接近。比如,西方很多“共享社区”会定期举办跳蚤市场,居民们把自己用不上的物品拿出来相互交换;而仁恒河滨花园也定期举办类似的跳蚤市场。难道周家桥社区的做法借鉴了国际上的“共享社区”理念?周家桥街道的负责人在回答笔者的提问时说:“我们开展会所文化活动迄今,对西方的‘共享社区’运动一点也不了解。我们只是从实际出发,努力创造令人感觉温馨和谐的社区文化。”
那么说,周家桥开展的“会所文化”,一不小心与国际接轨了?或者说不谋而合了?其实,仔细对照一下,两者既有共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相同的地方是让居民走出家门,形成一个新的社区群体,邻里之间相互帮助,共享社区的各种资源;不同之处,或者说周家桥“会所文化”超越“共享社区”理念的一个独特之处是,他们努力让更多的人成为发光体,成为社区的“太阳”,温暖别人,自己则在“燃烧”的同时获得一种精神的升华和至乐。
陆玲娣老太太是仁恒河滨花园拳操队的队员,某天老伴儿突发心脏病,队友们闻知,马上动用所有的人际资源,很快让老人住进了华山医院。后来,相濡以沫一辈子的老伴儿病故了,陆玲娣老太太一直情绪抑郁,连拳操队活动也懒得去参加了。这时,拳操队的老姐妹们轮流上门陪她聊天,拳操队队长、已是古稀之年的廉珊媛出资组织陆老太和另外三个老人一起到云南去旅游散心。半个月后回到上海,笑容又回到了陆老太的脸上,在晨练的行列中又可以看到老人的翩翩舞姿了。
一位在周家桥社区创业有成的老总,主动到街道了解社区里有哪些需要资助的贫困大学生。他提出三个条件:一、必须是家庭真正困难的大学生;二、不安排任何与资助者见面的仪式;三、不在媒体公开报道。因此,请原谅笔者这里不出现他的名字。连续四年,这位企业老总已资助了11位贫困大学生。这些大学生从未见到这位充满爱心的恩人是什么模样,但他们从他的善行中学会了如何成为传递温暖的光源――他们热心帮助邻里修理电脑、报名参加无偿献血、为民工子弟学校义务教学、为患重症的病人捐赠骨髓……
有人用“上半年跳舞、下半年唱歌、全年打乒乓”来概括周家桥会所文化活动的内容。其实,这样的概括太过于笼统了,远远不能展现周家桥社区缤纷多姿的活动内容,更无法让人领会其深刻的内涵以及对建设和谐社区、对建立新型都市人际关系所具有的社会学意义。
“温馨”――当周家桥社区居民用这两个字来谈自己的居住感受时,笔者觉得已经没有必要用更多的文字来描述,或用更多深奥的概念来诠释“会所文化”的时代价值。我们无法说清它是一种对传统的回归,还是一种全新的创造。他们的所有理念和实践都是从现代都市社区土壤中萌生出来的。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项在社区蓬勃发展的“快乐的事业”的背后,有一群来自街道、居委会、社区居民中充满热情、乐此不疲的人。如果他们仅仅满足于在社区布告栏贴贴通知布告,或用电动喇叭在小区喊喊“防火防盗”之类的话,是不会出现如此红红火火的“快乐气象”的。
要感谢那些默默无闻的“快乐事业”的幕后推手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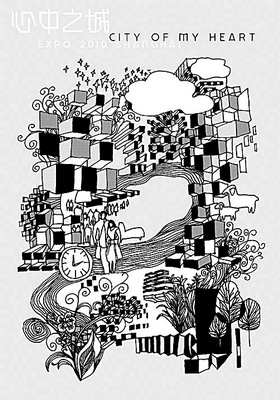
心中之城沈浩鹏
(注:有关“共享社区”的资料均引自方禾《西方社会兴起共享社区》一文,刊于2005年8月30日《国际先驱导报》)
陈歆耕1955年生,江苏海安人。著有报告文学《青春驿站》、《点击未来战争》、《废墟下的觉醒》等。现为《文学报》社长兼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