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什么是“打工诗人”?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有人开始为打工族中的诗歌写作者做了群体性的命名:“打工诗人”。至于这样的命名是否合理,我也不想在此作过多的论述。我感兴趣的问题是,“打工诗人”的作品究竟体现了一种怎样的精神和心态?他们何以会产生这种心
中国的现代化运动要求重建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体制,也要求重建中国的文化。在中国的现代化历史变革进程中,“打工族”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存在。打工改变了数以亿计的中国人的心灵史、生活史、个人编年史,这不仅是身体的、心灵的,也是文化的、形而上学的。“从深圳上海北京广州打工/回来的人/身上有不同的城市/一个人与另一个人/暗暗较劲/意思是我在的那个城市/比你的要好//他们以前在村里熟识/回来后彼此陌生了/在村里站在彼此眼前/有一个城市与另一个城市的距离”(张绍民《比较》)。我们所经历的历史,它不仅左右着个人的生活和命运,甚至也在我们现在的心理定势、潜意识和语言中显露出来。诗人是一个种族的触角。诗歌是形象的人类学,是对种族记忆的保存。历史一再地昭示,每当一个时代处在巨大的转折时期,敏感的诗人常常会从自身的经历中攫取某种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的事物,作为自己宣泄和寄托内心隐秘感情和思绪的参照。近些年来,出现一批“打工诗人”和写打工生活的诗歌,也自然成为无法回避的事情。“打工诗歌”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真实的见证之一,让我们窥见到一个长期以来被忽视的社会群体的真实生活和心理状态。
再卑微也要有尊严,再贫贱也要自由地表达意志,再羸弱也要拒绝那些强加于己的东西。“打工诗人”的写作是完成内心道义的自我反省与确证。民工面临着经济吸纳和社会拒绝的悖论性生存处境,而对这种先天的社会不公,从他们进入城市的那一刻起,就必须无条件地表示默认,并同样默默地遵守着。他们和城市的距离感如同黑暗与光明之间的反差那么遥远。遁入自我的阴影心态使得打工者的边缘地位愈来愈明显地突兀出来。在警醒世人的同时,也使得打工者更加无奈和消沉起来。于是诗人们在跨越阴影意识或者在宣泄阴影意识的同时,还更多地表现在对社会的抗争和寻求世界的认同和理解上。阴影是任何一件事物都无法掩藏的根本属性,有如孙大圣那根仓皇之中竖在庙宇后边的尾巴;阴影也为诗人们提供了认识时代生活的另一个特殊角度。“自从那天/踏上了南行的列车/单调而沉重的生活便/常常让我忌恨阳光的辉煌后面/是否还隐有张悲哀难堪的面庞/于是每天下班之后/总不忘去审视那株年青的枫叶树/是否已罩上了忧郁的额纹/而疲惫不堪/拥有阳光的日子/并不多见……”(卢杨林《南行的忧郁》。在阳光的辉煌后面,在阴影中,诗人“必须睁圆眼睛”,在自己的位置上思考和书写。他们深入挖掘和揭示日常生活与真实生命中到处藏匿的黑暗,从而重构我们的时代、我们的经验和我们的公共空间。
 |
|
|
谁试用谁/证明你有用/在三月之内/从一个七天到下一个七天/你被试用/你正在被试用/生活没有窍门//你的一生都在被试用/从一个试用期到另一个试用期/生活没有窍门/你乐意被试用,决意/你试用别人/这不现实,世界不现实/那一个梦现实//必须证明你有用/为谁所用?/钱是小过门/休止符出现,别问/别问。痛苦爱上你/这是幸福?什么都别问/你被试用//你是我/打工者,流浪者/吹笛子的人,在夜的/深处,你仍在试用/被风,欲望之塔/所有的人都在试用你/连同自己,妓女//谎言重复千遍成为真理/一个被试用连续的人/一个被连续试用的人/一个永远试用的人/一个人永远试用/一个与试用期等号的人/一个等号于试用期的人//0K!你被试用/照我的意思做,必须/这样。听话,虚伪叫忠诚/表现好才能加工资/在我眼里你还是个孩子/写诗与唱卡拉OK有区别吗?/傻冒,说话呀(噢!命运)//一个异乡人/一个没文凭的人/一个诗歌爱好者/一个说梦话的人/一个忧郁的影子/一个行走不定的人/一个试用期中的人(谢湘南《试用期与七重奏》)。
“打工诗人”是“一个异乡人/一个没文凭的人/一个诗歌爱好者/一个说梦话的人/一个忧郁的影子/一个行走不定的人/一个试用期中的人”。诗歌要求“打工诗人”在生活面前做一个“世故”者,而非纯情少年。在“打工诗人”的诗中,我们看到活生生的、生长在小时代的语言在他们的诗中成为叙述的基本成份,我们看到了诗歌和打工生活之间的血肉关系。
2
“打工诗歌”的真实与力量并非来自于“打工诗人”的写作水平与技巧有多高,而是源自于他们对生活的感同身受与熟悉。他们写的是自己的生活,是自己的体验与发现,是自己的苦痛与忧伤,也正是因此,他们出示了一种全新的生活与体验,一种人物与细节的真实。这也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现实,是具体而具象的现实,而不是抽象、想象与写意的现实。沉入社会生活底层的“打工诗人”,摆脱了一种被抽象化的时代情绪,看到了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一面,始终与此保持了直接的感性认识,并让诗歌对现实发出了它的指控与挑战。民工问题不是只关乎一些特定地域和特定人群,作为一个中国最广大的弱势群体,他们长期受到的不公平、不公正的待遇,关涉到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的公正、公平性问题。对于他们合法权利的捍卫,也是对人类基本生存权利的捍卫。“打工诗人”把头伸向阳光辉煌的后面,在大时代留下的阴影中,在漂亮的舞台后面,他们的手已经无法掂量夜的深度,他们的脚步由轻及重。在阳光巨大的辉煌后面,往往隐藏着更巨大的黑暗。“刘晃祺,我同在天涯的打工兄弟/在工厂流水线/为命运加班的你/超负荷劳作日复一日/在那个/让你23岁亮丽生命/走完人生最后一个驿站的/那个黑色的7月13日/……你,摇摇晃晃/离开了无限眷恋的土地//消化道出血
呼吸系统衰竭/生命已快走到终极/昏迷后醒来的你却说:‘别拦我,我要打卡/迟到了要罚款……’/哦兄弟为什么 为什么/为什么这样畏惧胆怯/我们不是现代包身工
我们不是奴隶/为什么不说一声‘不’!/为什么不把抗争的拳头高高举起?!/……3万元就换取了一个鲜活的生命啊/青春逝去里饱含多少悲怆与叹息/多少个打工姐妹兄弟/还在流水线上工作超时/栖居皆危房
面容呈菜色/薪水难到手
劳保无人识/……让我用微弱却不屈的笔/向刘晃祺一样的姐妹兄弟/发出心底茁壮的呼吁”(罗德远《刘晃祺,我苦难的打工兄弟》)。这首诗写的是广东美而进毛织厂打工仔刘晃祺因厂内日复一日的加班,身体极度虚弱,最后吐血昏迷,命殒异乡,再也分不清“自己是在白天还是在夜里”。没有什么比刀剑更直接,没有什么比语言更锋利。“打工诗歌”再次使我体察到这一点,作者饱满的情绪使诗句怒胀、克制、欲发还收,但又比发出的弓箭更有力,更击中要害。这种纪实风格的诗,它的直接,使人震憾。真正的悲剧,其实在悲剧发生之前就已经发生。“打工诗人”刘大程在万行长诗《南方行吟》中写道:“许多手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扼住打工者的咽喉,撕碎打工者的梦想/而天地很大,打工者却都是瞎子和哑巴/数千万之众,在异乡和老板面前便成为弱势的群体”。2005年8月9日的《新京报》重点推出了这首反映农民工艰难打工生涯的万行长诗,这也是在《新京报》开辟诗歌栏目以来首次用全版推荐一位诗人。“打工诗歌”的出现,显然不是诗人为了诗歌而进行的实验之作、先锋之作,而是诗人在坎坷的打工生活中呕心沥血的切身体会,它们语言上叙述上的“不够艺术”和思想上的“不够成熟”可能会遭到否定或耻笑,但谁也挡不住它们里面迸发出来的血性的光芒,那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的诗歌,那是劣质的生活场景和悲苦的命运所生发的情感细节与心灵的呐喊,而不是为了语言、艺术、荷尔蒙、下半身、后现代、与国际接轨等等口号下贫血的矫情之作。在田园的远逝与城市的冷漠中,在历史的缠绕与环境的错谬中,在积郁满腹的烦恼苦痛与无法表达的失语状态中,那被忽视的人群,那被抛弃的人群,那被践踏的人群,那被剥夺的人群,那被侮辱的人群,那被伤害的人群,那无望无告的人群,对于他们来说,生活就意味着忍受生活的侮蔑,生活就意味着痛苦,生活就是挣扎。他们是生活在自己祖国的难民,他们的命运是现代化进程中最不义之事。造成他们伤害的往往不只是某些个人的行为或无行动,而更是社会的无行动。马丁・路德・金说过:“造成我们时代最大的罪恶是大多数人的袖手旁观,而不是少数人的残暴。”不能保护弱者不受伤害的社会,不是好社会。“机器轰鸣声穿过白天/和黑夜/他们已经麻木/常常将黑夜当成白天/把白天当成黑夜/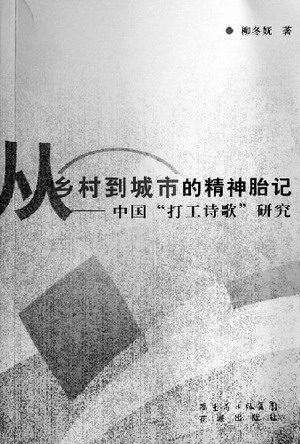 被机器操纵的手/已离开了他们的身体”(张守刚《在工厂》)。“血工伤事故/有人断了手指/有人不见了脚/呻吟是没有用的/你们要抬起头来/用法律作为武器/保护自己/将老板被狗吃掉的良心/揪出来/还大家公理”(张守刚《工伤》)。“他多次被炒/只因太懂《劳动法》/老板需要的是/能干活但不知道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人/小草有小草的尊严/而有了尊严/就只能像小草一样睡露天了”(张绍民《被炒》)。这些诗歌是对残酷处境中本真命运的体验和书写,我们从中能深刻地感受到作为社会最底层的“打工诗人”在叙述背后的强烈愤怒。
被机器操纵的手/已离开了他们的身体”(张守刚《在工厂》)。“血工伤事故/有人断了手指/有人不见了脚/呻吟是没有用的/你们要抬起头来/用法律作为武器/保护自己/将老板被狗吃掉的良心/揪出来/还大家公理”(张守刚《工伤》)。“他多次被炒/只因太懂《劳动法》/老板需要的是/能干活但不知道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人/小草有小草的尊严/而有了尊严/就只能像小草一样睡露天了”(张绍民《被炒》)。这些诗歌是对残酷处境中本真命运的体验和书写,我们从中能深刻地感受到作为社会最底层的“打工诗人”在叙述背后的强烈愤怒。
“打工诗人”以他们富于原创性的文本向我们展示了写作的另一种空间。在一个文字可以淹没人的时代里,我们反而很难遇到真正纯粹的文字。我不知道,“打工诗歌”,那些在打工群落里生长的词,那些带有内伤斑痕的文字,算不算纯粹,但至少与潮涌般的另一种文字构成了明显的分野。面对它,你显然感受着一种震颤性的体验。“打工诗人”,像在底层布下的嗡嗡作响的“精神地震仪”,深入个体中交叉、纠缠、反对、怨恨、郁结的部分,想为我们所处的看似底层的生活留下一份真实的声音与文字的见证。
(摘自《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中国“打工诗歌”研究》,花城出版社出版,定价:25.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