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柜里头,有一本长篇小说――《商鞅》,无事时拿起翻看过。写得一般,缺少让人全神贯注的吸引力。我就那么翻着,准备翻几下便送它回书柜里原样躺着……快要终卷时,有一段文字却让我的目光停了下来:那时,商鞅躲避新君惠王和公子虔的追缉,仓皇在路,这日逃至一家客店――
客店老翁按住他的手,坚决地说:“先生,没有路验,我们不能收留你。这是商鞅丞相制定的法律。《秦律》规定:收留没有路验的人,剁右脚。”
客店老妇人不满地说:“你背《秦律》干什么?这么大冷的天,先让他吃饭吧。”
客店老翁摇摇头:“吃饭?《秦律》说:给没有路验的人饭菜,砍右手。”
商鞅说不出一句话,他看着客店老翁把桌上的饭菜一样一样端起来,拿走了。
客店老翁冷淡地说:“先生,实在对不起。您请去县衙门自首。我实在不敢收留您,别的客店也不会收留您。商鞅丞相规定过,匿奸者与奸细同罪。若留的客人是奸细,全家斩首,十家连坐。”
商鞅央求地说:“那,给孩子买一点吃的,行吗?”
客店老板固执地说:“不行,商鞅丞相的法律有规定,以食物资敌者和投敌叛国同罪,腰斩,杀全家。还要十家连坐,十家同罚。《秦律》规定,我们不敢不听啊。”
这细节很有意思。我不知是不是作者凭空杜撰的,找出《史记》查对,见《商君列传》这样记载:
商君亡至关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君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蔽一至此哉!”
竟真有其事,像小说!――不像历史。
直至新千年,中国仍有人把他的事迹铺排成厚厚的长篇小说,显见仍有重要的“阅读”价值。这本长篇小说《商鞅》我虽未细读,却读懂了:它的主人公继续作为“改革家”被称颂着。
19世纪起中国迭遭大辱,张扬变法图新之帜实属必然。不过,很多人的历史态度和文化态度往往是,要么极端保守顽固,祖宗的玩意儿动不得一根指头,要么却豁达到顶点,“过去”的所有全是破烂、祸害,统统扔掉打碎方称吾意,于是咸与维新、革命无罪、造反万岁。说来也怪,中国文明垂世五千年,外表一看,谁都以为像是须眉皤然的老者形象,其实骨子里却深藏着轻躁无常的幼稚性情。“幼稚病”的起因,正是急功近利和是非无执――后者尤其要命。比如就因了“变法”这字眼让有些人觉得亲切,商君便被引为同志了,法家也俨然成为中国法制精神的一笔财富。然而古籍白纸黑字地放在那儿,枉言者应该知道他们其实是在胡扯,但大家大约都觉得为着“古为今用”的利益,是非曲直不必那么在意,就算是撒谎、自瞒自欺也不足惜。
这遮罩了是非的谎诳真不知有多少,以至如将它们一一恢复到真相,颇似西绪弗斯的苦役一般无有尽头,但我们也不敢放弃努力――至少,这努力的过程会使我们的心灵慢慢地习惯于信守。
循此,我们先还商君一个真实。
商君在历史上究竟起了怎样一种作用?他给我们的社会、文化、思想究竟留下了怎样一种遗产?这是我们在议论这位古人时真正应该回答的问题。而这样的问题,以往却通通被回避着――回避的办法,便是用商君的功过评价来替代对他所作所为的思考。这倒也是中国最常用的障眼法,对一个历史人物动辄纠缠于功过,什么三七开、四六开、五五开地计较来计较去,而其所作所为之于历史、文化的影响和后果却不被认知和思考。我们对历史难有理性了解的根源,盖即在此。所谓功过的评价,背后倘无合乎理性标准的思考为基石,极易流于功利主义的结论。商君其人,单论功过的话,不正是他,令原本贫而弱的秦国走向强大,渐为霸主,终扫列国一统天下的吗?照这种“功劳簿”的办法,则我们对商君除了颂扬就简直唯有闭口不谈其他。但历史岂是这么一个东西?历史应该是镜子,供后人揽来鉴察,从那里面知得失、明是非,也即所谓“前事之师”。否则,人类真大可不必修什么历史。
关键并不在商君有没有“变法”、有没有让秦国“强大”起来,而在于一提到“变法”、“强大”等字眼我们是不是就被唱赞歌的冲动所左右,而忘记从更高的原则进行思考。那么,何为“最高的原则”?雨果曾说:“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
根据《史记》的记载,商君重军功,奖耕织,打击贵族,立信于民。“行之十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从这个侧面看,变法推进了生产,令人民衣食足,压制犯罪,约民以信,削夺统治阶级特权――这些都与历史的文明方向一致。假使历史上商君的形象都保持在这个方面,后人对他便只有感恩戴德了;可惜事实不是这样,甚至主要不是这样。
孟德斯鸠在《波斯人信札》里说:“我时常寻求,哪一个政府最符合于理性。最完善的政府,我觉得似乎是能以较少的代价达到统治目的的政府……如果在温和的政府之下,人民驯顺,不下于在严峻的政府之下,则前者更为可取,由于它更符合理性,而严峻是外来的因素。”这已经是今天文明社会的一个常识。商君掌权下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乍听起来令人神往,可那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呢?――“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者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乃至“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弃灰于道者被刑”……如果百姓把灰撒在路上也会受刑,则“道不拾遗,山无盗贼”的奇迹又有何可稀罕、可称道的?不仅如此,只怕我们心中还会忽然升起一股巨大的恐惧感,似乎那表面平静安详的社会气氛中处处潜伏着危险、横祸和杀机!任何一个正常的人,是不可能在这样一种气氛底下感受到安全和幸福的,无论它是否已将犯罪现象消灭得一干二净!
几年前,读美国人华莱士的一部小说。它虚构的故事,说美国某市市长痛感世风的败坏,试图创造一个纯而又纯的社会,于是设法在议会通过一项严苛的法律,剥夺了市民除基本生存需要外所有个人自由和权利,同时赋予警察当局以极大权力,稍触者即遭逮捕被送入集中营。上述措施实施后,该市果然秩序井然,起初市民欢欣鼓舞,并无人理会个别持不同政见者的警劝,事情发展下去,人们最终发现这“洁净的”社会环境是以彻底牺牲公正、个性、隐私以及造就不受任何约束和监督的权力为代价的……华莱士的故事我怎么看怎么像商君“变法”后的秦国,虽然时间、地点隔了老远――并且一个出于忧患的虚构,一个却是铁一般冰冷无情的现实。
尤不可忽视的是,商君“变法”在中国历史上开了非常坏的先例:铁桶统治。在他以前,中国固不乏昏君佞臣,像纣、幽、历、晋灵公、屠岸贾之流,但好歹只是以个人之恶祸国殃民,自商君之后,个人之恶则变成制度之恶。它未必会以昏君佞臣式的个人暴虐体现出来,却上升为体制性的暴虐。以往,遭殃的往往只是某个忠臣或某一不幸的家族,不足以构成社会性威吓和钳制,而商君发明的连坐法却终于使每个角落都笼罩在人人自危的白色恐怖之下,这简直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项发明。他还鼓励和强制推行告密,“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者同赏”。可以想象,生活在这样一个“告密时代”,会是怎样一幅令人心惊肉跳的景象。但商君给历史作出的最恶劣的示范,其实是以言治罪:“令行于期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韩非・和氏》里有“(商君)燔《诗》、《书》而明法令”一句,此事不见诸别书难知真假,倘若是真的,则“焚书”的首创者就非秦始皇了。然可以肯定,商君之“治”十分看重对人的精神的压制和奴役,中国政治、人性由此所受的损害怎么估量均不为过。
原先,中国幸而有一种比之于大多数古代文明更富理性的“圣人―仁爱”社会政治伦理,它虽不具有现代民主精神和理念,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算是比较开明,比较不野蛮,比较关怀民权,比较能自觉抑制历史中“破坏性”之恶的一种社会架构。及至春秋战国,社会大乱,变数激增,原有的周礼在新的时代因素面前已嫌陈旧简单,不敷所用,所以诸说蜂起、百家争鸣,各种探索性思想纷纷提出,但以民为本、与民为善、惜民奉道仍是思想主流,无论孔、老、墨、庄、孟,各家社会理想或有别,治国方略侧重或不一,但都是在为一个更开明的社会而努力。只可惜在那样一个争霸为上的乱世,社会注定屈从于对强权的渴望和这种渴望背后的功利原则,理性的思想和学说因无法满足之而为权势者所鄙弃。商君初见孝公,亦优孟衣冠效仿主流思想以“王道”说之(司马迁讥他“挟持浮说,非其质也”),后者竟昏昏睡去。但商君之非孔子正在于此,他不可能处处碰壁、历尽坎坷犹衷心不改,相反,作为天生的投机家,他极快转换了话语,改以“霸道”进言孝公,双方此时一拍即合,而对中国历史的文明方向破坏最甚、干扰最重、危害最巨的一种治政模式就此诞生。
尽管因与“开明”背道而驰的“破坏”性本质,商君“变法”所生成的体制随着暴政很快达到顶点的虎狼之秦的崩溃而一道崩溃,取而代之的汉朝立国不久终认同于比较开明的儒家伦理,此后两千年中国也都将其立为社会的精神基础。但前者毕竟开了一条恶的先河,作为制度它是遭废止了,作为一种野蛮因素和破坏性力量它却在各朝各代的暴政中不时浮现出来。别的不说,中国历史的“特产”酷吏――明显是秦代“严刑峻法”播下的种子――因为个中巨慝层出不穷,司马迁写《史记》时已不得不单给此类人设了专门一章《酷吏列传》――由此“酷吏”作为统治集团的一大门派正式登场了,而这突然出现的酷吏横行现象自非空穴来风,作为替恐怖政治奠定理论基础、并用体制化方式第一次亲手实践它的商君能辞其咎吗?《酷吏列传》始着笔处,很明确地把酷吏之根源溯归于以用刑为能事的秦代,“昔天下之网密矣,然奸伪萌起,其极也,上下相遁,至于不振”。文中的“昔”字,正是直指秦代。
荒唐的是,直到现在还有不少人望文生义,以商君法家身份而将其与“法治”的概念联系起来,真十足揭示中国文化的悲哀。所谓“法治”,必以现代民主精神为基石,不是以民为敌,不是以刑役民、以刑残民,更不是密探统治、恐怖政治;在“法治”理念中,人民非但不是被制约的对象,相反是制约者,所有的法律均以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而立,均以他们的利益为根本,并保证侵害、剥夺人民利益的现象会得到最有效的抑制,纵有发生,亦将完全、迅速予以纠正。试问,商君之“法”骨子里跟现代法治哪里有半点共通之处?当时一位名叫赵良的义者当面质责商君:“君之出也,后车十数,从车载甲,多力而骈胁者为骖乘,持予而操戟者旁车而趋,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书》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将欲延年益寿乎?”如果说商君是所谓“法治”的象征,那么可曾有人听说,哪个现代法治国家的大法官这样遭民嫉恨,出门如此不便?
说到商君之“法”,承其衣钵的韩非子有过一番“法理”阐述,道是:
公孙鞅之法也重轻罪。重罪者人之所难犯也,而小过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无离(罹)其所难,此治之道。夫小过不生,大罪不至,是人无罪而乱不生也。
公孙鞅曰:“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是谓以刑去刑。”
活脱脱一副暴政面目、酷吏嘴脸。什么“重轻罪”,什么“轻者不至,重者不来”,什么“以刑去刑”,且不说这种奇谈怪想在法哲学上何其弱智,关键是它真正暴露出商君所谓“以法治国”乃是彻底的强权和独裁。在这种制度下,人民“动辄得咎”,以“小过”而被“重罪”。1944年郭沫若在《十批判书》里把它形容为只需要“牛马和豺狼”的“极权主义”制度,他当时的眼光真的很不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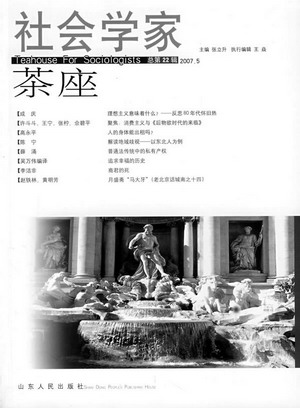 经商君之手,秦国的确走上了“强大”之路,但这样的“强大”也可以被歌颂吗?别人不说,我想陈胜、吴广们肯定是不同意的。在这问题上,有大是大非。秦末破天荒地爆发了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农民起义,便是商君式统治的最好注脚。司马迁给商君的盖棺之论是:“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并痛陈商君留下的两大历史教训:“伤残民以骏(峻)刑”,“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这位两千多年前的史家的是非观没有问题,我们今天有些人的是非观反倒有了问题。
经商君之手,秦国的确走上了“强大”之路,但这样的“强大”也可以被歌颂吗?别人不说,我想陈胜、吴广们肯定是不同意的。在这问题上,有大是大非。秦末破天荒地爆发了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农民起义,便是商君式统治的最好注脚。司马迁给商君的盖棺之论是:“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并痛陈商君留下的两大历史教训:“伤残民以骏(峻)刑”,“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这位两千多年前的史家的是非观没有问题,我们今天有些人的是非观反倒有了问题。
秦孝公刚死,便出现了小说《商鞅》中讲述的那尴尬一幕。不过,商君对拒留其宿的客店老板所发出的感慨“嗟乎,为法之蔽一至此哉!”恐怕是太史公先生加给他的,以使后来者戒。这一幕后不久,商君果然轻易地被政敌捉住,他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商君制定的“严刑峻法”来对付他本人:“车裂商君以徇”,“灭商君之家”。“评法批儒”的年代,把这称做“反革命的疯狂报复”。谁革命与谁反革命不好说,“报复”却是确凿的。死于“报复”的商君,其实大可以安然暝目――因为他亲眼得见,行“法”18年后,连昔日的反对派也已用实际行动继承了他的术策。
(摘自《社会学家茶座》第22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10月版,定价:14.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