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与外:中国人对自然的看法
也许由于我国在绘画艺术上有极大的成就,而我国的美术实际上可用山水画来概括之,因此,在中外文化人士的心目中,中国人是“爱好自然”、“师法自然”的。在环境艺术中,我国的庭园尤以“自然”闻名,不但使得十九世纪以来的欧西人士产生了向往,也
要了解中国人对自然的看法,不能单看“自然”二字。我们要知道在思想的源流上,儒、道两家对自然的看法以及这两种看法怎样为我们后世勉强地汇合在一起。
老实说,要深刻地解说这个问题,已经不是我粗浅的知识所能胜任的了。可是大体说来,我们使用习惯上的内外的观念,与方、圆的观念对照起来看,大约可以得到一种基本的了解。大家知道“方外”的意思是指“世外”,而宗教界称未出家的信徒为“方士”,很显然,这个方框代表着人世。它不但代表了、暗示着人为的居住环境,同时表示在此环境中所必须具备的行为规范。这个方框的外面,是我们不能控制的自然现象。

也许我过分地牵强附会了。我老觉得使用圆形代表道家的空间思想,用方代表儒家的空间观念,是一个很方便的办法。儒家以方为世在历史上是有凭据的。井田之制是一种方形的观念,周礼王城之制也是一种方形的观念。道家据我所了解,并没有清楚的几何形的象征,但后世所提出的太极的观念,是大自然浑然一元的想法,可用圆形的意象来设想。
根据这一种了解,我们对自然没有恐惧感,世内世外表示我们对不同的行为法则的看法。自然界,具体地说是外界的环境,是反映一种无拘无束的人生观。由于对方内、方外观念分得十分清楚,中国人接受了自然环境为一种不加装点的、较高层次的秩序。
当然,真正的自然环境并不如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祥和近人。对自然美的欣赏需要高度的修养,而且必须是精神型的人才成,因为只有在精神化的自然界中,才能克服真实的自然界所加予人类生存上的压迫与威胁。
田园诗人与山水画家造成了这种精神化的自然意象。在他们的笔下,自然界是世外之天堂,人之所以可能飘然而去者,乃因摆脱了俗世之中一些责任的牵连,乃因摆脱了人人所不能看破的一些人间之结,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名利与情丝。自然,借着后世佛、道出世观念的帮助,与现世的文明生活环境,不但构成了对比,而且显然形成了两个极端,使我国的知识分子徘徊其间,时时有不知所措之感。
中国读书人的理想是在世之内外取一个平衡点,亦即所谓“方圆之间”。用一句普通话来解释,就是既通人情,又达天理。在世上做一个规规矩矩、顺遂世情的人,又能优游于山林之间,享受大自然的情趣,修身养性,因而能知天命。故这话也可说为“天人之际”。
努力达到这样的实质生活环境是传统知识分子的目标。可是这种自然观与环境的创造有什么直接关系呢?其结果在我看来,是臆造的自然。能在高山、深林中跋涉以欣赏自然景色的人到底是不多的,能“悠然见南山”忘却穷困潦倒的人究竟也是不多的。大体说来,真正把大自然当天堂的情形不多,方框以内的文明生活仍是大家所迷恋的现实。在若干世纪的传统之中,文学、艺术所描述的自然环境逐渐代替了真实的自然环境,除了真正具有出世勇气的人能为僧为道者外,大部分的中国念书人只能满足于方内的方外感。事实上很多僧人道者所居之名刹大寺常常也是建造于都城之中,或散处于人世之间。方外者对大多数人而言,乃是不受约束、不必为生活操心的生活方式,并不真正意味着处于大自然中的生活。
我国的园林艺术就是在这种矛盾的心境下的产物,自汉魏以来就有记载达官贵人经营园圃的故事。依理说,他们应该走出城外,结竹篱茅舍于山水之间的,但他们宁斥巨资造园。自他们的想象中建造一个自然景色的抄本,其目的显然是可兼有俗世生活与自然情趣。因此,园林艺术的开始就暗示着宫廷园林的走向。
结果是什么呢?中国人自己塑造的自然,与宫廷富丽的人为环境联结在一起,成为一种很奇特的贵族意味浓厚的空间艺术。自然环境不但掌握在画家的想象之中,而且被建筑物穿插着。至于所谓“自然”的本身,变成一些材料,水、石、花、木,按着诗人画家的想象力组织起来,后来则按一定的公式安排起来。
所以明、清以来中国人心目中的自然,成为自然中的素材。大家对石头很考究,对花很考究,对树木很考究。其结果是堆积自然素材,失去自然情趣。这也难怪,试想除了皇家以外,谁能在自己的院子里再建山水画里表现的自然?
背弃了自然的精神之后,我觉得中国人的自然观可用方孔中看世界来比喻,失掉了没有画框而能欣赏自然的能力。用几何来表示,可以说是方内之圆。
正与邪:中国人对环境的价值观
中国人对人为环境所采取的衡量标准是多方面的,阴阳家有风水堪舆之学,是自祸福、休咎来判断。民间的宗教信仰重神鬼之说,是自驱邪避祟的角度上去判断。我们自然也有一套审美的标准,可以自纯美的观念去判断,但是自我个人粗浅的经验中,觉得真正深植于国人心灵深处的价值标准,仍然是自方、圆的观念中传导出来的道德观以及后来与审美的价值浑然一起的正、邪观念。当然,我要请各位同学原谅我过于简化了这一相当繁复的问题,因为我是喜欢提纲挈领,把核心先点出来的。
我觉得只有正、邪二字可以概括国人对环境批判中大部分的内容。与西方文明的美感观念比较起来,我们所能接受的形式很窄。西方人于十九世纪整理了自古埃及以来的各文化中的美观标准,所以具有多样性。由于这多样性,西方人能抛开善与美的关系,只谈美。惟中国自周以来至今天,内容一直加强与补充,根本上没有重大的变化。
大体上说,我们的单一标准是由“方”的引申中来的。第一个抽引出的观念是“正”字。方只是几何形,而“正”则有外形的意义加上道德的含义。“方正”二字连起来,是中国环境观中最高的标准。
在环境的计划中,正字所带来的意思,约略相当于西方文艺复兴以后的观念。其最明显的特色是均衡对称,人处在任何环境中,希望其周遭的建筑等实物,以他自己为中心,左右是均等的。这自然是人文主义观念的基础。可是西方所没有强调出来的,乃是又由“正”引申出的“中”的观念,它使得外在环境与儒家的哲学可以重合。这“中”字在环境上就是中轴线。
中轴线看上去是很轻易的,但不一定容易体会。比如我们东海大学的校舍都是均衡对称的,照说都有中轴线了?不然。我们的办公大楼是对称的,但自前面走去,没有入口,楼梯在后面,而面向文理大道的方向,有楼梯而没有趋近的中轴通道,因此中国人生活其中,并没有真正“中国的”感受。“正”与“中”的观念要表现在行走在中轴线上,而不只是外表对称而已。
方正的标准在外形的要求上,是建立人造环境的权威性,所以在体型上以“大”为上,以“小”为下。所以国人习惯上把“大方”连起来读。大方是一个十分抽象的字眼,在早期的文字中,并没有形式的意思,只是一种人格或能力的描写。但套用到形式上,觉得十分顺适、恰当。今天使用这字眼状写一物的外形,即是表面上既大且方的意思,体大型方就是大方。但是大、小是相对的形容词,多大才算大呢?所以我们的形式观念,自大方引进了“气魄”这一个抽象的字眼。虽然在实际的度量上并不是那么大,但用周围的其他环境条件衬托出来,使它显得大,就是有气魄的,因此也就是好的。
从“大方”的形式观推下去,就可以具体地指出既宽又高的理想标准。我接触过的业主中,不论其年龄或出身等背景,不论在国外受过多少年的西式教育,对建筑物外形的要求,都不外高、宽二字。高可用较抽象的“崇高”来描写,崇高是体大的一面。“仰之弥高”是我们人体的心理反应。宽字即是广字,宽、广在人格中表示“宏”,表示“量”,故亦是大字的化身。宽大的心理状态可以用舒展来描写。瞻仰是对崇高感的激赏,表示头部上下移动,既高且广是壮阔的美感的来源。
方正的另一含义是简单。正字又可引申为整字。完整是其一义,整齐亦是其一义。简单而整齐就暗示完整的意思,在外形上,是方正感所不可或缺的性质。这一点自然使我国的建筑与西方古典的传统有很多相似之处。反过来说,要国人接受造型组合变化繁复而有奇特趣味的西方中世纪形式就十分困难。
这些当然都是方内的价值标准。在这里,歪邪的卑下是不用多说的,邪与恶字常常连在一起。我曾注意到,即使在儒家观念之外的阴阳说,也进一步强调这一说法,把方正与福祉同解,把歪邪与不幸相等。各位也许不能意会这一观念对我国环境计划的影响,但如果从西方建筑传统来看,斜的使用是很普通的一种解决环境问题的手法。因为我们文字的引申力与暗示力非常强,所以把邪与斜就很轻易地看做一类了。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不打算细说“歪”字在环境观得到的反感。想来大家可以意会我要在此提出来的,是“方外”环境的价值观。以我看来,对于方外者,我们的尺度总有些松动。这种环境的观念既非正,亦非邪,是一个“奇”,可是在这里,价值的观念并不很明确,表示方外的行为准则并没有一定的办法。比如“奇妙”与“平淡”,虽然一来自阴阳,一来自道家,但大家都可以接受。“巧”与“拙”亦是相对的观念,但亦为中国人所一体接受,使用不同的标准来衡量。表现在外形上,是中国庭园的曲折、炫奇甚至巧妙的安排。“小”在这里不一定表示“小气”,可能表示“小巧”。这又是文字的魔术在搞鬼了。
新与旧:中国人对环境表示的时间观
在环境的价值观中有一条是特别重要的,那就是中国人对时间的看法。时间表现在环境上是怎样的呢?很通俗的说法,就是新、旧的观念。其中的新表示在时间上的短暂,旧表示在时间上的长久。这是研究中国人思想行为上十分有趣的题目。
把我的主题点出来,我要说,中国人是喜新厌旧的。这一点发现,连我自己开始都觉得奇怪,为什么在一个以传统为重,以永恒的真理为重的民族,会对外在环境产生一种不同于道德标准的另一标准呢?这也是我国一贯的双重标准的一部分吗?

我逐渐发现,中国人是使用另一不同的角度去看世界的,所以我们的永恒感与西方的永恒感不同。比如说,在基督教东来前我们不相信灵魂不灭而升天的说法。即使轮回的说法,虽是外国传来的,至少表示了一种“周而复始”的中国人的哲学。周而复始,乃意味着新旧的永恒交替。物之生即死之开端,死即生之开端。但我们是喜生、恶死的。我们希望生,故“新生”为大家之所喜。
这种价值决然不同于西方。不是说西方不喜欢新奇,而是在西方的思想中,悲剧趣味的纪念性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西方人用人为环境的永恒感来表达这种纪念性的要求。我们不硬去与时间之流失抗争,我们承认时间是不能抵抗的,因此我们的永恒感是生物的,是寄望于后代之繁衍,后代之发达的。换言之,我们寄望于新生。
其结果是什么呢?在人为环境中,中国是保留古代遗物最少的文明古国。旧的不去,新的不来。除了少数的例外,我国更换朝代的时候,多半迁都,而把前代的古城一把火烧掉。建筑使用的材料都是暂时性的,我们并不是不产石头或砖头,而是没有人动脑筋去建造比较耐久的生活环境。因为我们知道变动不居的道理,永恒是强求不来的。
由于这个缘故,我们不尊重古代的建筑。即使在台湾,在古代遗物的保存上也碰到极大的阻力。在钢筋混凝土充斥的今天,大家对古式的民房或村落感到厌恶。如果今天为农村改建四楼公寓,农民会十分高兴地感谢政府恩德。对过去,我们没有留恋。可是看看西方世界,情形就完全不同了。他们对于过去十分尊重,古代一瓦一石均予以保存。在高度发展的西德,有不少中世纪的城市照原样保存下来。
从文化保存的观点来看,我自然很羡慕欧洲的做法。但是我国的文化中真没有保存古迹的这一精神?完全相反,如果让古人的生活环境破破烂烂地不加整理与重修,则为后人的不孝,是一种不道德的、没出息的行为。
所以要看我国的古迹,要到穷乡僻壤去看。目前所遗下的东西都是在干燥而穷僻的华北。真正有面子的富庶地带,后世的子孙是不让前代的残迹有所遗余的,他们所使用的办法是重建,或相当彻底地重修。
在台湾,我们要看古代的庙宇要到没什么烟火的鹿港龙山寺去看。烟火鼎盛的台北龙山寺与北港妈祖庙则早已重修、重建过若干遍,完全不见早先的规模了。我参观北港的妈祖庙时,实在不忍心责备他们,因为信徒们奉献的真心表达在新的崇拜环境上;新的庙宇,通俗而有一种生命的力量。而我们的批评标准是难免西化了的。
再举另外一个例子来看,台北市每年自十月到十二月这三个月中,你看不到真正的台北市。“总统”府、台银大厦及行政区的一切建筑,均披上新装。为什么有这种必要呢?因为我们现代的城市是表现不变性的。我们也尊重砖石,但我们所重视的是它抗震、抗风的力量,不是它外形的不变性。当我们的祖先用木材盖房子的时候,是每年要油漆的,故每到年节,它们与世人一样要披上新装。新装表示喜气洋洋,新装表示对福气的祈求。
色与空:中国人对环境的感受
自新年喜气洋洋的气氛,我们很快就可想到中国人对实质环境感受的性质。在这里,我姑且把这种感受的讨论限制在色彩方面,因为色感是对表面的感受,是最能说明国人的环境观的。
很奇特的是,中国人对色度的感受与其他方面一样,有很明确的二分倾向。在方内的世界,我们对色彩的要求是夸张的与激动的。对于颜色,我们要求鲜丽。很多年前,日本人伊东忠太就讨论过中国人的色感,提到我们喜欢强烈的原色,日本人则比较喜欢自然与清淡的颜色。
当然伊东忠太所看到的,仅是我国宫廷与民间建筑、装饰的实质。他是外国人,他不会以士人思想中的抽象理念,作为对中国人色感的判断根据。自这个角度看,他至少比中国的读书人少了一层有色的眼镜。我国的读书人在面对理念中的自然时,环境是没有色彩的,是黑白的,是比日本人的清淡的色感更没有颜色的。
传统士人对自然的观察所表达的色感,可以用一个“空”字来说明。“空灵”是这一情态的形容词,也是艺术最高的境界。在我国士人艺术的主体――山水画上,这一点表现得最清楚。画家不但使用以黑白为色的墨渲染画面,使笔到处有飘忽不实之感,而且在后期,使用了大量的露白,实际上等于用“空”来表示“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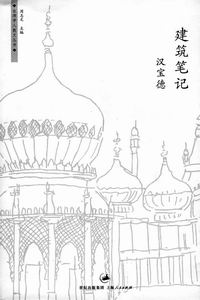 很极端地说,空是一无所有,是一种使人不产生感受的环境。这种理想表现出来就是“平淡”。可惜这理想并没有真正发挥在国人实质环境的建造上,我们几乎举不出什么实例来说明这一精神的存在。
很极端地说,空是一无所有,是一种使人不产生感受的环境。这种理想表现出来就是“平淡”。可惜这理想并没有真正发挥在国人实质环境的建造上,我们几乎举不出什么实例来说明这一精神的存在。
在这实质与理想的两个极端之间,我们中国没有调和的色感地带。这一点在以中庸为标榜的中国文化中,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所以在传统的中国环境中,没有“和谐”的色调系统。我们的色彩美主要是在原色间的对比上,在黑白与原色的对比上。前者如宫殿的色调,后者如中国人所喜爱的红与黑的关系。在新建筑的时代,建筑师如布鲁尔(1902―1981)的色彩手法在观念上是中国的。我们不喜欢重叠原色时所造成的关系。在方内的世界里,我们对色彩的要求是有很多象征性的意义的。比如颜色与社会的阶级制度自周代以来就定下了。而后虽有更改,但仍是森严的。大体说来,不管制度怎么变,强烈而具刺激性的颜色的传统基础,使用对比的原色,使得我们的建筑在华丽的感受上超过西方任何时代的宫殿。
色彩的象征性表现在民间是幸福与灾祸。比如红色是中国人最喜欢的颜色,但不是因为它代表血液,或火焰,而是红乃幸福的、欢乐的象征。鲜丽的红表示这种幸福感的纯度,因此中间色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直到今天,中国人对颜色的感受还不是纯视觉的。
(摘自《建筑笔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版,定价:25.00元)
